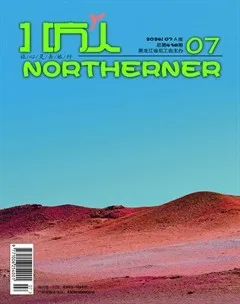他們的孤獨是因為這些他者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的《親屬》是一篇簡單的小說,它的情節幾乎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單身的姨媽到車站等她的外甥,等到半夜,外甥沒來。
這么簡單的一件事被奧茲寫得那么長,然而真正讀起來又覺得一點兒也不長,每一個字都不可或缺,每一個字都情緒飽滿。
這個姨媽,吉莉·斯提納醫生,單身未育,瘦削嚴肅,戴眼鏡。此時,她為這個外甥吉戴恩細心準備好了各種生活用品,冰箱里放滿吃的,還有各種取暖的設施,桌上還擺著新鮮水果和干果果盤。準備好這一切之后她就到了車站,等著外甥來。
等待的時候,她回憶了外甥小時候來這里度過寒暑假的一切經歷。你會不會以為那是一些溫馨美好的記憶,就像侯孝賢執導的《冬冬的假期》那樣?畢竟這是一個如此疼愛外甥的姨媽。
并不是。外甥是一個“昏昏欲睡,耽于夢幻的孩子”,他可以一連幾個小時一個人玩游戲,并不喜歡與人溝通。他很固執。但更固執的似乎是這個姨媽。有一次,外甥堅持一個人待在家里,不愿意跟著姨媽出診,說有玩具袋鼠陪他。姨媽大為光火,用雙手打他的頭、他的肩膀、他的后背。外甥吉戴恩在這樣的暴打中,一聲不吭地蜷縮著身子,等襲擊結束后才問:“你為什么恨我?”
她突然間驚愕不已,哭著吻孩子,向他道歉。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喜怒無常的姨媽,但事實上,這喜怒無常正展現了她的破碎,她孤獨到失衡,她的愛總是帶著恨,因為愛總是令她動作變形。
孩子并沒有因此不再來,這些事他也沒有告訴自己的母親。為什么沒有告訴?并不是因為孩子忘了這事,而是我們需要猜到他的猜測:他敏銳地猜到母親不是一個什么都能告訴的人。至于孩子怎么想的,作者和孩子本人一樣,不會給我們答案。
故事直到最后,孩子(現在已經20歲了)都沒有來,也許是下錯了車站,也許是不想來,姨媽卻懷疑孩子是在車上睡著了,誤了下車。她穿過整個村莊,走到停車的地方,叫來司機開車門,她堅持要到車上再檢查一遍。
她又孤零零地回到家。為外甥準備的那一切都在。
她加熱了準備的魚和土豆,然后關掉電熱器,坐在廚房的椅子上,哭了起來。
在我貧瘠又偏執的小說閱讀中,奧茲這篇小說是將孤獨寫得最好的一篇。這個姨媽,比梭羅還孤獨,比《局外人》中的默爾索還孤獨。為什么呢?因為她的期待。
正因為全篇都在寫期待,寫回憶,所以,此時的孤獨是那么孤獨,過去的不再復現,等待的不一定來,只剩下此時,漫長的此時。
可以與之對讀的是美國女作家卡森·麥卡勒斯的一個短篇《旅居者》,非常適合與奧茲的《親屬》對比閱讀。
內容也是同樣簡單,很日常:約翰·費里斯從巴黎回美國參加父親的婚禮,正準備第二天乘坐飛機離開。多出來的這一天,他在紐約偶遇了前妻,于是應邀到她家里吃了一頓晚餐。
這個短篇的主體部分正是這頓晚餐。前妻一家的熱鬧和溫馨使他的孤獨顯得那么可恥,他不得不偽造自己的現狀,說:“我是去年秋天才認識燕妮的,她是一位歌唱家,簽了合同在羅馬演出,估計不久之后我們就要結婚了。”
事實上,燕妮是有夫之婦,現在是一個夜總會的駐唱歌手,經常工作到深夜。一年來他們根本沒有提到過婚嫁的事。
“費里斯突然覺得自己成了一個闖入者。他為什么要來呢?他在受苦。他自己的生活似乎過得如此孤單,活像一根脆弱的支柱,幾乎沒能撐起歲月殘骸中的任何東西。他覺得在這家人的房間里一分鐘都待不下去了。”
當我們見到衣著溫暖的人,我們更為自己的衣不蔽體感到寒冷,費里斯正是如此。他在前妻家的溫馨中深感孤獨。吉莉·斯提納呢,則是在對外甥的期待中深感孤獨。如果沒有前妻的晚宴,如果沒有外甥的可能到來,他們的孤獨不會那么尖銳。
他們的孤獨都因為這些他者。
(摘自2024年第5期《讀者·原創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