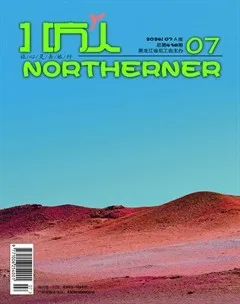在菜場感受城市的呼吸

一座城市,最吸引我的,從來不是歷史名勝或者商業中心,而是菜市場。中國太大,經濟高速增長讓許多城市的外觀大同小異,甚至連旅游商品都面目可憎地趨于一致,只有在菜市場,還能從一些地域性的物產上,分辨出各自不同的風貌。
我去汕頭衡山市場,看著賣姜的四十多個攤位,把洋姜、子姜、生姜、老姜等一樣樣品味過去;在臺灣蘇澳的南方澳魚市,凡是沒見過的海產我都要嘗試一下;千島湖畔的淳安小菜場,我和商販一起,抓著清水螺螄在機器上一個一個地剪去尾巴……像這樣的菜場,充滿了生活氣息的流動。在曼谷,在東京,在順德,在成都,在長沙,這些城市的氣味幾乎都可以從菜市場里面找到。
我知道作家殳俏正在拍一個關于“地球上的菜市場”的紀錄片,從菜市場開始品味那些風格化都市,了解城市人的區域性格。這是太讓人期待的題材,角度選得真好。記得當年蔡瀾先生給我講過在那不勒斯的經歷:早上五點就被房東叫醒,迷迷糊糊坐船去一個小島上采購最新鮮的魚,回來的途中,又去菜場采買和魚搭配的各種輔菜,然后回到旅館,安靜地等廚師把午飯做好。這種似水流年的感受,我覺得可能是旅游中最高的境界吧。
回到廈門的第八市場。那天一共有三個人陪我去買菜,除了“醬油哥”,還有一位大廚,叫張淙明,他是蔡瀾先生很喜歡的一位年輕廚師,有很好的海鮮料理手藝。另一位叫“海鮮大叔”,生物學家、科學松鼠會會員,據說是中國認識魚的種類最多的人之一,他熟知各種海產成熟的季節、出沒的區域以及口味。我們的奇幻旅行就要從這里開始。
第八市場藏身在縱橫交錯的老街老巷里,三四層高的騎樓綿延不斷,外墻的色彩早已被風雨所摧老,露出古樸懷舊的質感。這幾乎是我在國內見過的最大的海鮮市場了,幾乎匯聚了中國沿海所有的海鮮種類。
廈門的土筍凍有名,我指著水里蚯蚓一樣的蟲子,問是不是做土筍凍的原料。“海鮮大叔”糾正道:“這是北方的海腸,廈門當地的沙蟲叫可口革囊星蟲,身上是有Burberry格子花紋的。”再往前走是一家賣貝類的店,有四十多種貝殼,“海鮮大叔”仔細介紹著各種螺的界門綱目科屬種以及口感。張廚聽著不耐煩,說:“老陳愛喝啤酒,給他選個苦螺就可以了。”
隔壁一家還是水產。有一種相貌丑陋的魚叫虎鯊,是臺灣海峽出產的魚類,從前廈門人不吃,叫它“狗鯊”,因為它的皮上有很多沙子一樣的東西會影響口感。后來,日本從廈門進口虎鯊,需求量很大,廈門人漸漸也開始吃這種東西。攤檔里三個年輕人很麻利地把虎鯊進行了切割,交給張廚。兩個小時之后,清水煮過的虎鯊魚片和秋葵一拌,淋上醬油,爽口。
就這樣一家一家逛下來,總共五條街,購物袋開始逐漸飽滿。在日新月異的城市變化中,這片老的街區或許也要面臨拆遷。每天,從第八市場走出去的食物會幻化成無數餐桌上的景觀,也會化作裊裊的炊煙,成為這個城市特有的味道。
即將結束采購,張廚帶著我轉到一個很深的小巷子,叫河仔墘,巷子很窄,而且只有一個挖牡蠣的老太太。張廚對《舌尖上的中國》拍了汕頭的蠔烙一直耿耿于懷,他堅持認為廈門的海蠣煎才更美味,因此要買一點新鮮的牡蠣。只見他蹲在老婆婆身前,笑容可掬地挑了七八兩蠔,禮貌地放下錢,和婆婆說再見。老人卻旁若無人,自始至終沒有搭話。據張廚說,從前賣蠔的是一對老夫婦,這位婆婆特別健談。每次去買蠔,她都要跟你講,吃蠔要吃小蠔,個頭大的都是外地運來的,本地的小蠔才最甜,適合做海蠣煎。但老太太有一個毛病,每天會長時間地和老伴兒爭吵,幾乎從開市到收市,在她家買過蠔肉的廈門人都記得他們尖銳的閩南話的交鋒。幾年前,張廚去進貨,發現老爺爺不在,再過一陣,婆婆也不在鋪子里了。又過了將近一年,老婆婆一個人孤單地回到了這個挖蠔的小攤檔上,自此再也聽不見她說一句話,只有頭頂的小風扇在不停地轉。張廚的故事讓大家唏噓,離開市場的路上,很長時間都沒人說話。
還是“醬油哥”善于調節氣氛,不緊不慢的閩南話伴隨著車輛發動同時響起:“現在是廈門最美的季節,也是最鮮艷的季節,等下拐過彎去,你就能看到大片鮮紅的哄房發——哦,是鳳,凰,花。”
(摘自文匯出版社《吃著吃著就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