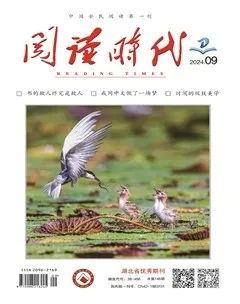“包”治百病,幾千年前就存在了
沈騰、馬麗主演的電影《抓娃娃》票房一路飆升,片中女主貼在男主耳邊念經(jīng)般說(shuō)的“愛(ài)馬仕kelly橙色荔枝紋”迅速成為全劇爆梗,同名話(huà)題也沖上了熱搜,有網(wǎng)友調(diào)侃“‘包’治百病”。日常生活中,一提到流行的包包款式,你可能馬上就會(huì)聯(lián)想到法國(guó)、意大利等時(shí)尚潮流之地。可誰(shuí)能想到時(shí)尚的盡頭是傳統(tǒng),好看又實(shí)用的包包,我們的祖先早在幾千年前就用上啦。
商周春秋:古早版“國(guó)民包”居然還分男女款
《詩(shī)經(jīng)·大雅·公劉》中有這樣一句詩(shī):“乃裹糇糧,于橐(tuó)于囊。”描述的是公劉在出發(fā)前做準(zhǔn)備,率領(lǐng)眾人將豐收的糧食制成干糧,大包小包都裝得滿(mǎn)滿(mǎn)當(dāng)當(dāng)。可見(jiàn)關(guān)于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時(shí)期。不過(guò)向來(lái)講究的古人在那時(shí)將大包稱(chēng)為“囊”,而小包則被喚作“橐”。
詩(shī)中的“囊”是為了裝干糧,古人心想:“既然囊可以用來(lái)裝干糧,那我隨身的鑰匙、手巾、印章以及憑證一類(lèi)的物件也能裝!”于是他們就研發(fā)出了“佩囊”。這個(gè)“佩囊”通常是被掛在腰間,不過(guò)它還可以手提,或肩背,所以也被稱(chēng)為“持囊”或“挈囊”。
作為“國(guó)民包”,佩囊的材質(zhì)與款式也在不斷升級(jí)換代。至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佩囊易名為“鞶(pán)囊”。據(jù)《禮記正義》卷二十八《內(nèi)則》中記載:“男鞶革,女鞶絲。”由此可知升級(jí)版的“國(guó)民包”居然已分男女款,男款的是用皮革制成,而女款的則是絲制的。
漢代:獸頭腰包皇家發(fā)布的“限定包”
漢朝時(shí),還出現(xiàn)了一種叫“綬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其賞賜臣僚,可謂皇家發(fā)布的“限定包”。有綬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綬囊也叫“傍囊”,主要用于盛放印信一類(lèi)的東西。
因?yàn)椤鞍币雅c身份聯(lián)系了起來(lái),所以在圖案、色彩上都有規(guī)定和講究。綬囊的正面通常有獸頭圖案,其中以虎頭居多,整體造型為方形,四角略圓,周邊還會(huì)加點(diǎn)小裝飾,日常被系在前腹或腰間。
在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要想知道一個(gè)人是否有官爵加身,就看他腰間的綬囊上是否繡有“獸圖”。東漢史學(xué)家班固,就曾受賜虎頭綬囊一雙。
綬囊一直流行到魏晉南北朝,只不過(guò)包上的圖案不再拘泥于獸頭,獸爪也成為流行元素。
唐代:出差官職不夠借包來(lái)湊
唐代以后,隨著社會(huì)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古人對(duì)包的需求開(kāi)始精細(xì)化,于是又一新款限定包發(fā)布,它就是“魚(yú)袋”。
“魚(yú)袋”的主要功能就是用來(lái)收納“魚(yú)符”,而所謂“魚(yú)符”多用木頭或金屬制成,因?yàn)橥庑蜗耵~(yú)而得名。魚(yú)符有兩片,分別刻有“合”“同”二字,里面詳細(xì)地刻著官員的官位、任職何地以及俸祿等情況,這樣便于官員被皇帝宣召入宮時(shí),驗(yàn)明身份,防止欺詐現(xiàn)象。從這里可以看出,魚(yú)符相當(dāng)于現(xiàn)代人的居民身份證,而魚(yú)袋則是一種卡包。
只不過(guò),這種卡包在唐代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員才有資格佩戴。據(jù)《新唐書(shū)·輿服志》記載:“隨身魚(yú)符者,以明貴賤……皆盛以魚(yú)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最高檔次的包居然是用黃金裝飾。若是職位低的小官,想要到“國(guó)外”出趟差,還得去找大官借個(gè)紫色的“金魚(yú)袋”來(lái)?yè)螆?chǎng)子,這個(gè)行為在當(dāng)時(shí)被稱(chēng)為“借紫”。至天授元年間,武則天直接下令將“魚(yú)符”換成“龜符”,于是魚(yú)袋也就換成了“龜袋”。
宋代:招文袋連“鬼”都得配一個(gè)
到了清雅的宋代,士大夫以及讀書(shū)人已不再追求能象征身份地位的包,而是將充滿(mǎn)文藝氣息的“招文袋”作為穿搭的標(biāo)配。“招文袋”又被稱(chēng)為“昭文袋”或“照袋”,民間則稱(chēng)“刀筆囊”,是用來(lái)裝書(shū)本文具的包,多用皮革制成,相當(dāng)于現(xiàn)代人的書(shū)包或是補(bǔ)習(xí)袋。招文袋掛在腰上,官員們退朝后要將書(shū)袋掛在便服上。
目前招文袋并沒(méi)有出土文物,但很多古畫(huà)中都曾出現(xiàn)它的身影。如宋代李公麟《白描十六羅漢渡海圖》中的招文袋,看起來(lái)非常精致,在包蓋處還做了些類(lèi)似祥云的波浪狀設(shè)計(jì)。而宋代畫(huà)家方椿年所作《仙人過(guò)海圖》中的招文袋,看起來(lái)更像是布帛制成,包的翻蓋處還有一個(gè)小小的包掛,可見(jiàn)招文袋的制作材質(zhì)也很多樣。宋末元初畫(huà)家龔開(kāi)《中山出游圖》更搞笑,連畫(huà)中的鬼都給配了一個(gè)可斜挎的招文袋。
招文袋如此盛行,大概是因?yàn)樗O(shè)計(jì)簡(jiǎn)單,不拘泥于材質(zhì),也沒(méi)有過(guò)多的鑲綴,款式又很利落,實(shí)用性很強(qiáng),像極了現(xiàn)代文藝青年們的帆布包。若是走在宋代的大街上,不背上一個(gè)招文袋,都不好意思說(shuō)自己是文化人。

明清:貴婦“鏈條包”火了
在明清時(shí)期,“褡褳”非常流行,是普通勞動(dòng)人民和小商販的心頭好。商人或賬房先生外出時(shí),總是把它搭在肩上,這樣可以將兩只手解放出來(lái)干活。“褡褳”追求的是自然隨性與實(shí)用,它多以藤、草、麻等材料結(jié)網(wǎng)成袋,與現(xiàn)代人的草編包、網(wǎng)織包極為相像。褡褳分為兩層袋子,使用的時(shí)候從中間對(duì)折,搭在胳膊上,所以它還有一個(gè)名字叫“褡膊”。
褡褳也受貴族婦女的喜愛(ài),在福建福州宋黃昇墓中出土過(guò)一個(gè)小型的褡褳,系于尸體袍內(nèi)腰間,全形似兩個(gè)對(duì)稱(chēng)的扇狀帶相連,呈銀錠式,可以合并或展開(kāi)。可見(jiàn),褡褳不僅可以搭在肩上,也可以系在腰間。
除了褡褳外,商品經(jīng)濟(jì)繁榮的明清時(shí)期,由于新生事物的誕生,也出現(xiàn)了一些特定的包,如專(zhuān)門(mén)用來(lái)裝扇子的扇囊。明清時(shí)期的文人墨客喜歡在折扇上題詩(shī)作畫(huà),為了保護(hù)好折扇,不讓折扇上的字跡模糊,古人就制作了一種絲綢材質(zhì)的扇囊。古人將扇囊系在腰間時(shí),不仔細(xì)看都會(huì)以為是個(gè)裝飾物,壓根就沒(méi)有包的痕跡。
值得一提的是,鏈條包的祖宗在中國(guó)。2019年南京江寧將軍山明沐斌繼室梅氏墓出土了一件來(lái)自600多年前的“明朝貴婦方形鏈條包”。其實(shí),說(shuō)它是“包包”,也并不準(zhǔn)確。它的大小,充其量只有零錢(qián)包那么大,和現(xiàn)在一般的“包包”相比,用法和功能也有所不同。這是一款“嵌寶石蓮紋金盒”,現(xiàn)藏于南京市博物總館,金色盒面上,滿(mǎn)飾蓮花、如意云紋,鑲嵌紅、藍(lán)、綠三色寶石,還配了一條金色鏈子……不少網(wǎng)友直呼:“買(mǎi)它!”
曾參與考古發(fā)掘的工作人員介紹,這只小金盒,是掛在胸前的配飾,可以打開(kāi)。當(dāng)年,里面究竟裝的啥?時(shí)隔久遠(yuǎn),已經(jīng)無(wú)從得知,可能是香料,也有人根據(jù)盒子上的梵文等元素推測(cè),可能是放佛教經(jīng)文的。
此外,現(xiàn)代人所熟悉的荷包也在明清時(shí)期流行起來(lái)。尤其到了清代,服裝納入了滿(mǎn)族服飾的特點(diǎn),官服中必須佩戴荷包。每年過(guò)年,皇帝還將裝有金銀珠寶的“歲歲平安”荷包作為年終獎(jiǎng)賞賜給朝廷大臣們,而民間少女們也在等著將自己親自縫制的荷包送給心上人。
縱觀包的發(fā)展歷史,現(xiàn)代人不得不再次感慨:時(shí)尚的盡頭是傳統(tǒng)。
(綜合源自《北京青年報(bào)》《現(xiàn)代快報(bào)》及“上海博物館學(xué)院”,有刪節(jié))
責(zé)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