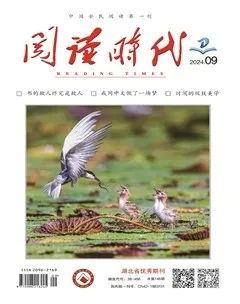荒漠之心
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非洲大陸的布須曼人被西方“文明人群體”蔑稱為野蠻人。他們的正名,得益于英國人類學家勞倫斯·凡·德·普司特在1955年進行的一場探險,以及記錄探險歷程的《荒漠之心》。書中,普司特引領讀者跟隨他的腳步跋涉南非深處,以平等的視角去觀察和認識這個古老族群,一層層揭開強加之罪背后的真相。
普司特是這樣講述第一次邂逅布須曼人的:“兩名幾乎嚇壞了的害羞婦人,后面緊跟著六個孩子。我給兩名婦女一些煙草,又給了孩子們一罐原味薄荷糖。婦女迅速消失在兩座小茅屋之間,回來時捧了一大堆曬干的鯛魚。”布須曼人的淳樸,在普司特的筆下一覽無余。而隨著了解的深入,布須曼婦女的堅韌品格,愈加令人敬佩。“男人都外出賣毛皮去了,要好幾個月才能回來。這段時間,她們得靠自己想辦法養活自己和兒女。”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中,身材矮小的她們既不害怕也不抱怨,只是默默與大自然博弈,等待家人的歸來。

普司特是在最難熬的旱季深入沙漠的,酷熱難耐的旅途,加深了他對傳說中“啜井”的期待。在親眼見證“啜井”時,普司特倍感驚訝:沙丘之間的舊河道深處,布須曼人將沙挖至手臂的深度,當出現潮濕的沙時,把一端纏繞干草的中空木桿插入洞中,埋上沙子,用腳踩實。然后,他們用盡全力吸吮木桿,等到汗流浹背,一股純凈明亮的水就從嘴角出現,水流越來越快,灌滿了一個又一個鴕鳥蛋殼。這無疑是一種絕技,更是人類對抗惡劣環境時展現出的不屈與頑強。
書中記述了布須曼人關于愛情的習俗:未婚男子會手持一副精巧的小弓,配上一種用草稈做成、尖端涂有特制汁液的箭,發現屬意的女子,就朝其臀部射出一箭。如女子將箭折斷,就表示拒絕;把箭保存好,則表示同意。普司特很想拍攝這種動人場景,他找來一名已婚但漂亮的布須曼姑娘和一名叫恩修的布須曼帥小伙,讓兩個人模擬表演。布須曼姑娘和她的丈夫都同意了,恩修卻怎么勸也不肯。直到表演取消,恩修才悄悄對普司特說:“那個人是我的朋友。雖然他說不在意,但我知道他看到自己的女人假裝是我的時,其實會很難受。”這種解釋,讓普司特的內心受到了震撼:在那一刻,恩修仿佛全身披覆著無與倫比的尊貴和優雅。
音樂對布須曼人無比重要,普司特“從沒發現任何一支窮困或絕望到沒有任何樂器的布須曼族群”。旅途中,遠處的獅吼像流星般逐漸消逝,某處矮樹叢里突然傳來音樂聲,“樂聲抑揚頓挫,越來越大聲,是旅行者懷鄉的曲調,帶著離別的憂傷,卻又有旅程中自由昂揚的歡樂”。那曲調和聲音,以及遠方躍動的星光,還有無盡黑暗的波動起伏,在銀河的巖石上碎裂成泡沫向外噴濺,一切都融合得如此美好。
神秘,是因為從未走近。留著非洲血液的普司特,其旅程既是大無畏的探險日記,又是深沉的精神追尋。在對布須曼人的不斷了解中,他看到了這支古老族群最真實的一面——“那是人類不曾丟失的部分”。
(源自《揭陽日報》)
責編: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