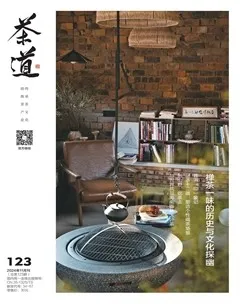日本最初茶栽培地探訪記(上)






日本臨濟(jì)宗初祖榮西禪師(公元1141-1215年),被稱為“日本茶祖”。
關(guān)于榮西禪師最初栽培茶樹的背振山石上坊,之前只是在一些文獻(xiàn)中看到記載,但一直查詢不到茶人實(shí)地考證的記錄,也不知道石上坊遺跡現(xiàn)在的狀況,或許早已蕩然無存。
本著“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xué)問者淺”的想法,我于2024年仲夏終于踏上了尋訪背振山石上坊的路程。
NO.01
走入背振山
據(jù)福岡市博物館“背振山的歷史與文化”披露:在日本鐮倉時(shí)代后期制作的名為“背振山靈驗(yàn)”的宴曲中唱道:從西遙遠(yuǎn)松浦瀉,可以看到圍繞笛崎松和磯路的志賀島,山上可以遠(yuǎn)望玄界灘沿岸的風(fēng)景。從玄界灘可以看到背振山,對(duì)于進(jìn)入博多灣的船只來說這是一個(gè)標(biāo)志,這里曾經(jīng)聚集了渡海到中國求學(xué)求法的眾多信仰者。相傳隨遣唐使同行的空海、最澄、圓仁、圓珍,以及平安時(shí)代末期兩次入宋的榮西等許多日本僧侶都進(jìn)入過背振山,以祈求航海安全。
背振山曾經(jīng)是日本天臺(tái)密教的重鎮(zhèn),一度十分繁榮昌盛。靈仙寺是這一帶眾多寺坊的總寺號(hào),如同真言宗高野山上的金剛峰寺,靈仙寺的下院以“坊”命名,我們要去探訪的“石上坊”就是其中之一,全山最盛時(shí)號(hào)稱共有“干坊”。在背振山上立有一根木柱,上面寫著“背振千坊巖萬坊英彥山三千八百坊”,就是傳說最多時(shí)這一帶共有3800坊,可見這座天臺(tái)圣山昔日的盛景。背振山也是靈仙寺的山號(hào),根據(jù)千坊所處的位置分為上宮、中宮和下宮。室町至戰(zhàn)國時(shí)代,由于戰(zhàn)火頻發(fā),這里的寺宇幾乎全部廢棄。明治初期后,山名曾被改為“上宮岳”“御岳”和“弁才岳”。
車開在崎嶇山路上,隨著導(dǎo)航經(jīng)過一座高架橋后,下橋就是左右分叉的丁字路口。指示牌顯示,通往石上坊需要向右拐彎。此時(shí),山路已經(jīng)明顯變窄,右邊的路口已被封住,車無法再行駛了,但距離石上坊還有三公里,如果步行的話大約需要一小時(shí)。問題是這里不能停車,來回兩小時(shí),車可能就被拖走了,況且山里路況不清楚,進(jìn)山容易出山難。看來只能退回到吉野里町的道驛,去打聽一下是否還有其他上山的路徑。
吉野里町道驛修建得還算氣派,道驛上寫的“千坊館”的名稱就是來自背振山上的“千坊”之稱,廣場上有一個(gè)環(huán)形溪水汲水處,許多附近的居民提著大大小小的水瓶在這里依次排隊(duì)接水,想必這里的山泉水十分清澈與甘甜,可謂一方好水滋養(yǎng)著一方好茶。道驛的商店里有當(dāng)?shù)叵薅ǔ鍪鄣摹皹s西茶”和“榮西”牌的茶飲,表明這里與榮西禪師的淵源十分深厚,吉野里町的山民至今還受惠于榮西禪師的遺德。
向商店里的大媽詢問去石上坊的山路,她們馬上警覺起來,其中一位說“上山的路已經(jīng)封閉,沿途有許多塌方和落枝,十分危險(xiǎn)。我不能告訴你們,萬一出了事故我們無法承擔(dān)責(zé)任。”這時(shí)的我們也是十分猶豫,車船勞頓,好不容易到了山前,卻不能進(jìn)山看一眼。于是,我們決定先吃午飯,在店里買些東西吃,或許當(dāng)我們從過路游客變身為堂吃顧客后,店員對(duì)于我們的請求會(huì)有不同禮遇。
于是,我們在商店里買了面包和飲料,以及當(dāng)?shù)禺a(chǎn)的大葡萄,在入店口一旁的桌子上用午餐。結(jié)束用餐后,又往車上搬了一箱“當(dāng)?shù)叵薅ā钡臉s西茶飲。再次詢問上山路線時(shí),剛才這位大媽終于找來筆和紙,給我們手繪了一張上山的路線圖,畫完之后還帶我們走到門外,指著前山接近山峰處的一片開墾地說:“石上坊就在這里,附近有一個(gè)茶園,找到茶園跟著指示牌走就可以找到了。”
獲得如此重要的信息和指導(dǎo),我們連忙謝過大媽,準(zhǔn)備上路。大媽卻再三關(guān)照:“開車上山一定要小心,要避開落枝和山石,出了問題要自己負(fù)責(zé),不要說我們讓你們上去的!”我們心領(lǐng)神會(huì),她指的是另外一條山路,要穿過一個(gè)隧道,出隧道后馬上右拐就可以一路開到靈仙寺附近。
NO.02
走進(jìn)靈仙寺
出了隧道,經(jīng)過一座橋,右邊的道路又被封了起來,只留出一條車行道的缺口。前面有一輛車,看到封路的警示牌,就倒車離開了。我們因?yàn)橛辛舜髬尩氖掷L線路圖,判斷就是要從這個(gè)缺口往深山里行駛。
山路越開越狹窄,兩邊的杉樹挺拔林立,路上不時(shí)有落枝橫道,我們只能十分小心地慢行,在有分岔的路口就拿出大媽手繪的地圖分析與判斷前行的方向。在一個(gè)較大的路口附近,有伐木工人在作業(yè),負(fù)責(zé)照看路況的大叔穿著黃色的馬甲,手持白色的小旗。我們開始擔(dān)心他會(huì)攔住我們繼續(xù)前往,當(dāng)我們向他詢問石上坊的位置時(shí),他卻十分友好地向我們指明了方向。在深山老林,一個(gè)善意的指點(diǎn),頓時(shí)給了我們新的希望。
之后的山路更窄,只能通過一輛車,如果對(duì)面有來車,已經(jīng)無法找到會(huì)車的地方了。路面上的落葉腐爛后長出了薄薄的苔蘚,有些濕滑,必須慢慢駛過這樣的路段,速度過快車輛容易打滑。車道的一邊就是懸崖,雖然有高大粗壯的杉樹阻擋,但還是擔(dān)心車輛會(huì)側(cè)向一邊。
車行十分鐘左右,看到一塊“靈仙寺跡距離70米”的牌子,注意到前方路面不整,我們就決定在此停車,步行前往。走過70米,需要往下走幾十級(jí)臺(tái)階。臺(tái)階口緣是用杉木橫臥而成,在濕潤的山間已經(jīng)長出一層層綠苔,相當(dāng)濕滑,需要拉著扶手慢慢下行。沿途看到了一些“山岳佛教圣地靈仙寺”“乙護(hù)法堂”“坂本咔”“蛤水道,蛤岳”以及“靈仙寺跡森林浴步道(日本茶樹栽培發(fā)祥之地)”的指示牌。
走了十多分鐘,我們先在“水上坊”附近小憩,一塊“靈水與水上坊跡”的牌子上寫著:靈水和水上坊遺址是附近唯一的涌泉水源,旁邊有刻著金剛界大日如來梵文“摩”字的石牌。這一帶被認(rèn)為是背振山中宮靈仙寺水上坊的遺跡,有一座三米乘四米的基石建筑遺跡,說明這里曾有一座廢寺,旁邊還有江戶時(shí)代天和、享保年號(hào)的法華經(jīng)供奉紀(jì)念塔,以及文政年號(hào)的信女供養(yǎng)塔等。走在這樣的山間小徑上,可以深切感受到當(dāng)年在此結(jié)庵的修行者的不容易。
背振山是位于九州福岡縣和佐賀縣之間的一座山,海拔達(dá)到1054.6米,是日本三百名山之一。據(jù)山根泰志撰寫的“夢幻之國境線:廣瀨文庫《背振山堺圖》與周邊”考察分析,當(dāng)時(shí)的背振山上宮有山頂宮,中宮有靈仙寺,下宮有修學(xué)院。現(xiàn)在,背振山上宮有背振神社,山頂保留有上宮弁財(cái)天和航空自衛(wèi)隊(duì)的雷達(dá)網(wǎng)站。下宮的修學(xué)院起源于1300多年前的飛鳥時(shí)代末期,和銅二年(公元709年)湛譽(yù)上人開辟背振山道場,逐漸形成以中宮靈仙寺為中心的“背振千坊”的山岳佛教圣地。慶長五年(公元1600年),在鍋島直茂公(佐賀藩祖)的幫助下,下宮的積翠寺得到復(fù)興,京都的曼殊院門跡(皇族)正式授予“修學(xué)院”院號(hào)。因此,積翠寺被稱為修學(xué)院,背振山的中心也從中宮的靈仙寺轉(zhuǎn)移到下宮的修學(xué)院。
中宮的靈仙寺現(xiàn)存的建筑物只有建于1852年的乙護(hù)法堂一棟,處在標(biāo)高500米的山腰上,附近散落有一些建筑遺跡、經(jīng)冢、墓塔等。經(jīng)冢群以平安時(shí)代后期為主體,1986年7月土砂崩塌時(shí)發(fā)現(xiàn)了一件收納18卷紙本經(jīng)的銅制經(jīng)筒。經(jīng)筒為鑄銅4層積上式,高34.7厘米,這個(gè)經(jīng)筒被推定為12世紀(jì)前半期的作品,現(xiàn)藏于佐賀縣立博物館。
(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