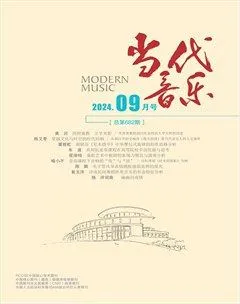趙元任學科融合導向思維在其音樂領域的滲透縱覽
[摘 要] 在當前教育大環境下,學科融合成為各類學科尋求新的發展機遇和契機的必然路徑。本文將趙元任音樂成就視為學科融合的產物,對其音樂論文和音樂作品從思維模式、指導思想、創作依據等方面進行概覽分析,以期為音樂學科新的發展方向和模式提供些許借鑒和思考。
[關鍵詞] 學科融合;趙元任;音樂實驗;結構主義;漢語言學
[中圖分類號] J605" "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2233(2024)09-0190-03
學科融合抑或學科交叉是教育界自二十一世紀以來出現的日漸高頻的詞匯,尤其是在2007年美國公開推行STEAM教育模式后,學科融合存在的意義愈發突顯。既承認學科的基本差異又不打破學科剛性邊界,提倡學科間可利用信息的相互融合滲透,以此推動學科的新發展,便是學科融合的核心思想。但實際上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趙元任先生便已用其獨特的思維方式為學科研究導向開辟道路,成為學科融合理念的世紀先行者。
以博學著稱的趙元任先生,其所涉學科涵蓋數學、物理學、哲學、音樂學,被稱為“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同時也是中國現代音樂學的先驅。趙元任之“先”不僅在于學科內的成就,更在于他在學科間搭建的思想橋梁。譬如在語言學中為語音理論引進長度、強度、音高、陪音、噪音和樂音等跨物理和生理領域的術語;[1]在音樂藝術創作中借鑒語言學中音韻音律的理論;又如在普通符號學中融入聲音等具有藝術美感的因素,種種都是趙元任“先”之代表。
商務印書館已出版的《趙元任全集》系列中,第十一卷收錄了現今所能收攬到的由趙元任創作撰寫的所有音樂著作,包括148首音樂作品和16篇中英文音樂相關論文。與所創作的音樂作品相比較,趙元任撰寫的音樂論文數量不算豐茂,正如他的女兒趙如蘭女士所說:“……父親在音樂方面的活動絕大部分是課余業余的。”[2]但正是在這樣業余空閑寫就的論文中,縱觀所述便能悟得,他并非就音樂言音樂。打通學科間隙,不同學科理論互為借鑒的融合思維模式在他的諸論文中縱橫始終。將不同學科領域辯證地融合,使藝術成為可分析可解釋的科學,而又讓理論科學變得感性和富有活力——這正是趙元任做學問的“先”之所在。
一、以邏輯學的思維進行音樂試驗
雖然隸屬哲學范疇的邏輯學內容復雜,難以一言概之,但還是能被簡略概括為一門研究內容、形式、結構,探索思維規律的學科。趙元任就很熱衷于進行學科體系結構和規律的探索,他的漢語語音研究、漢語語法研究、符號學研究等都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3]所著《中國話的文法》(1968)更是被譽為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扛鼎之作。追求嚴謹周密的研究態度同樣也根植于趙元任的音樂研究領域。
趙元任第一首公開發表的音樂作品鋼琴曲《和平進行曲》創作于1915年,彼時他的主修專業正是哲學。更早之前于1913年寫就了他的首部作品,即風琴曲《花八板與湘江浪》。這兩部趙元任的早期創作無論是音樂語言還是創作載體都大相徑庭,但兩者都是趙元任在研究音樂的內容和形式、研究思維的規律中誕生的,都是融合思維的試驗。
在刊發《和平進行曲》的《科學》首期雜志上,趙元任譜后附言“吾乃時得之于西人所奏之皮阿挪 (piano)”。并坦言道“此作完全是西方風格的”[4]作品,而創作的目的是“不用字號而用五線譜者,以五線譜可一覽而得聲之高下,且符號有時過繁,錄用字號常不易讀,而五線譜則有條不紊”?譹?訛。中國傳統音樂的記譜方式多為如工尺譜、減字譜等文字記譜,以數字標記音高的“簡譜”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傳入中國的。青年趙元任留美時輔修音樂創作,認識到“五線譜”這種音樂記錄形式能更準確、客觀地呈現音樂,且能更接近原始意愿,清晰記錄音樂風貌,從而達到時間和空間的并存。為了證實且內化五線譜的這種三維功效,便有了這首《和平進行曲》的誕生。至于《花八板與湘江浪》則是他在更早些時候以風琴為音樂載體進行的創作試驗。這部作品是“首次嘗試將外來多聲思維在鍵盤上與中國風格相融合”[5]。盡管作品創作之初成型于風琴,但因其成功地體現了趙元任的音樂理念,之后這部作品便在鋼琴上一再被演繹,故此它便被稱為“第一首具有中國風格的鋼琴曲”。
趙元任后來的創作都以對時間、空間、載體、形式的追求為先,不論是器樂曲還是聲樂作品,都很講究音樂創作的邏輯性,《新詩歌集》如是,《兒童節歌曲集》也如是,就如趙如蘭對父親作曲行為的評價一般:“父親對于音樂創作的興趣,有時也可以說是一種對邏輯的興趣”[6]。說是創作,卻更像是做實驗,一個有關邏輯思維的試驗。在這些試驗中,趙元任利用西方傳統古典音樂中的系統規律,不斷嘗試和聲、調性、中國曲調等元素結合的方式。試驗之初,規則的運用結合上痕跡明顯、手法生澀,便“不論是用類似五聲音節的旋律,還是用很多轉調來增加旋律活動的范圍,各種試驗都看得清清楚楚”[7];等試驗到“把中國音樂的特色同新的技巧融合得更自然一點”[8]便是試驗成功了。創作于1917年的鋼琴曲《偶成》因在民族風格上做出的大膽創新而被音樂學界公認為是第一部帶有鮮明中國印記的鋼琴曲,[9]可算是一部成功的試驗作品。
在創作中找規律是趙元任音樂活動中最為普遍的行為,尤其是他創作的藝術歌曲:要考究歌詞聲調的平仄和音調的高低長短;要考量中州派還是國音派的字調、音調的配合使用;要判斷清濁音的表現力……[10]這些都是邏輯行為的例證。哪怕是討論關于音樂的表現方式,在趙氏的表達中,“標準”“法則”等詞匯使用頻繁?譹?訛,也正明確了他對于藝術邏輯化、科學化的態度。因此,哪怕是對于自己創作的作品,趙元任能說出更多的因為所以,至于情緒之類的評價大多便三緘其口。理性大于感性,這也是他與別的專業作曲家最大的不同。
二、在辯證統一的方法論指導下研究音樂
趙元任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起便致力于國家語言統一運動,著名的96字奇文《施氏食獅史》便是因論證中文字符和拉丁字母之間的辯證關系而生的。與此同時,他又致力于漢語方言的調查。“國語統一運動”和“方言調查”這兩項圍繞語言進行的運動之間本就充滿了“辯證的統一”[11],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誕生了他一系列以歌曲為主要表現形式的作品,包括《教我如何不想他》(1926)、《海韻》(1927)等至今膾炙人口的藝術歌曲。藝術歌曲本屬于西方音樂體系,以西方的音樂形式為載體來裝載富含漢語言韻味的內在,這便是又一項具有辯證統一思想的行為。
趙元任在音樂領域的許多行為都是具有鮮明辯證統一的思想特征的。他早年間的一些書信中常記有與音樂同行間的學術探討,例如曾于1931年7月在《樂藝》第1卷第6期上發表有題為《討論作歌的兩封公開的信》的音樂論文,可稱為關于“中西語言和音樂雙學科思想交融”問題的一次重要思想大討論。趙元任在書信中與時任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校刊編輯的廖尚果先生主要就字節的和聲使用、核心字眼的拍點時值、詞曲間的輕重音和節奏節拍分配等問題進行了互動。其間討論的即中西音樂文化碰撞中有關取舍的思考:是多一些對西方音律法則的依附,或是在中國音韻音律的根系中求發展。這也是有關辯證統一思想的探討活動。
對于如何取如何舍,取什么舍什么,趙元任又有自己的一番堅持。趙元任有首很著名的歌曲《老天爺》,作曲家譚小麟從美國把它帶回中國時,它是一首首尾風格統一的純五聲韻律式的作品,但實際上這已是經由譚小麟根據中國審美習慣進行了結尾部分的修改而成的。在這部歌曲的原稿中,趙元任給中國五聲式的旋律使用了一個很不中國式的結尾,雖然他很同意譚小麟對于“風格統一”的理解和建議,但仍出于“旋律與歌詞通過節奏和音調變化得到密切結合”和“利用語言的特點作為旋律的素材基礎,這樣能使歌詞增加更強的表現力”的原則,保留了自己最初的創作手稿,并由此提出“調性自由的轉換方法,以及一些其他技藝,并非西方作曲家可以壟斷的”[12]的觀點,闡明了他從中國音樂特色出發的藝術創作思維立場。
趙元任的工作領域經常在客觀研究和主觀感性間切換。他研究各地方言,走訪民間,收集資料和記載數據,這些都是客觀的。在他的音樂論文中就有很多分析即客觀又科學,譬如《中國音韻里的規范問題》(1959),是從歷史、地域差異等多重視角規范地分析發音問題;又如《歌詞中的國音》(1937),不但對送氣音、不送氣音、清音、濁音、顫音、鼻音等進行地域上的發聲比較,還從生理構造出發物理性地講解其發聲原理。但是這些科學研究之余,他往往又會將理論的條條框框跟具有主觀表達特點的音樂藝術進行聯系,甚至承認音樂規則之外的變量存在。這種將主觀和客觀巧妙融合的辯證的研究方法正是趙先生作為中國現代音樂學研究先驅的特點。趙如蘭女士對音樂學這門學科評述道:“音樂學這一行在目標上,在方法論上說起來,有很多方面是類似語言學的。音樂學與作曲的不同,就好像語言學與作詩、寫小說的不同一樣。”[13]這里談論的問題既涉及學科內的共性和個性,也關乎學科間的通性和特性,秉承的就是她父親趙元任先生研究音樂學的方法和態度。
三、從漢語言學、符號學中尋音樂的根
作為中國現代語言學家的開山祖師,趙元任在語言學科領域的研究包括:語音研究、語法研究、方言研究、語義研究,其中具化到關于音位、音韻、聲調、語調等。伴隨著他的研究,他在語言學專業創立了許多經典理論,這些學術研究同時也橫向交融于他的音樂研究區域。
“無論詩文還是口語,只要遵循漢語特有的聲、韻組合及聲調組合規律,即突出漢語節奏主旋律,便可充分顯示出漢語的音樂性。”[14]這段話來自《漢語節律學》一書,其中關于漢語言中自帶音樂性的觀點表述,明顯呼應了趙元任的漢語言節律觀。在趙元任《關于我的歌曲集和配曲問題》(1970)——答李抱忱來信一文中,在解答關于“吟跟唱”跟歌詞歌曲配合的問題時提到“吟是根據歌詞的平上去入來定大致的調子”,同時跟美國通俗音樂中Jam Session的表演方式進行類比,并總結出“文一些兒或是正經一些兒的歌詞,大致是平聲低或是往下來,仄聲高或是往上走”以及“歌詞很白或是有幽默性的,就多用音的四聲”等。這里就涉及了漢語言學中漢語語音的七種節奏形式,以及對構成漢語節奏主旋律的“律”的強調。這樣的審美標準顯而易見地展示出趙元任在歌曲創作過程中遵循的規則,即從漢語言節律中尋音樂的出處。
“語言是傳遞消息的一種信號,標記語言的文字也是一種信號。再特別的語言,比如科學的專門術語,跟各種符號——例如數學、化學乃至音樂里的符號,也都是信號。”[15]此論點著述于趙元任《北京口語語法》(1952)一書中。在1956年他又再次在《中國語言的聲調、語調、唱讀、吟詩、韻白、依聲調作曲和不依聲調作曲》一文中強調了這個論點,開篇就明確指出寫此文章的目的是“描述和比較一個人發音的音調高低,對于中國語言韻律、音樂所產生的各種不同的功能”[16]。通過對語言中的成分進行理論舉例,同時結合自身音樂創作過程中的探討和與其他作曲家的交流,建議在音樂創作中注重語言成分和音樂元素的配合方式,從而把將所表達出來的語言、文學、音樂作品作為“信號功能和表情作用”[17]的角色進行欣賞。他特別強調語言音韻和音樂韻律間的功能性的互通,將音樂里所謂的感情表達以信號的表達方式進行明確意義的傳達,從而完成音樂所應具有的社會屬性,這樣的音樂創作才更可推敲、可延展。
諸如上述的非音樂類學科論點被借用于音樂領域的例子還有許多。如《常州吟詩的樂調十七例》(1961)中將吟詩中聲調高低的音樂性和地方字調發音結合論證;短文《用中文唱歌》(1924)中借用了語調法則;《中國派和聲的幾個小試驗》(1928)中以數學方程推演和聲音程的組合方式;《黃自的音樂》(1939)中大贊黃自在樂句中對于中國字輕重音的嚴格配置;《說時》更是以語言語法規則為要領貫穿文章前后。
在對趙元任音樂領域思維導向狀態的縱覽分析中,我們能清晰解讀出他對于學科間融合互助、協同與共的關系認同。音樂不單單是藝術的,也可以是科學的;不僅是可被感知的,同時也具備可視化的容量。音樂又是可再生利用的,以音樂為融媒,跨越文理,為自然科學搭建不同思想寬度的研究平臺,這是趙元任先生留給當代學科建設發展極為豐厚的思想寶藏,更為音樂學科的社會性發展提供了可借鑒模式和更廣闊的思路。
參考文獻:
[1] 趙賢德.趙元任先生對現代語言科學理論與實踐的探索[J].江蘇理工學院學報,2018,24(03):12-17.
[2] 趙如蘭.我父親的音樂生活[J].音樂藝術,1980(03):18.
[3] 張智義.趙元任語言思想內核研究[J].常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2022,40(06):92-97.
[4] 趙元任.趙家的生活(英文版)[M].紐約:紐約伊薩口述資料服務公司,1975:78.
[5] 陳鴻鐸.鋼琴音樂創作在中國的百年發展及反思[J].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17(01):61.
[6] 趙如蘭.回答一些關于父親的問題[J].中國音樂,1983(02):39.
[7] 趙如蘭.我父親的音樂生活[J].音樂藝術,1980(03):20.
[8] 同[6].
[9] 梁茂春.百年琴韻——中國鋼琴創作的萌芽(上)[J].鋼琴藝術,2015(05):23-28.
[10] 趙元任.趙元任音樂論文集[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17-18.
[11] 陳原.趙元任全集第11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前言.
[12] 趙元任.趙元任音樂論文集[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9.
[13] 同[6].
[14] 吳潔敏,朱宏達.漢語節律學[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142.
[15] 趙元任.語言問題[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9.
[16] 趙元任.趙元任音樂論文集[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1.
[17] 趙元任.趙元任音樂論文集[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12.
(責任編輯:韓瑩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