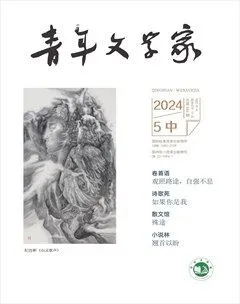淺析《長(zhǎng)恨歌》日常化的上海書(shū)寫(xiě)與城市文化建構(gòu)

作為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不可磨滅的代表人物,王安憶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以上海為背景的小說(shuō)。其中,創(chuàng)作于20世紀(jì)90年代的小說(shuō)《長(zhǎng)恨歌》最是王安憶尋根上海文化,塑造文學(xué)上海的巔峰之作。本文將從《長(zhǎng)恨歌》的文本出發(fā),首先分析王安憶上海書(shū)寫(xiě)的方式與特點(diǎn),即獨(dú)特的歷史觀和不同于他人的上海生活經(jīng)歷讓她另辟蹊徑地深入上海底層生活日常,進(jìn)行頗有尋根意味的日常化上海書(shū)寫(xiě);其次,論述其建構(gòu)的上海這個(gè)龐大城市的文化體系結(jié)構(gòu),重點(diǎn)探尋其文化結(jié)構(gòu)內(nèi)核涵義,即上海的“芯子”;最后,以宏觀視角,落腳于城市,拼接出王安憶意識(shí)中的上海,找到創(chuàng)造出“王安憶式”上海的上海想象。
一、另辟蹊徑—看見(jiàn)生活中的上海
20世紀(jì)以來(lái),上海作為當(dāng)代中國(guó)最矚目的城市之一,頻繁地活躍于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文字之中。一大批以上海為城市背景設(shè)定的文學(xué)作品開(kāi)始涌現(xiàn),并由此誕生了與京派文學(xué)相對(duì)的海派文學(xué)。廣義而言,從早期鴛鴦蝴蝶派的張恨水、包天笑,到海派文學(xué)的“巔峰”張愛(ài)玲,都是極具海派文化特點(diǎn)的作家。而這類(lèi)以上海為文本發(fā)生地,描繪上海都市中人物的生活狀態(tài)、情感走向,并在其中表現(xiàn)出個(gè)人對(duì)于上海文化的闡釋、想象與歷史見(jiàn)證的作品,便被稱(chēng)為上海書(shū)寫(xiě)。
在所有上海書(shū)寫(xiě)者中,王安憶有極高的研究地位,因?yàn)樗粌H繼承了前人對(duì)于上海風(fēng)情的氛圍化敘寫(xiě),更為重要的是她發(fā)掘上海底層市井生活中的上海城市樣貌,另辟蹊徑,強(qiáng)調(diào)日常化的上海書(shū)寫(xiě),以記錄日常背后的歷史文化。米歇爾·德塞圖在《日常生活實(shí)踐》一書(shū)中曾提出過(guò)“日常生活實(shí)踐分析理論”,他強(qiáng)調(diào)研究者不應(yīng)該像高樓上的俯瞰者,從俯視全局的視角去展開(kāi)研究,而是要深入日常生活實(shí)踐的場(chǎng)域,才能準(zhǔn)確地分析和建構(gòu)理論。王安憶正是踐行了這一理念,在《長(zhǎng)恨歌》的文本中著重強(qiáng)調(diào)上海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并以此與上海的歷史書(shū)寫(xiě)建立聯(lián)系,突出個(gè)人日常中蘊(yùn)含的歷史感、歲月感、滄海桑田的變化感,從而達(dá)到“對(duì)勢(shì)必被湮沒(méi)的文化記憶的恢復(fù)”的目的。
小說(shuō)開(kāi)篇便將讀者的目光帶往上海人日常生活最常見(jiàn)的,也是最主要的居所—弄堂。在書(shū)中,王安憶認(rèn)為它是“這城市背景一樣的東西”,“是中國(guó)畫(huà)中稱(chēng)為皴法的那類(lèi)筆觸”。女主人公王琦瑤的家就是典型的弄堂建筑,是一幢“堂屋里的光線有點(diǎn)暗沉沉,太陽(yáng)在窗臺(tái)上畫(huà)圈圈,就是進(jìn)不來(lái)”的老式弄堂。其次,王安憶在文中也用了頗多筆墨來(lái)敘寫(xiě)上海人生活中的穿衣和吃食,尤其是在食物方面,更是被視為“做人的里子”,即使是在動(dòng)蕩的時(shí)期里,王琦瑤代表的上海人卻在增加下午茶的樣式,點(diǎn)心、湯圓、烤魚(yú)片……各種花樣應(yīng)有盡有。穿衣上的細(xì)致描摹更是向讀者展示了《長(zhǎng)恨歌》中的上海是一個(gè)“針針線線、絲絲縷縷織成的世界”。書(shū)中,王琦瑤為了參加“上海小姐”的選拔,在服裝上幾經(jīng)考量,仔細(xì)琢磨選材、顏色、做工、紋樣等,從大輪廓到小細(xì)節(jié),細(xì)致入微;在平安里時(shí),王琦瑤和嚴(yán)家?guī)熌高@兩個(gè)女人之間的較量也是在穿衣打扮上展開(kāi)的。由此可見(jiàn),小說(shuō)的字里行間都在講述那個(gè)時(shí)代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的細(xì)膩,凸顯著王安憶日常化上海書(shū)寫(xiě)的特點(diǎn)。
王安憶之所以采取下探市井生活,回避宏大的歷史敘事的寫(xiě)作方式,是因?yàn)樗陨愍?dú)特的歷史觀和她曾在上海的生活經(jīng)歷。在王安憶自述中,她說(shuō)歷史應(yīng)該是由日復(fù)一日的生活點(diǎn)滴演變而來(lái)的。正是這樣的歷史觀,決定了她會(huì)放棄記錄戰(zhàn)爭(zhēng)和革命來(lái)講述歷史的傳統(tǒng)模式,轉(zhuǎn)而選擇描寫(xiě)日常生活的穿衣、吃食、居所的狀態(tài)和變化來(lái)映照歷史,感嘆世事變遷。并且,長(zhǎng)期在上海定居的經(jīng)歷,也讓王安憶將視角放低,能夠看到上海的“草根性”,撇去表面的聲色犬馬、紙醉金迷,了解真正的上海市民的百味生活。這樣一個(gè)看似“邊緣化”實(shí)則“日常化”的上海,一群認(rèn)真生活、專(zhuān)心生活的上海市民,才是王安憶對(duì)于上海的想象。
二、弄堂生活—折射上海文化“芯子”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曾在《看不見(jiàn)的城市》一書(shū)中寫(xiě)到,構(gòu)成城市的不是街道的臺(tái)階或者屋頂?shù)匿\片,而是她的空間量度與歷史事件之間的關(guān)系。所以,對(duì)于一座城市而言,與人相同,城市文化的組成理應(yīng)是像人格研究理論中的“牛油果型”人格一樣,由“外皮”的建筑、街道等空間幾何體和“內(nèi)核”日常生活等人文歷史積淀,并產(chǎn)生的奇妙的共鳴共同組成。
因此,要解析王安憶筆下上海的城市文化,便應(yīng)將目光放到代表上海空間的弄堂符號(hào)所承載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上。在《長(zhǎng)恨歌》打造的“日常化上海”中,弄堂建筑取代了時(shí)髦的咖啡廳、花園洋房,成了建筑的主角、小說(shuō)的載體、歷史的見(jiàn)證者。《長(zhǎng)恨歌》全篇一共出現(xiàn)了四種弄堂:石窟門(mén)弄堂、新式里弄、公寓弄堂和棚戶(hù)區(qū),分別代表了不同的階級(jí)、不同人群的居住地。石窟門(mén)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權(quán)勢(shì)之氣的一種”,有著大氣恢宏的外觀,內(nèi)里的結(jié)構(gòu)卻是狹窄復(fù)雜的,這正符合大部分中產(chǎn)階級(jí)的上海市民精明又重顏面的群體性格特征,在追求經(jīng)濟(jì)利益最大化和功能最合理的基礎(chǔ)上,充分延續(xù)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寄托。新式里弄相對(duì)于傳統(tǒng)石窟門(mén)弄堂則是更進(jìn)一步,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所以修建了能看到街景的陽(yáng)臺(tái),“但骨子里頭卻還是防范的”,依然有鎖有柵欄,防衛(wèi)森嚴(yán)。而公寓弄堂嚴(yán)防死守,“房間都是成套,一扇門(mén)關(guān)死,一夫當(dāng)關(guān)萬(wàn)夫莫開(kāi)的架勢(shì)”,每一戶(hù)之間的人情紐帶幾乎斷絕,越來(lái)越接近當(dāng)代的建筑形式。相比于以上三種弄堂,棚戶(hù)區(qū)則是最與眾不同的一處,底層人民聚居在這里,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他們雖住著漏雨漏風(fēng)的屋子,但這一間間小屋都是敞開(kāi)的,每一間小屋的燈光盡管微弱,但聚在一起像“一鍋粥似的”熱鬧、稠密,像一條寬廣又包容的大河,帶著整個(gè)上海向前流淌。
四類(lèi)弄堂雖然建筑形式各有不同,但他們的主人都是在這里過(guò)著柴米油鹽的生活,這是弄堂生活的核心所在。前文也曾寫(xiě)到王安憶在書(shū)中對(duì)衣食住行的描寫(xiě)細(xì)致且生動(dòng),王琦瑤在穿著上與嚴(yán)家?guī)熌赴蛋递^勁;喝蓮心湯必須配蟹粉小籠包……放大這些上海世俗生活的微縮景觀,我們應(yīng)當(dāng)看到上海市民面對(duì)生計(jì)問(wèn)題的懇切與努力,對(duì)生活精雕細(xì)琢,堅(jiān)守著代代傳承的生活經(jīng),在這些統(tǒng)稱(chēng)為“家”的弄堂里,經(jīng)營(yíng)著自己的煙火生活,日子充實(shí),人務(wù)實(shí)。不論人在外如何漂泊,在弄堂的“家”的世界里總是平和而忙碌地過(guò)著日子,這一份恒常而穩(wěn)定的日常精神,就是弄堂生活折射出的上海文化“芯子”,是歷史的浪潮沖刷后沉積下來(lái)的恒久的東西。正如王琦瑤身著家常花布旗袍在照片中的情態(tài):“這可說(shuō)是‘上海生活’的芯子,穿衣吃飯,細(xì)水長(zhǎng)流的。”王安憶建構(gòu)的上海城市文化正是在寄寓上海弄堂這一空間的外殼里的余韻綿綿、細(xì)水長(zhǎng)流的日常文化精神。
王安憶的上海書(shū)寫(xiě)著眼于日常生活為核心的上海文化“芯子”,建構(gòu)上海浮華都市表層之下的底層弄堂世界。這一底層文化視野使其有別于張愛(ài)玲,更區(qū)別于沉浸于十里洋場(chǎng)的上海懷舊病。作為兩位同樣是以女性角色為小說(shuō)主角,同樣多以上海為故事背景的女性作家,張愛(ài)玲與王安憶常被研究者們進(jìn)行對(duì)比。當(dāng)《長(zhǎng)恨歌》出版成為熱銷(xiāo)書(shū)之際,人們給王安憶貼上了“張派傳人”,給這本書(shū)貼上了“懷舊文學(xué)”標(biāo)簽,王安憶本人卻多次公開(kāi)反對(duì)這樣的言論,推崇魯迅先生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精神。的確,雖然二人同樣在小說(shuō)中以上海為背景舞臺(tái),卻選擇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視角看上海。王安憶選擇底層視角,以平實(shí)的語(yǔ)言描繪上海的人間煙火、市井生活,是人們“用手締造的上海夢(mèng)”,對(duì)于生活懷揣著熱切與真誠(chéng)的期望;而張愛(ài)玲則是浮于摩登上海的燈紅酒綠之上,其小說(shuō)的文化符號(hào)多取決于上海的新興事物和能代表上海現(xiàn)代性的要素,是看盡世俗的沒(méi)落貴族之感,看盡了人生起落無(wú)常的虛無(wú)之感,其構(gòu)造出的是一個(gè)“虛幻的上海夢(mèng)”,自甘消弭頹敗沉浸于浮華之中。
因此,同樣地,《長(zhǎng)恨歌》這部小說(shuō)也不應(yīng)該歸屬于懷舊文學(xué)之流。王安憶曾言:“其實(shí)我在寫(xiě)作時(shí)根本沒(méi)有什么懷舊感,因?yàn)槲覠o(wú)‘舊’可懷。”(《我眼中的歷史是日常的—與王安憶談長(zhǎng)恨歌》)會(huì)產(chǎn)生這樣的爭(zhēng)議主要是因?yàn)樾≌f(shuō)出版正值懷念舊上海熱潮迭起之時(shí),小說(shuō)的第一部也正是描寫(xiě)的舊上海時(shí)期的故事,第三部便被許多人弱化,只認(rèn)為小說(shuō)的重點(diǎn)就在于第一部的懷舊上。但是,這些解讀都忽視了《長(zhǎng)恨歌》最重要的對(duì)資產(chǎn)階級(jí)的批判性,對(duì)懷舊一流的反對(duì),恰恰是在第三部。尋找上海文化的“芯子”—上海人恒久不變的日常精神,才是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主要情感,并非懷舊。
三、文字中的城市—鮮明立體的上海意識(shí)與想象
王安憶的日常化上海書(shū)寫(xiě)在她的其他作品中也同樣有所體現(xiàn),這些作品和小說(shuō)人物改變了以往讀者通過(guò)其他作品對(duì)上海單一的認(rèn)識(shí)。在王安憶的筆下,上海是立體的、親切的,是現(xiàn)代性和非現(xiàn)代性?xún)蓚€(gè)維度并存的世界,這樣的文字表達(dá)了她鮮明且獨(dú)特的上海意識(shí)與上海想象,對(duì)傳統(tǒng)的上海意識(shí)和想象進(jìn)行了補(bǔ)充,打破了上海的浮華鏡臺(tái)。
首先,關(guān)于上海最廣為人認(rèn)同的意識(shí)—現(xiàn)代性。作為中國(guó)經(jīng)濟(jì)最發(fā)達(dá)的城市之一,上海的現(xiàn)代性是給所有人的第一印象。上海的精致與時(shí)尚是其現(xiàn)代性的鮮明特征。但是,王安憶描繪上海現(xiàn)代性的途徑不只在于表面的繁華,更是注重描摹上海人骨子里的精致完美以及他們現(xiàn)代化的思想。主人公王琦瑤等人有固定的時(shí)間聚在一起喝下午茶,為此“總要把房間整理一遍”,并且“特地去買(mǎi)了一套茶具”。這雖然書(shū)寫(xiě)的是日常生活,但更突出了上海人已然將儀式感、文化、修養(yǎng)全部融化在了習(xí)慣里,把生活過(guò)成了藝術(shù),這一切并不是為了追求什么,只是充分日常化的現(xiàn)代性,更是對(duì)生活的審美。除了生活觀念的現(xiàn)代性,《長(zhǎng)恨歌》中對(duì)于上海女性思想的現(xiàn)代性也有重點(diǎn)體現(xiàn)。王安憶筆下的上海女性追求浪漫,卻不執(zhí)著于浪漫。她們是柔情似水的外表和性子,內(nèi)里卻也有水一般“抽刀斷水水更流”的韌勁。這股韌勁,讓她們面對(duì)一群不懷好意的孩子,仍然可以?xún)?yōu)哉游哉地吃完小籠包,讓她們可以?shī)y容精致、衣著考究,但見(jiàn)到美食仍然大快朵頤,毫不矯揉造作。她們用這股韌勁樂(lè)此不疲地專(zhuān)心于生活。上海人與上海城在這里做到了相互成就,交相呼應(yīng)。
另外,是經(jīng)常會(huì)被現(xiàn)代性的光環(huán)所掩蓋的,上海的非現(xiàn)代性。上海之所以是一個(gè)矛盾的城市,正是因?yàn)樵诂F(xiàn)代性突飛猛進(jìn)的發(fā)展時(shí),非現(xiàn)代性仍然存在。在發(fā)展的過(guò)程中,上海對(duì)城市底層的忽視、一定程度上的排外性、對(duì)金錢(qián)的狂熱追求,都是上海不和諧的因素,嚴(yán)重影響了市民的眼界。王安憶十分理性地避開(kāi)了對(duì)上海的“濾鏡”,跳出與上海過(guò)近的距離,客觀又理性地觀照整體的上海,開(kāi)闊的視野讓更多人認(rèn)識(shí)到了更全面的上海,帶讀者到上海的各個(gè)角落,看那些被現(xiàn)代化落下的角落的樣子。
《長(zhǎng)恨歌》中的上海不僅是現(xiàn)代性與非現(xiàn)代性并存的立體上海,更是一個(gè)“王安憶式”的上海,有鮮明的王氏風(fēng)格,這源于王安憶與眾不同的城市想象模式。王安憶筆下的王琦瑤不過(guò)是城市的代言人,實(shí)際上是寫(xiě)了一個(gè)城市的故事。在讀《長(zhǎng)恨歌》,感嘆王琦瑤一生顛沛流離之時(shí),我們卻可以依稀感知到城市的脈搏。這是因?yàn)槌鞘斜旧硪呀?jīng)幻化成為一種現(xiàn)代文明的信號(hào)與女主人公王琦瑤的人生軌跡相融合,生命的起起伏伏都與這座現(xiàn)代城市同頻共振。這種“人城同構(gòu)”的想象方式和歷史的獨(dú)特的想象途徑,完美地被作者以掛鉤日常的方式聚合在一起,建構(gòu)“文學(xué)上海”的新世界,才形成了現(xiàn)在讀者看到的貼膚可感的上海這座城市。
王安憶的《長(zhǎng)恨歌》既不同于前人描寫(xiě)聲色犬馬、歌舞升平的摩登上海,也不追隨當(dāng)時(shí)所流行的“懷舊熱潮”,她以自己獨(dú)特的歷史觀和更深入的底層文化視野,另辟蹊徑地選擇日常化的上海書(shū)寫(xiě),講述上海弄堂中柴米油鹽的生活,描摹出上海現(xiàn)代發(fā)展潮流之下不曾改變的人間煙火,同時(shí)挖掘真正的城市文化內(nèi)核,并以其為中心,搭建“王安憶式”的文學(xué)想象中的上海。這種書(shū)寫(xiě)和想象為扭轉(zhuǎn)上海文學(xué)發(fā)展方向,敲醒了那些沉溺于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歷史懷舊者和過(guò)度關(guān)注物質(zhì)城市的文學(xué)工作者,并為他們指引了新的憧憬和方向,揭開(kāi)了上海文學(xué)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