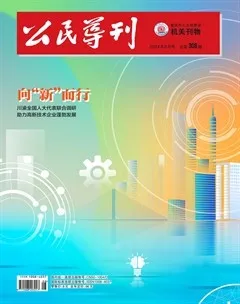研學“熱”需“冷”思考


在名勝古跡、公園、博物館、大學校園,隨處可見許多著裝統一的孩子在領隊老師的帶領下了解歷史文化、品嘗當地美食……進入暑期,持續攀升的不止是溫度,還有研學游的熱度。
研學游的興起,既是教育與旅游深度融合的時代產物,也是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的銳意革新。
然而,在市場日漸“熱辣滾燙”的同時,部分經營者資質不全、產品質量參差不齊、產品價格不透明、實際服務與廣告承諾不符等亂象也隨之產生。
如何進一步優化服務、規范市場,滿足大眾對高質量研學產品的需求,成為值得深思的問題。
定價多不菲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在古代,走出課堂的教育活動被稱為“游學”,是一種比較常見的教學方式。所謂通過云游天下,在“游”與“學”之中實踐“知行合一”。
研學游不僅可以幫助孩子開闊視野、增長知識、鍛煉體魄,更能飽覽祖國大好河山美景,增強他們愛祖國愛家鄉之情。
越來越多的家長期待通過研學等新的教育手段培養和提高孩子的綜合能力,達到寓教于樂的效果,這也是研學游受到家長青睞的重要原因。
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中小學生的研學實踐教育基地超1600個,?研學企業達3萬多家,?研學市場規模達1469億元,預計2026年將超2000億元。
據記者了解,研學游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由學校組織,納入了整體教學計劃,要求做到不以營利為目的、不增加家庭經濟負擔,價格一般在1000元左右,具有時間短、路程近等特點。另一類則由商業機構組織,由學生、家長根據自身家庭情況、個性化需求自主選擇參加,是目前研學游市場的“主力軍”。
各大旅游平臺、旅行社推出的研學游就屬于此類產品,博物館發現之旅、探索自然親子活動、海外游學等項目繁多,令人眼花繚亂。
然而,更讓人驚嘆的是研學游的價格。
記者在各個網絡平臺上搜索發現,研學游產品價格大多在幾千元到幾萬元不等:北京7天6晚9999元、粵港澳7天6晚10999元、絲綢之路12天11晚16888元;斯里蘭卡7天6晚21998元、澳大利亞10天9晚31998元……
各個平臺還設置了客服,只要你跟客服聯系并表示出興趣,立即會有專人來為你詳細介紹、量身定制。
“你想要的我們這里都有。”有客服表示。
記者咨詢了某教育培訓機構的研學游產品,其北京、大連、秦皇島、深圳、香港等地的研學游,價格幾乎沒有低于1萬元的。
如北京9日游價格高達16880元,具體費用還會根據客戶選擇的出發地不同、是否包含機票等條件有所上浮。
對此,客服聲稱,他們的產品非常具有性價比且非常搶手,一些熱門目的地不提前很久預定,基本搶不到名額。
質量令人憂
家長們為孩子花錢總是格外慷慨。而高昂的價格與空洞的內容形成鮮明對比,才是被家長們吐槽的真正原因。
“去三國爭霸還是去絲綢之路?”“去澳大利亞還是去新西蘭”……不少家長開始在網絡社交平臺上尋求答案。
記者梳理發現,目前市場上的研學游大致包括國防教育、人文景點、名勝古跡、自然風光、科技探索、親子之旅等類型。同時,部分產品行程還加入了知名高校或企業。
以北京9日游為例,行程包括參觀故宮博物院、圓明園、北京大學,以及探訪博物館、登長城等,安排得滿滿當當,鮮有空余休息時間。
看似豐富的行程,是否設置了富有特色的研學項目,是否會滿足不同學生的差異化研學需求?家長們卻不得而知。
“在比較產品的過程中,課程設計、導師資質、帶隊水平等真實情況難以甄別,有點像‘開盲盒’,一不小心就可能會‘踩雷’。”有家長表示。
一位帶孩子旅游的家長說,他在博物館入口處領孩子等博物館的定時講解時,看到這樣一個畫面——一個舉著小旗子的領隊,帶著一群中小學生朝志愿者走來。孩子們穿著統一的服裝,一雙雙眼睛新奇地左看右看。領隊問正在講解的志愿者:“可以讓孩子們跟著免費聽一聽講解嗎?”志愿者沒同意,隊伍掉頭走了。沒過一會兒,又來一個研學團,領隊向志愿者問出了同樣的問題。
“家長們完全不知道花高價給孩子們報的研學團,連講解費都想省,讓孩子們蹭免費的。同為家長,看到這一幕很感慨,這樣的研學游意義在哪里?”這位家長有些激動地說。
“孩子回來之后說,覺得很無聊、很累!”一位給孩子報名參加北京研學游的家長稱,報名的時候,機構稱研學的行程很多,還包括參觀中國古代最高學府,感覺非常值得。結果等孩子回來一問,才得知跟報名時說好的內容完全對不上,說去清華、北大研學,實際上只在門口拍了個照片,轉頭就去了某個不知名的小景區。
還有家長反映,有的機構假借“支教研學團”“公益項目”名義,實際帶孩子去了免費的博物館,“支付高價的收獲僅僅是有人幫忙帶孩子,其實孩子啥也沒學到。”
安全存隱患
研學游亂象的背后,反映出一系列問題。如機構缺乏專業資質、從業者素質良莠不齊、服務標準不統一、研學質量不高,導致虛假宣傳、以次充好現象嚴重。
一方面,部分機構缺乏教育理念和專業素養,過于追求經濟利益,導致項目設置內容匱乏、質量低下;另一方面,標準和管理制度的缺失使得一些不合格機構渾水摸魚,擾亂正常市場秩序。
一位做深度文化主題研學產品的講解老師介紹,根據她的觀察,很多做研學游的機構以前其實是做傳統旅游的。看到研學游市場的火爆,他們把目光轉了過來,只是將傳統旅游產品包裝一下,冠上了“研學”的名頭,實際上孩子們既“研”不到也“學”不到,“就是活脫脫的‘兒童旅行團’嘛。”
另一位研學游從業者也表示,部分機構從各個地方招聘大量帶隊老師,不審核相關資質,即使沒有相關從業經驗也“照單全收”,只為快速在研學游市場中分一杯羹,“帶隊導師沒有相關資格認證,還有大學生兼職導師,給孩子們講的科普知識甚至可能是錯的!”
據報道,有研學團讓兒童趴在路邊臺階上吃自熱米飯,并且沒有預備休息地方,孩子們只能隨地坐和躺,還宣傳是鍛煉孩子的“刻苦精神”。
這樣的研學游成了變相“割韭菜”,食宿隨意讓人詬病的同時,安全防范形同虛設更讓家長們后怕。
“在一個景點外面遇見過研學團,一群年齡各不相同的孩子過馬路,隊伍稀稀拉拉,拉得很長,帶隊老師走在最前面,有的還在玩手機,完全不管后面的孩子是否跟上,看起來太危險了!”沙坪壩區的一位大學老師說。
監管需加強
對于研學游來說,“游”是載體,“研”和“學”才是核心。
有老師認為,研學游的價值在于彌補課堂教育的不足,讓孩子們在課外享受旅行時光的同時,把知識和資源、書本和實踐串聯起來,讓孩子動手、動腦,真正有所收獲。
巴南區人大代表、重慶百君律師事務所律師邱鵬程介紹,當前對于研學產業的監管,各地各級各部門都在持續發力,但總的來說缺乏制度合力。
如《天津市教委關于印發天津市中小學研學實踐活動管理辦法的通知》,只針對中小學組織的研學活動進行監管,對社會組織的研學活動無法監管;《黑龍江省研學旅行服務企業(機構)管理辦法(試行)》,只能對旅行社開展的研學活動進行監管,無法對培訓機構、文化機構、純粹研學基地的研學活動進行監管;而山東省濟南市發布的《濟南市市級中小學生研學基地、營地管理辦法(試行)》,很明顯只管研學機構;《吉林省教育廳、吉林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于規范吉林省中小學研學(社會)實踐收費管理的通知》則只關注了研學的價格,不涵蓋研學的質量。
“總的來說,當前研學產業監管舉措多,但如‘九龍治水’,實效性卻不高。”邱鵬程說。
在邱鵬程看來,從業者素質不高、研學質量不高、研學基地條件欠缺、只游不研、價格不透明等問題,核心就兩類,一是合同訂立是否公平,是否存在合同陷阱的問題;二是合同履行是否到位,是否存在合同約定得天花亂墜卻未兌現的問題。這兩類問題本質上都應該由市場監管局進行監管,前者有合同行政監督管理辦法可規范,后者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可約束。此外,當地教委、文旅委等部門可制定相關標準,明確研學游的教育標準和規范,便于市場監管局對照執法。
“只有多部門形成合力,加大監管力度,引導機構堅守育人初衷,才能讓研學游真正發揮出教育的功能,為學生的成長成才提供有力的支持,推動研學游市場規范有序發展。”邱鵬程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