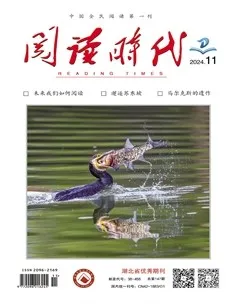孫犁未曾謀面的老師
入夜,雨悄然而至,伴著微風,淅淅瀝瀝,敲打著窗欞,如梵音,如小夜曲,清脆悅耳,一時間濾去了世間的嘈雜。我的心格外寧靜,就想找本書讀,找本與這寧靜契合的書,細細去讀。
于是,我從書架上翻出了兩本久違的書。
這是兩本包著書衣的書。我的書很少包書衣,沒有珍籍,自己未必讀得完,別人也未必讀,何必費事多此一舉。翻開泛黃的書衣,是一套《孫犁文集》。扉頁上端,赫然有孫犁先生親筆書寫的兩行娟秀的鋼筆字:
建斌同志指正
孫犁一九八四年七月
眼前頓時一亮,一件青蔥歲月時做的莽撞事浮現心頭。
20世紀80年代,我國剛剛打開通向世界的門窗,“歐風美雨”呼嘯而至,蕩滌了積存已久的陳腐之氣,讓人耳目一新。同時,也裹挾著大量灰塵雜物,把人弄得眼花繚亂、頭暈目眩。有一天,極為偶然地在哪本書中翻到了孫犁先生的名篇《荷花淀》,因為曾經讀過,只是隨意翻翻,不想卻被拽了進去。之前讀時覺得平淡無奇,既無動人情節,也無驚人之語,印象寡淡。此時細細讀來,感覺如同一條小溪,不疾不徐,潺潺流淌進干渴焦躁的心田,那么滋潤,那么熨帖。這篇著名的小說很短,感覺像散文,更像詩,鮮活的文字歡蹦亂跳地撲入心懷。我試著把一段話按詩的形制做了排列:
她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雪地上
也像坐在一片潔白的云彩上
她有時望望淀里
淀里也是一片銀白世界
水面籠起一層薄薄透明的霧
風吹過來
帶著新鮮的荷葉荷花香
這不是詩的語言嗎?多么清新雋永,詩意盎然。讀著這樣的文字,讓人覺得意蘊無窮,余音繚繞,如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又似久食糠菜,一旦逮著機會吃了一口肥肉,勾出饞蟲,再想吃卻沒了,那滋味豈是難受兩字了得。
于是,我四處搜尋孫犁先生的書。因身處偏僻的鄉下中學,所教畢業班教學任務繁重,竟很難覓得,只借到了一本薄薄的《鐵木前傳》。該書所寫背景即為我的家鄉河北安國,家鄉事,家鄉話,家鄉情,娓娓道來,親切感人。我一連看了幾遍,許多段落都可以背誦,仍愛不釋手,直到書的主人來討要,才依依不舍奉還。
自此,在寫作上,我就把孫犁當成了心目中的老師,用心體味他的語言,琢磨他的行文。
一日,發現一張過期的《天津日報》刊載一則消息:天津百花出版社新近出版《孫犁文集》兩冊。一時心血來潮,就直接給孫老寫信求書。信寄到《天津日報》,寄出后便覺荒唐,報社編輯能管這種瑣事?別說信難以轉到孫犁先生手中,即便轉到了,大作家又怎會理睬我這個無名小輩?自己敲了幾下腦殼,便把這事拋到腦后。
忽然有一天,郵遞員送來個郵件,鄭重地要我簽收。打開一看,竟然是我所求的那兩冊文集。更讓我想不到的是,翻開扉頁,居然有孫老的親筆題字。這實在超出我的想象,讓我喜出望外!
我如獲至寶,正好下午沒課,當即關上屋門,捧卷研讀,沉浸在先生用文字描述的那個世界里。因愛不釋手,一時物我兩忘,連時光似乎也已停滯。飯時已過,肚子發出抗議,我才匆忙去學校食堂打飯,而食堂已關門,只得吃幾塊餅干充饑。兩冊書,一篇篇讀來,如沐春風,如飲甘霖,自覺受益頗多。捧著這兩本有孫犁先生簽名的書,就如同有位和藹可親的老師站在面前,春風化雨般滋潤著我的心靈,引導我在文學的道路上前行。

這年,我的處女作,短篇小說《二鳳》,發表在河北保定地區文聯主辦的刊物《花山》頭條,編輯是金怡(后來得知是鐵凝)。中篇小說《村東,有座小白樓》,榮獲湖北首屆屈原文學獎征文二等獎。此后,相繼有中短篇小說在《青年文學》《上海文學》《長城》《莽原》等刊物發表。后來,由于諸多原因,輟筆多年,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未能走遠。不過,文學的種子已在心里扎下深根,我會用一種特別的視角去觀察社會,感悟人生,因此在急速流轉的世界里不會暈頭轉向,迷失自己。
孫犁先生遠逝了,他的文字依然活在人間。他的著述不算多,我把能搜集的幾乎都找到了。孫犁的書,適合靜讀。讀時,就像面對一位忠厚的長者,他不會告訴你多少高深的道理,卻會把你帶到一個他所創造的清新的世界里,讓你屏蔽掉浮躁喧囂的現世,慢慢融入其中。此時,你會覺得世間一切靜好,生出許多感動。等你再面對紛繁凌亂的生活時,或許就會有了不同的心態。
孫犁的書,立在書櫥中一個觸手可及的位置。當我徜徉在書海時,就會覺得有位和藹可親的老師站在身旁,教我為人為文。與孫犁先生雖素未謀面,卻感覺他如影隨形,時刻相伴,我認他是最好的老師。
雨,仍然沒停。伴著悅耳的雨聲,讀著孫犁,心里生出許多感動。
讀完這兩冊書,我依然包好書衣。這兩冊書在書柜眾多赤裸著的書中很惹眼,我知道,我會隨時把它們抽出來,再讀。
責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