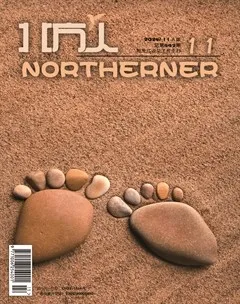我在清華湊數的日子

我自民國四年進清華學校讀書,民國十二年畢業,整整八年的工夫在清華園里度過????????????????????????????????????????????????????????????。人一生沒有幾個八年,何況是正寶貴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現在回想已經有些模糊,如夢如煙,但是較為突出的印象則尚未磨滅????????????????????????????????????????????????????????????。
“我要回家!”
八月末,北京已是初秋天氣,我帶著鋪蓋到清華去報到,出家門時母親直哭,我心里也很難過。我后來讀英詩人考珀的傳記時特別同情他,即是因為我自己深切體驗到一個幼小的心靈在離開父母出外讀書時的那種滋味——說是“第二次斷奶”實在不為過。
清華分高等科、中等科兩部分。學生們是來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地代表著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聽到。一天夜里下大雪,黎明時同屋的一位廣東同學大驚小怪地叫了起來:“下雪啦!下雪啦!”別的寢室的廣東同學也出來奔走相告,一個個從箱里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里面穿的是單布褲子!
有一位從廈門來的同學,因為言語不通沒人可以交談,孤獨郁悶而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語喊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鄉,但是不能時常來陪伴他。結果這位可憐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在清華,不洗澡后果很嚴重
新生的管理是很嚴格的。齋務主任陳筱田先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說話干脆而尖刻,精神飽滿,認真負責。
每天早晨七點打起床鐘,赴盥洗室,每人的手巾臉盆都編上號碼,臟了要罰。七點二十分吃早飯,四碟咸菜如蘿卜干八寶菜之類,每人三個饅頭,稀飯不限。飯桌上,也有各人的學號,缺席就要記下處罰。
臉可以不洗,早飯不能不去吃。陳筱田先生常常躲在門后,拿著紙筆把遲到的一一記下,專寫學號,一個也漏不掉。有學生久久不寫平安家信以致家長向學校查詢,因此學校規定每兩星期必須寫家信一封,交齋務室登記寄出。學生身上不許帶錢,錢要存在學校銀行里,平常的零用錢可以放少許在身上,但一角錢一分錢都要記賬。
在學校用錢的機會很少,伙食本來是免費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開始收半費,每月伙食是六元半錢,我交三元錢,在我以后就是交全費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錢,這都是在開學時交清了的。理發每次一角錢,手法不高明,設備也簡陋,有一樣好處——快,十分鐘連揪帶拔一定完工。所以花錢只是買零食。校內有一個地方賣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為嘉華公司,后改稱為售品所,賣豆漿、點心、冰激凌、花生、栗子之類。只有在寢室里可以吃東西,在路上走的時候吃東西是被禁止的。
洗澡的設備很簡單,用的是鉛鐵桶,由工友擔冷熱水。孩子們很多不喜歡親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簽名,以備查核。規定一星期洗澡至少兩次,這要求并不過分,可是還是有人只簽名而不洗澡。照規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則在星期五下午四時周會時公布姓名,若仍不洗澡則強制執行派員監視。
想要畢業,先學游泳
清華對于體育特別注重。
每天上午第二堂與第三堂課之間有十五分鐘的柔軟操。鐘聲一響大家涌到一個廣場上,地上有寫著號碼的木樁,各按號碼就位立定,由舒美科先生或馬約翰先生領導活動,由助教過來點名。這十五分鐘柔軟操,如果認真做,也能渾身冒汗。這是很好的調劑身心的辦法。
下午四時至五時有一小時的強迫運動,屆時所有的寢室課室房門一律上鎖,非到戶外運動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別人運動。我是個懶人,處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雙球鞋,打爛了三五支網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塊。
清華畢業時照例要考體育,包括田徑、爬繩、游泳等項。我平常不加練習,臨考大為緊張,馬約翰先生對于我的體育成績只是搖頭嘆息。我記得我跑四百米的成績是九十六秒,人幾乎暈過去;一百碼是十九秒。其他如鐵球、鐵餅、標槍、跳高、跳遠都還可以勉強及格。游泳一關最難過。
清華有那樣好的游泳池,按說有好幾年的準備應該沒有問題,可惜這好幾年的準備都是在陸地上,并未下過水里,臨考只得舍命一試。
據同學告訴我,我當時在水里撲騰得好厲害,水珠四濺,翻江倒海一般,否則也不會往下沉。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膩膩的。
我心里明白,這一回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便在池底連爬帶游地前進,喝了幾口水之后,頭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游完全程了,于是從從容容來了幾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地躍登彼岸。馬約翰先生笑得彎了腰,揮手叫我走,說:“好啦,算你及格了。”這是我畢業時極不光榮的一個插曲,我現在非常悔恨,年輕時太不重視體育了。
我的清華,我的愛情
臨畢業的前一年是最舒適的一年,搬到向往已久的大樓里面去住,別是一番滋味兒。這一部分的宿舍有較好的設備,床是鋼絲的,屋里有暖氣爐,廁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馬桶。不過也有人不能適應抽水馬桶,以為做這種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勢是無法完成任務的。可見吸收西方文化也并不簡單,雖然絕大多數的人是樂于接受的。
我必須承認,在最后兩年實在沒有能好好地讀書,主要的原因是心神不安。我在這時候經人介紹認識了程季淑女士,她是安徽績溪人,剛從女子師范學校畢業,在女師附小教書。我初次和她會晤是在宣外珠巢街女子職業學校里。
那時候男女社交尚未公開,雙方家庭也是相當守舊的,我和季淑來往是秘密進行的,只能在中央公園、北海等地約期會晤。
青春初戀期間誰都會神魂顛倒,睡時、醒時、行時、坐時,無時不有一個倩影盤踞在心頭,無時不感覺熱血在沸騰,坐臥不寧,寢食難安,如何能沉下心讀書?“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更何況要等到星期日才能進得城去謀片刻的歡會。
到了畢業那一天,每人都穿上白紡綢長袍黑紗馬褂,在校園里穿梭般走來走去,像是一群花蝴蝶。我還是代表全班的三個登臺致辭者之一,我的講詞規定是預言若干年后同學們的狀況,現在我可以說,我當年的預言沒有一句是應驗了的!至于我自己,最多是小時了了,到如今一事無成,徒傷老大,更不在話下了。
拿了一紙文憑便離開了清華園,不知道是高興還是哀傷。兩輛人力車,一輛拉行李,一輛坐人,在驕陽下一步步地踏向西直門,心里只覺得空虛悵惘。此后兩個月中酒食征逐,意亂情迷,緊張過度,遂患甲狀腺腫,眼珠突出,雙手抖顫,積年始愈。
清華八年的生涯就這樣結束了。
(摘自微信公眾號“青年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