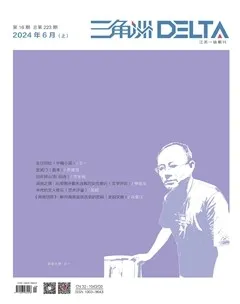新時代背景下交際能力模型的發展
大學教育是將學生從自然人培育為社會人的過程,成為社會人的重要標志在于能不能提供有效的社會服務。人的價值體現在人所處的社會網絡之中和人與社會的互動之中。站在新時代之初,教育者必須要有新理念新格局,完成打造擁有外語應用能力和交際能力的復合型外語人才的外語教育目標和使命。
提升外語交際能力一直是研究者和教育者關注的焦點,也是培養具有家國情懷、國際視野、專業本領,能講好中國故事的外語專業人才的需要。關于語言能力、交際能力和互動能力的研究對于外語教學、研究和實踐有著深遠的影響。
喬姆斯基提出語言能力的概念,認為語言能力是母語者建構合適的句子的能力。研究者的注意力逐漸由語言本身引向語言所表達的意義層面。海姆斯隨后提出交際能力理論,認為交際能力不僅需要語言能力,還需要交際對象、內容、適當的策略以及特定的交際語境,也涉及交際者的各種語言形式的社會文化知識。海姆斯對于交際能力的闡述進一步細化了影響意義的諸多因素,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隨著研究的推進,互動能力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Claire Kramsch提出互動能力的概念,認為互動能力并非專屬交際某一方,而是由交際參與者在“能動、行動、活動”的過程中共同構建的。除了語言能力外,著重語境與意義的語用能力是各種能力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研究者已經認識到語用能力的重要性,但在教學和測試中,語用能力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本文系統分析交際能力,交際能力的組成部分語用能力,交際能力發展的新動向互動能力的發展演變以及三者的相互關系,以便為外語教學提供有益的借鑒,指導交際教學的目標與方向。
對于語言能力、交際能力和互動能力三者的關系,研究者作了多種探討,其中Abdulrahman和Abu-Ayyash認為喬姆斯基的語言能力理論改變了語言學的研究方向,海姆斯批判地繼承了喬姆斯基的語言能力理論,他指出僅有語法知識無法確保有效交際,認為喬姆斯基的理論不足以解釋整體性的個體語言行為,從而提出了交際能力理論。Claire Kramsch與其他研究者從交際互動與能力建構的視角審視語言問題,提出了互動能力理論,將外語能力概念進一步引向實踐與建構。無論三者關系如何,所涉及的構面如何,本研究認為語言交際是一種整體化的人類行為概念,語言能力、交際能力和互動能力在語言交際活動中立體交錯,視角不同,各有側重,共同構建交際行為,達成交際目標。因此,本文希望通過對交際能力和交際能力模型的分析探討,考量作為交際能力重要構面的語用能力和互動能力在語言交際中的作用與相互關系。
海姆斯的交際能力原則
海姆斯作為交際能力的提出者,強調交際能力是交際者在交際場景中使用語言的能力,而不是脫離交際場景孤立存在的語言能力。海姆斯提出了交際場景中語言使用的四項規則,即海姆斯的交際能力原則:形式可能,即交際中的語言符合語法,交際中的語言或行為能夠引發適當的語言反饋或非語言反饋;可行,即交際語言與行為在交際者的認知范圍內,是交際者可以理解的,可行原則更偏重心理語言學層面,強調交際者能夠理解或辨識交際內容;適當,是指特定語言行為表現符合特定情境要求,如交際語言與行為符合身份情境或文化情境;切實行動,指前述被認為是形式可能、可行和適當的語言在真實情境中得以實際使用,切實行動也包括:即便是被認為形式不可能、不可行和不適當的語言在特定情境中仍然會被使用,如兒童話語或反諷。
Canale和Swain的交際能力模型
在喬姆斯基語言能力理論和海姆斯交際能力原則的基礎上,Micheal Canale和Merril Swain提出了交際能力模型,因其簡要適用,這一模型是目前為止外語教學研究中應用最為廣泛的框架模型。Canale和Swain的交際能力模型(以下簡稱Canaleamp;Swain模型)有助于清晰地展示交際者在交際時需要具備的知識和技能。
以交際(communication)為中心,Canaleamp;Swain模型包含三種能力:語法能力、社會語言能力、策略能力。其中語法能力是知識要求,社會語言能力和策略能力是技能要求。語法能力是交際的前提和基礎,社會語言能力和策略能力是優化和強化交際效果的保障。
具體而言,語法能力確保交際的可理解性(comprehensiveness),在知識層面需要交際者具備語音、詞法、句法、語義的相關知識;社會語言能力側重技能或規則,以確保交際的適切性(appropriateness),需要交際者理解并遵守相應的社會文化規則以獲得語句的聚合性(cohesion),需要交際者理解并遵守相應的話語規則以保持話語的連貫性或條理性(coherence);策略能力偏重技能,目的在于確保交際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策略能力可分為語言策略和非語言策略。解釋、復述、推測、論辯等屬于語言策略,而表情、手勢、動作等身勢語言屬于非語言策略。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表情、模因、縮略語、交際中所使用的應用軟件等多模態網絡技術元素的使用也被納入非語言策略的范疇中。
總體而言,Canaleamp;Swain模型與海姆斯的交際能力四原則一脈相承,有共通之處。語法能力與海姆斯的形式可能原則照應,二者的區別在于形式可能原則涵蓋更廣,除了語言符合語法之外,還要求語言交際行為能引發語言或非語言反饋。
海姆斯之后,研究者提出的交際能力觀念愈加涵蓋廣泛,研究者開始關注語言教學的切實需求,這種關注催生了交際教學法理論與方法的形成,也印證了交際能力研究對語言教學帶來的深遠的影響。
Bachman和Palmer交際語言能力模型
隨著相關研究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期,Bachman和Palmer提出的新模型被命名為交際語言能力模型(以下簡稱Bachmanamp;Palmer模型)。這一模型中,語用能力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上。Bachmanamp;Palmer認為交際語言能力由組織能力和語用能力構成。
組織能力類似于Canaleamp;Swain模型中的語法能力,因此可以稱之為語言組織能力。組織能力由語法能力和篇章能力構成,語法能力指生成可理解語句的,關于語音、詞匯、構詞、句法、語義等方面的能力;而篇章能力指能夠將語句組織成為可理解的口頭語或書面文本的組織、連貫、修辭等的能力。篇章能力中的連貫性是偏重衡量口頭語言的能力標準,而修辭能力則偏重衡量書面文本的組織能力。
語用能力在Bachmanamp;Palmer模型中被視為語言知識的半壁構成要素,這證明研究者開始意識到語用能力在交際中所占的比重和重要作用。Bachmanamp;Palmer認為語用能力是以言行事的功能知識與社會語言知識的總和。
語用功能知識即交際者以言行事的能力以及理解和表達言外之意的能力,功能知識可以幫助交際者將言語、句子、文本與傳遞的意義以及說話者的意圖連接起來。語用功能知識包含以下四個方面:概念功能、操控功能、啟發功能、想象功能。語用功能知識的具體含義如下:
概念功能保證交際中的意義傳遞,確保語言表達與理解的順暢清晰。實際交際中人們的描述、分類、解釋、表達特定的情緒情感,都體現了語用功能知識中的概念功能。操控功能是語言使用者利用語言影響或控制外部世界的能力,包括工具性、規約性、人際性等的具體功能。啟發功能指利用語言交際或在語言交際中拓展交際者知識的功能。想象功能是指為了達到諸如幽默、藝術或美的目的通過語言創設想象世界的功能,笑話、修辭、文學與詩都屬于此類。
語用能力中的社會語言知識可等同于Canaleamp;Swain模型中的社會語言能力。語用能力中的社會語言能力被看作是優化交際效果的保障,社會語言能力側重技能或規則,目的在于確保交際的適切性,需要交際者理解并遵守相應的社會文化規則。
對于策略能力,Bachmanamp;Palmer模型也有所提及,但不同于Canaleamp;Swain模型中的策略能力,Bachmanamp;Palmer交際語言能力模型中的策略能力側重交際者在測評中表現出的策略能力,認為交際者的話題知識和情感圖式構成其策略能力,具體表現在交際者設定目標的策略能力、進行評價反應的策略能力和規劃實現交際目標的策略能力。
交際能力模型的新發展
語用能力和互動能力的提出和相關研究的發展符合語言學的發展規律。韓禮德1978年提出的社會符號學(Social semiotic)認為語言的使用受到語境因素的影響,身份、地位、關系等社會因素制約語言使用,語言在社會互動中建構現實,語言與社會現實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語用能力和互動能力的提出與韓禮德的社會符號學這一論述相互照應。維果斯基的社會文化理論(Social culture theory)同樣指出人類習得語言并非靠模仿,而是置身于真實、自然、充滿意義的語境中,通過社會互動習得語言。盡管研究者反復嘗試對交際能力進行分解歸類,但語言的發展最終仍要回到語言交際的整體性本質。
語用學是關于語境中語言使用的研究,是交際者視角的關于語言選擇的研究,語用學研究交際者在社會互動中遵循的語法規則和社會文化規范,以及語言選擇對交際參與者的影響。同時,語用學并不認為交際中的語言是線性流淌的結構,而是強調交際中的不斷變化,適時調整適應,共同塑造意義的語言選擇。在語用學的概念中,“交際者”“語言使用”“語言選擇”“社會互動”等關鍵意義被反復強調,這些意義的發展與闡釋使得研究者逐漸將注意力轉向互動能力在交際中的作用和表現。
互動能力理論建立在語言能力和交際能力理論的基礎之上,Kramsch關于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的觀念認為說話人的互動能力預設了交際雙方共享的“內部語境主體間性”(internal context inter-subjectivity),交際成功的重要基礎在于建立主體間性。因此,建立主體間性是互動能力的重要指標,具體包含三個條件:聽話人理解說話人傳達的信息,說話人知道聽話人理解其傳達的信息,聽話人知道說話人知曉這一情況。
交際能力關注交際者個體在特定交際語境中的知識和技能,而互動能力由交際過程中的所有交際者共同建構,是全體交際者在交際語境中交互與作用的動態過程。
喬姆斯基的能力理論將語言劃分為語言能力和語用能力,從海姆斯、Canale和Swain,到Bachman和Palmer,眾多研究者試圖將交際能力進行分解并歸類,提出了交際能力的不同發展模式的諸多構念,后來的研究者對能力模型中的構成要素進行了詳盡的研究和驗證。
目前關于交際能力、語用能力以及互動能力的研究始終不能脫離語言交際的整體性本質。語言交際不是孤立的語言本身的交際,而是交際者在諸多社會因素、認知因素、情感因素共同作用的語境中依靠語言能力、語用能力、互動能力的整體性作用所推動的動態發展過程。對于外語教學實踐而言,在語言教學的同時,明確交際與互動的規律和目標,將語用與語法融合到教學與評價中,以交際整體觀指導外語教學,注重互動與互動的有效性,將是外語教學改革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新方向。
作者簡介:
張進,女,陜西富平人,副教授,馬來西亞沙巴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應用語言學,語用學。本文為2023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規劃基金項目“莫言研究學術史(1985—2023)”(項目號:23YJA751020)、2023年度西安外事學院校級研究課題“中外合作辦學教學管理機制優化路徑研究”(編號:23mjy12)的階段性成果。作者單位:西安外事學院國際合作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