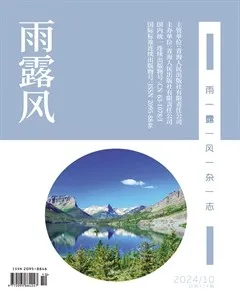論索南才讓小說中的生態倫理思想
索南才讓的小說以日常敘事消解異域牧歌風情、獨特民族文化等豐富內涵,展現草原上當代牧民細微的精神狀態與生活方式。他的小說大多以牧場生活為題材,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致使各種非人類生物物種不可避免地進入到作家的寫作場域之中,人和自然之間常常有著諸多或緊張或和諧的緊密關系。作者冷峻而克制的情感中蘊含著對人與自然、與非人類生命體之間的生態倫理的思考。
一、索南才讓小說中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
索南才讓曾經在采訪中表示:“如果一個作家對他的環境和他的時代漠不關心,他就不能夠深刻理解他的環境,不能夠感受到時代帶給他的影響力,那么他的創作就會陷入困境。所以,作家與他的時代應該是血肉相連的一種狀態。”[1]索南才讓所生活的青海湖北岸草原是一片生態環境脆弱的區域,面臨許多生態問題:氣候干旱、植被水源涵養能力差、風沙和鼠蟲等災害嚴重、土地沙漠化,等等。作為土生土長的青海人,索南才讓意識到隨著現代化的到來,生態危機正以超乎人類想象的速度繼續惡化,甚至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而生態問題的真正內在根源是現代性的文化危機”[2],索南才讓的小說在探尋生態危機的根源、表達生態倫理思想的同時,蘊含著對以人類中心主義為重要癥候的現代性文化危機思考。西方進入近代以后,現代人的主體性精神得到了高度的強調和彰顯,并不斷外化為人對自然的絕對控制和對物質利益的瘋狂攫取,加劇了生態危機的惡化。生態主義認為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人以征服自然、蹂躪自然的方式來證明自我、實現自我、弘揚自身價值的人類中心主義是必須拋棄的。
索南才讓的長篇小說《野色失痕》在動物視角下展現了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作者在慣常的人的視角外新增了牛的視角,巧妙地運用“人—牛”雙視角切換、對比敘事完成了獸性視角下對于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在公牛“妖”的眼中,人的形象不再是人們理所當然認為的“人”,而是一個有著“赤紅大臉盤”“蛤蟆似的眼睛”[3]且行為粗魯殘忍的“妖怪”,并且人還像扔垃圾一樣丟掉了給予“妖”安全感和溫暖的母親。“妖怪”牧民那仁克丟掉“妖”的母親只是因為那頭母牛流血太多,也已經老了,一句輕飄飄的“索性就撇棄了”[3]102和“妖”一生得不到溫暖和母愛的痛苦、迷茫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在那仁克看來稀松平常或有趣的行為舉動,例如用“烏朵兒”將石子砸到牛背上,調教牛群時的抽打等,在“妖”看來則是給牛們帶來了極大的苦楚。“妖”親身體會到年幼弱小時被人禁錮在筐子中轉場的折磨,清晰地觀察到同胞們挨打之后微微顫抖的身子和警惕、恐懼的狀態。索南才讓的“天才”之處就在于他擁有從生活里腌漬出來的活態的、天真的、透明的經驗。他憑借對動物習性的無數次觀察,使牛視角下的世界宛如在顯微鏡下那般纖毫畢現,從而有力地解構了人類視域,顛覆了人類視域下的價值判斷,實現了“萬物視域”下對自然價值的本質肯定和對生命價值的重估。此外,小說還借助叔叔尕巴斯這一諄諄教導的旁觀者之口,說明人類在自然面前妄自尊大的荒誕性。尕巴斯將人與萬物的關系比作五臟六腑:“所謂等級,就和內臟一樣,不管是心還是肺,是肝還是脾,都是在腔內,難道說有哪個會跑到外面去?”[3] 26-27尕巴斯用非常清晰易懂的比喻闡明了作者想要表達的“物無貴賤”的反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在萬物視域下,個體呈現出不同價值,因而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下之分,亦不存在絕對唯一的價值判斷。生態倫理是判斷人與自然、人與非人類生物之間關系的道德尺度和坐標。在這篇小說中,索南才讓一如往常地運用動物視角控訴動物生命遭到人類忽視、拋棄或管控等不平等對待的現象,從而使整篇小說帶有濃厚的生態倫理底色。
二、索南才讓小說中生態倫理精神的構建
索南才讓的小說雖然有些是在描寫自然和非人類生物的工具性價值,但也有相當多的篇目將自然和非人類納入倫理關懷對象,他將其視為具有審美的主體,或敬畏的對象,或具備情感和智慧的生靈,打造出一個充滿贊天地之化育、超一己之得失的生態倫理精神的世界。
索南才讓的小說具體地感受和表現了自然及非人類生物本身自足的審美性。
在自然環境方面,小說通過對天空、草原、河流、星空等景觀進行不同層面的描述,展示了一個具有粗糲質感、原始風味的美麗荒原。在《我是一個牧馬人》中,作者從視覺和聽覺上寫出了一個寂靜又和諧的草原,藍的天空、墨綠的灌木、潔凈的月亮、嗚嗚的風、悠遠的草原、大片的星星,組合成了一個色彩繽紛絢爛、聲音悅耳柔和、空間層次豐富的場域。在《原原本本》中,草原在悠長的歲月中獨自美麗數千年,不因人的來去而黯然失色。自然風景獨立的審美主體性不是人的內在精神或本質力量的外化,而是風景意義之本身。同時,自然與人類形成了一個互相參與的審美系統,人物在把自己作為自然的一部分,全然開放感官,參與到自然中,在自然中放空自我,在凝神靜觀中感受人與自然的和諧美。
在非人類生物方面,小說通過對動物的身體描寫,展現其審美自足性,表達動物的自身內在價值。在《在辛哈那登》中,對于馬“戰士”的身體描寫十分細膩、翔實,迎風飄動的鬃毛、細碎波浪般卷曲的尾巴以及旺盛的汗水,讓主人公感到陽光下的馬兒是如此神秘和動人心扉。馬的身體是自然界塑造的完美形體,其散發的熱烈生命氣息讓主人公如癡如醉,不住地贊賞。在《我是一個牧馬人》中,“我”目睹了母馬分娩艱難、痛苦的全過程,看見了動物母性的光輝。主人公為身材高大而渾身火紅的漂亮小馬駒起名為“塔合勒”,以此延續他對另一匹母馬的日夜思念。在《和一頭牛共進晚餐》中,母牛毛發和肉體散發出的生命力仿佛可以傳遞,明亮而空靈的眼睛似乎能夠將整個地球裝進去。動物的身體是人與其交往的重要媒介,小說中動物身體的被“看見”,是其生命個體價值、權力等被發現的前提。在被“看見”的基礎上,動物的審美主體性由此確立,尊重的生態倫理精神也就成為被建構起來之一維。
索南才讓的小說展現了人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人在廣闊無垠的自然空間和以斗轉星移為刻度、循環往復的自然時間中認識到了自然的獰厲和人的脆弱,從而對自然產生了崇高感和敬畏之心。在《山之間》中,九成和海春行走在茫茫無邊的荒原中,海春一直觀察著晴朗、下雨、高溫、低溫等天氣變化并為此感到擔憂。太陽落山后,海春面對混沌的天地感到恐懼:“走出去,站在星空下,四下里無沿無際,海春感到自己越來越小,最后變成一粒沙粒”[4]186。第二天,二人終于在高溫、缺水與體力耗盡的情形下殞命戈壁,海春帶著死去的九成回到石屋等待死亡,在浩瀚無邊、寂靜無人的戈壁面前,荒原自身的寂靜、荒蕪和蒼涼是一種對生存的威脅,它使人產生驚惶、恐懼和痛苦的感覺。“沒有邊界的空間意味著絕望而非機會,它抑制活動而非鼓勵活動,它證明了人類在應對大自然的浩瀚無際和冷漠無情方面是無能為力的。”[5]康德認為崇高是出于人們出于對“自身保存”的潛意識,面對自然界本身具備的巨大的能量和形體,人類產生了恐怖的感覺,因而在心靈中生發出一種理性的力量與這種恐懼抗衡,在此過程中產生了一種尊敬之情。海春在與自然的時空抗衡中多次感到可怖不安,甚至有時無法用語言來表達心中的恐懼,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對自然的敬畏之心。在《接下來干什么》中,人對于自然敬畏的態度則趨向于一種宗教信仰。在席卷荒原的自然災害之中,牧民的羊羔死了個精光,但牧民卻認為這是來自“老天爺”的怒火,人不能責怪上天,“因為老天爺做什么事都是有道理的。他當然也不能責怪牲畜,因為它們自始至終都是沒有發言權的”[4]135。作者在民間話語中找到了自然的神性,構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生態倫理立場,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現代人對自然敬畏之心的缺失。
索南才讓的小說體現了對非人類生物情感、智慧的關注。索南才讓的小說在描寫人與人之間輕賤淺薄的情感時筆調冷峻疏離,然而當寫到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時,語言畫面就變得溫暖和諧。主人公們不僅視這些動物為伙伴、朋友、助手,甚至是值得尊敬的對手、救命恩人,更重要的是主人公們對它們的生存權利、悲歡情緒給予肯定和感同身受,這實際上已經是在嘗試跳出人類中心主義。《在辛哈那登》中,當“我”找到撞死阿媽的公牛復仇時,雙方展開了一場人獸之間激烈的尊嚴之戰,“我最后一次在它眼里看見了原本就屬于它們這個群體的傳統,之后,將永久地消失”[4]16。“原本就屬于”包含著“我”對牛的尊嚴、勇敢、無畏的肯定情感,然而對“我”而言,為母報仇則是人之為人的尊嚴,即使公牛有活著的權利,而“我”不得不殺死它。雙方之間即使處于一種敵對的狀態,但是二者是以平等的姿態站上擂臺的,“我”對公牛既不蔑視也不輕視,肯定它戰斗的理由,這是一種承認的尊重。在《和一頭牛共進晚餐》中,“我”為母牛救自己一命的行為感到十分不可思議和興奮,并決心請這頭牛吃一頓“盛宴”。這篇簡短的小說氛圍十分輕松幽默,在人與牛的言語對話和肢體行為的描寫中,充滿了作者對于動物靈性和智慧的贊賞和肯定。
概而言之,索南才讓小說多在與自然的“交流”“對話”中把握人與自然共生共存的澄明意義,具體表現為,通過展現自然及動物的審美自足性、人對自然的敬畏之心、人對動物的情感和智慧的關注等多個維度,構建以平等、尊重、敬畏等為外顯的生態倫理精神。
三、個人經驗下生態倫理思想的產生
對于索南才讓而言,他既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牧民。在雙重社會身份中,其小說中表現出的生態倫理思想是極其矛盾的:一方面,主人公們熱愛荒原自然美、動物身體美,對動物情感、生命有關注和尊重,對自然和非人類物種持有鮮明的平等、尊重的生態倫理精神;另一方面,主人公們的命運又與荒原的事物纏繞在一起,存在不可避免的生態倫理沖突。
小說中存在搖擺不定的生態倫理立場,一部分原因可能來自于索南才讓“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6]。在這種敘事模式下,索南才讓對生活有著多層面和多樣性的理解。索南才讓曾經在采訪中說:“那么真正的自然文學是什么呢?它代表的是自然對人類的反饋嗎?是詰問嗎?我想是這樣也不是這樣。答案在作家心里,每一部誠實的自然文學作品,就是最好的回答。”[7]索南才讓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講的都是絕然個人的生命故事,融入了個人的生命奇想和深度情感,他寫小說并不是為了生態倫理說教,而是以一名牧民的身份誠實書寫對生活和個體生命的感受。“荒原上”的文學空間之原型是現實中非虛構的青海牧場,生活在牧場上的新一代青年牧民在真實世界里既是生態區的保護者,同時也會陷入生活多維的關系網,他們不光與自然、非人類生命之間有關聯,更有個體生命的思考,包括對于未來的迷茫,對生活的無意義感等。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荒原牧民們的生命是多面性的,無論什么時代,生命之間都充滿互相排斥和矛盾。即使在生態時代下,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也是無可避免的。
索南才讓生態倫理立場中堅定的部分與作家個人生活經歷有關,他小說中的生態倫理立場是其特有的思維模式與民族精神的表現,是特有的地理環境的產物。索南才讓出生于青海省托勒草原海晏縣境內一個純牧業村莊,十二歲輟學,和許多年齡相仿的男孩子一樣開始了放牧生活。青海湖的碧波蕩漾和草原的荒涼枯寂是他少年時期的風景記憶,獨特的自然地理空間極大地影響了索南才讓對于人與自然環境、人與非人類生命體之間關系的體悟。在與自然風光和動物的親密相處中,索南才讓有一種人和自然彼此守護、照料的責任意識。小說對人與風景融為一體、人與動物惺惺相惜的描寫如此真切、真實,端賴作家在青海原鄉中汲取的豐富生動的、粗糲真實的一切元素之呈現。
四、結語
索南才讓的小說不乏生活原生的質感和粗糲的肌理,作者在展現自然空間及動物的審美性和人對非人類生命體所持的平等尊重態度時,蘊含著生態整體主義的態度,這表明索南才讓已經具有較為自覺的生態倫理立場。但與阿來、劉亮程等作家相比,索南才讓小說中的生態倫理精神仍然處在一個分散且不穩定的狀態,“生態敘事在他小說中基本處于輔助性線索的地位,似乎還沒有突出的生態敘事聚焦意識。他對藏族、蒙古族的生態倫理似乎也缺乏較為系統的關注,對青藏高原的生態危機缺乏全局性思考”[8]。不過,這也正是索南才讓小說的特色,他用在青海的直接、新鮮的經驗向我們展現了一個具有更多敘述可能性、更多復雜情感的現代荒原。
作者簡介:劉甜擔(2000—),女,漢族,山東棗莊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注釋:
〔1〕周詩浩.索南才讓:作家與他的時代應該是血肉相連的狀態[EB/OL].(2022-11-19)[2024-09-20].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2/1119/c405057-32569923.html.
〔2〕雷鳴.危機尋根:現代性反思的潛性主調[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09.
〔3〕索南才讓.野色失痕[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4〕索南才讓. 荒原上[M]. 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
〔5〕段義孚.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M].王志標,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6〕劉小楓. 沉重的肉身[M]. 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
〔7〕何蘭生.索南才讓:我用牧鞭寫人生[EB/OL]. (2023-08-09)[2024-09-21].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24166871.
〔8〕歐陽瀾.邊地小說的生活美學與生態敘事——評索南才讓中短篇小說集《荒原上》[J].阿來研究,2023(1):22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