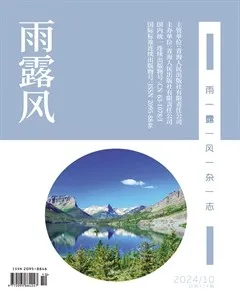論海明威小說的對話藝術:真實
海明威創作小說的重要原則——真實。他的小說去繁就簡,將一切可能遮蔽真實表達的累贅成分切除,把對生活最準確的觀察和最真實的感受注入由每一個字詞融合而成的場域中。尤其是他小說中的對話藝術,讀來如身臨其境,對話真實而有藝術感染力。
一、對話中置身其中的場景感
直接引語“被認為是人物說出來的話的本來面目”[1],使得讀者閱讀時往往忘記敘事者的存在,能夠感受到一個故事的真實。
小說以單刀直入的對話展開,使讀者快速進入真實的對話場景中。但由于海明威在此之前沒有對人物和事件作一個簡要介紹,同時直接引語的運用也避免了作者情感的介入對文本客觀性和真實性產生的影響,所以讀者在閱讀對話時,容易產生疑惑。隨著對話的深入,事件的輪廓逐漸顯露出來。這種在對話前不作任何解釋并采用直接引語的形式,更貼近現實生活中偷聽別人的對話,對話雙方沒有意識到旁聽者的存在,能毫無顧忌地進行真實自然的交談,而旁聽者也就是讀者將會體驗到置身其中的場景感。
如《乞力馬扎羅的雪》開篇以對話展開:
“奇怪的是一點都不痛,”他說,“你知道,你這才知道它發作了。”
“真是這樣嗎?”
“千真萬確。可我感到非常抱歉,這股氣味準叫你受不了啦。”[2]
究竟什么疾病發作“一點也不痛”,為什么又會有奇怪的味道,讀者不得而知,對話的二人當然不會向一個偷聽對話的人解釋,作者將生活場景還原,謎底藏在后續對話中,引導讀者細細揣摩。
隨著對話不斷推進,讀者的疑惑一一被解開,故事的男主人公哈里在狩獵途中,腿被劃破后感染,染上壞疽。這也就解釋了開頭對話出現的原因,在傾聽對話過程中,一個真實的故事層層展開。
除此之外,在沒有背景信息的前提下,直接引語的對話形式也讓讀者仿佛親臨現場,根據對話的態度語氣來判斷人物關系。
“人物對話是直接引語中最常見的形式,它直接展現了人物之間的種種關系:親昵、敵視、論爭、譏諷等。”[3]
如在《五萬元》開頭:
“你的情況怎么樣,杰克?”我問他。
“你看到過那個沃爾科特嗎?”他說。
“只是在健身房里。”
“唔,”杰克說,“跟那個小伙子較量,我需要好運氣。”
“他不能打敗你,杰克。”士兵說。
“我多希望他不能啊。”[2]
小說的開頭沒有故事背景和人物關系的交代,直接以對話的形式切入。再聯系題目《五萬元》和對話內容,似乎沒有什么直接關聯,對話以詢問的口氣開始,逐步將“杰克”“沃爾科特”“我”“士兵”一系列重要人物引出,人物之間的關系也在對話中浮出水面。“我”“杰克”“士兵”處于同一戰線,“沃爾科特”是他們共同的敵人,這些信息通過簡潔的對話展露出來,讓讀者在對話中直觀準確地了解人物個性并把握人物關系,且不受背景信息的影響。
小說以直接引語對話開頭的形式講述故事,能讓讀者在閱讀中達到一種現場觀看戲劇的效果,在傾聽對話中拋開修飾的外衣,真實地感受到人物的語氣態度,探索人物關系,沉浸式感受故事。
二、對話中刻畫真實的人物形象
“真實感來源于‘純粹’,要達到純粹,關鍵在于消除先入為主的‘應該’和‘想當然’。如果一個人不相信別人的話,又想在美學上達到勒內·笛卡爾想在哲學上達到的高度,即追求最基礎、最原始的認知起點,那么,‘應該’和‘想當然’就成了危險的立足點。”[4]海明威在對話中克制自己情感的外露,基于自己對生活的細致觀察來刻畫故事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不會“想當然”地安排人物對話作為“傳聲筒”,而是通過對話把人物最真實、最自然的一面展現出來。
如《弗朗西斯·麥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故事講述的是一位名叫羅伯特·威爾遜的狩獵向導引領弗朗西斯·麥康伯及其夫人瑪戈在非洲叢林進行狩獵之旅。
每個人物的話語代入角色中,沒有絲毫違和感。麥伯康作為“精通場地球類運動,在不少次釣大魚的比賽中創過紀錄”的美國富人,有著很強的自尊心,所以第一次捕獵顯露出的膽怯讓他覺得顏面盡失,他對威爾遜說:“我對那獅子的事非常難受。不該把它擴散出去,是不?”他希望在獅子面前臨陣脫逃這件事情能夠爛在威爾遜的肚子里,與此同時希望再次有機會向妻子證明自己的實力,從“我們明天要為你另外表演一場”就能感受到他急切想要獲得認可,挽回自己在妻子瑪戈心中的男性形象。但是他的妻子瑪戈剛開始還為“他和她感到痛心”,可是過了二十分鐘,妻子又表現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干嗎不高興?我不是到這兒來找煩悶的啊”。其實此時麥伯康在妻子心中男性偉岸的形象早已崩塌。
對于瑪戈來說,她與麥伯康的結合是金錢與美色的各取所需,“他們有健全的結合基礎。瑪戈長得太漂亮,麥伯康舍不得同她離婚,而麥伯康太有錢了,瑪戈也不愿意離開他”。除此之外,他們沒有深層次的情感鏈接,所以當麥伯康身上軟弱的氣質被妻子發覺后,妻子沒有選擇包容他,而是表現出對他的鄙夷,并且對丈夫發出攻擊——“你是個膽小鬼”。麥伯康作為瑪戈的丈夫,面對妻子的出軌,沒有撕心裂肺的憤怒,他們之間的對話也證實了他們的婚姻更像是一場各取所需的交易。
對話的內容完全符合人物心理與其生存狀態,真實自然的對話使得整個角色鮮活起來。對男性氣質崇拜卻又不能放棄金錢誘惑的瑪戈,膽小但又想證明自己的麥伯康,在他們身上可以感受到人之為人的隱曲,并能夠理解他們的言行,在對話中感受一個真實的人物角色。
三、對話中揭示真實的情感
(一)在重復中揭示真實的情感
海明威對話中重復的形式顯化了人物深層次的真實意識活動。“美國學者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的《小說與重復》對重復理論進行深入研究,他把重復總結歸納為三大類:第一類為細小處的重復,如語詞、修辭格、外形或內在情態的描繪等方面的重復;第二類為較大處的重復,即一部作品中相同或相似的事件和場景的重復出現;第三類的著眼更大,指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中人物、主題和事件的重復,這種重復超越了單個的文本界限。”[5]《橋邊的老人》則是第一類中的“細小處的重復”。小說中戰火即將蔓延至橋邊,老人和“我”展開的對話全程圍繞動物展開,老人在自己性命不保的情況下,擔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他養的小動物。
“沒家,”老人說,“只有剛才講過的那些動物。貓,當然不要緊。貓會照顧自己的,可是,另外幾只東西怎么辦呢?我簡直不敢想。”[2]
“可是”“怎么辦”“不敢想”這類詞語的重復以及由此組成的句子在這篇短短的小說中出現三次,充分展現了這幾只動物是老人在戰爭中唯一的牽掛,然而趕上動亂必須與動物分別的他在“我”“怎么辦呢?”的重復中陷入對動物們安危的深深憂慮中。從大的時代背景看,西班牙內戰爆發,人類自身命運陷入危機,動物的生命安危早已被人們置之度外。人類關注的是戰爭的勝利或失敗,權力的爭奪與交接。而在這位老人的世界中,“政治與我不相關”,在他的價值體系中,戰爭、權力、政治從來不是衡量一件事情是否重要的尺度,反而那幾只動物是他內心深處的精神寄托。
在小說結尾,老人木然重復著“那是我在照看動物”而沒有一個確定的傾訴對象,他和《祝福》中的祥林嫂“我真傻,真的”一樣,在絕望中發出自己的哀號,祥林嫂在向魯鎮的人傾訴自己痛苦經歷時卻淪為人們的談資,麻木的看客無法共情祥林嫂的痛苦,全文中祥林嫂一共說了4次“我真傻,真的”,從最初的尋求安慰到麻木訴說再到最后的失語,祥林嫂一步步走向絕望,墜入死亡的深淵。老人和祥林嫂一樣在重復性的訴說中傾吐自己的痛苦與無奈,向世界發出求救,無奈的是他們都處于社會的底層,多次的呼喚與求救也泛不起半點漣漪,與之而來的是夢的破碎。
海明威的語言以簡潔著稱,重復的話語必定透露出作者的創作意圖和價值判斷。 “他從民主主義的立場出發,在作品中妥善處理個人與全局、愛情與責任之間的矛盾。”[6]大環境的戰爭與個人對和平的渴求之間的矛盾之下,老人只能無力重復自己的需求,海明威對此也深表同情。海明威在對話的重復中揭示人物內心的真實情感并展現自己價值觀,這也是他真實創作原則的展現。
(二)在省略中體味真實的情感
海明威提出:“角色說的話要具備作家所強調的抑揚頓挫、風味、情緒、含意。”[6]對話的描寫中,海明威舍棄了對人物情感的渲染,把人物的情感、態度隱藏在富有暗示性話語的冰山之下。所以理解海明威筆下文本對話需要高度的敏銳和反復地閱讀,如此才能揭開人物平靜對話的面紗,體會暗流涌動的情感變化。
在《白象似的群山》中,整部小說基本上由姑娘和男人的對話構成,對話的內容以墮胎為線索來展現二人對于要不要墮胎問題的心理斗爭。表面上看是男女主人公針對酒的味道展開討論,但是在細讀過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二人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且都有著各自的小情緒。姑娘說酒的味道“甜絲絲的就像甘草”,而接下來男主人公試圖將這一話題轉移到墮胎上,“樣樣東西都如此”,其實真正想說的是墮胎也會像這酒的味道甜絲絲的。姑娘對此所暗含的深意心知肚明,她的回答前半部分看似是贊同男人的看法,但是后面姑娘話鋒一轉,又換了一種比喻,“簡直就像艾酒一樣”,艾酒是一種苦酒,這與前面“甜絲絲的像甘草”相矛盾,表明她對男人發言的諷刺以及不滿。而男人這時候也聽出她的言外之意,但他不知如何扭轉姑娘的心意,惱羞成怒,只得讓姑娘“喔,別說了”,后面男人勸說無效只好順著女人的話說下去:“好吧,咱們就想法開心開心吧。”可以看出男人的妥協是無奈的。在這一回合的對話中,男女主在深度交流的過程中,這些情緒變化都被隱藏起來,冰山之下的世界才是作者真正想要向讀者表達的東西。
在與契訶夫小說《變色龍》中人物對話的對比之下,這種風格更加凸顯。
《變色龍》中人物的對話主要圍繞“狗是誰家的”進行,人物對話情感充沛,情緒起伏明顯,沒有太多暗含性語言,從對話中能直接了解人物的性格。
文中奧楚蔑洛夫對狗的辱罵中“竟敢”“該死”“不要”“不許”這類帶有主觀情緒的詞語充斥在對話中,人物的憤怒情緒溢于言表,而且在對話中提示語“膽怯地問道”“擠進了人群問道”將人物的神態動作也呈現出來,使得對話傳遞的信息更加豐滿,使讀者在理解人物話語的內涵上有更多的抓手,將巡警的膽小怕事、民眾的愛湊熱鬧天性展現得一覽無余。此外在標點符號上,契訶夫多次連用“!”“?”這樣帶有明顯情緒的標點符號,更能讓讀者直觀地感受到人物強烈的情緒變化,而正是這種直白、態度鮮明的對話讓奧楚蔑洛夫“變色龍”形象在反轉中更加鮮明深刻,使得作品富有喜劇色彩。
相比于《白象似的群山》,在標點符號上,《變色龍》“?”“!”的大量連用與《白象似的群山》“,”“。”的謹慎使用形成對話場域“熱”與“冷”的鮮明對比,在海明威平淡的語句下,人物情緒也被隱藏在每個字詞中間。二者都運用直接引語,“直接引語中的人物對話:一種是交流型,即通過閑聊、辯論等方式達到人物之間的互相了解和對故事、對世界的逐步認識。這種對話的言辭大都具有明確的含義,人物在對話中獲得共識。另一種為含混型,即人物的話語中包含著多重意義或可作各種各樣的理解,人物在對話中未達到真正的交流。”[3]顯然《變色龍》的對話屬于“交流型”,《白象似的群山》屬于后者,屬于“含混型”的對話,二人的對話富有暗示性,在表層討論的對象只是一個指代,真正內心的交流與復雜的情緒交織在表層的討論之下等待發掘,實際上是將人物內心的波瀾壯闊深藏于平靜的水面之下,如同冰山一角,只展現出一小部分,而更大的部分則隱匿在水下,留給讀者無限的想象空間。
綜上,在海明威的小說中,對話不僅是故事的載體,更是真實性的堅守者。他巧妙地運用對話這一形式,讓故事自然而然地流淌而出,每一句對白都經過精心雕琢,既保留了生活的原汁原味,又蘊含著作者深刻的用意。這種分寸感的把握,使得對話不僅傳達了表面的信息,更在字里行間透露出人物的性格、情感和動機。讀者在品味這些對話時,仿佛能夠穿越紙背,窺見角色內心深處,了解人物的真實意圖和情感。
作者簡介:余增艷(2002—),女,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學科語文。
注釋:
〔1〕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 新敘事話語[M].王文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2〕海明威.海明威短篇小說全集(上)[M].陳良廷,蔡慧,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3〕胡亞敏.敘事學[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4〕楊敬仁.海明威研究文集[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5〕米勒.小說與重復[M].王宏圖,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6〕董衡巽.海明威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