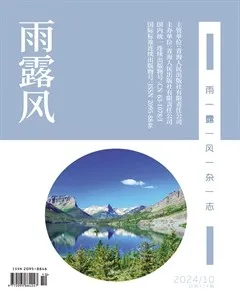張愛玲小說藝術語言創造的感性外觀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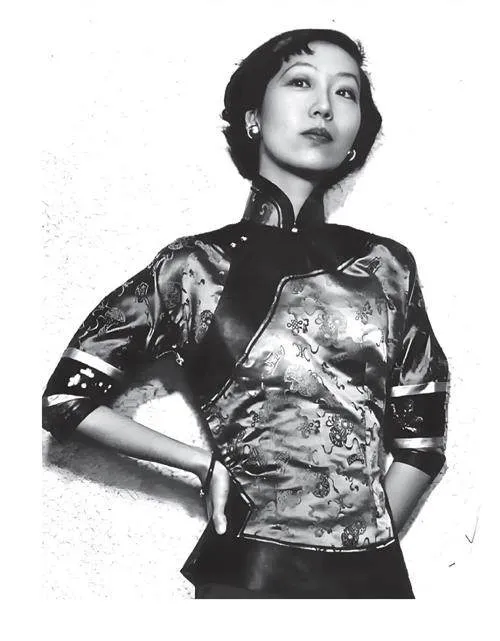
意象是一種物象形態,具有隱喻、象征等作用。張愛玲在文學作品創作中,有意識地運用意象技巧,豐富了作品內涵,并呈現出凄艷、蒼涼、流動的視覺效果,使人物形象、情感的刻畫更加細膩。本文在概述張愛玲小說的基礎上,從具有色彩感的“凄艷”意象、構建雕塑感的“蒼涼”意象和形成工筆圖式“流動”意象三個方面,對張愛玲小說藝術語言創造的感性外觀進行詳細分析。
張愛玲小說作品情感細膩、形象鮮明、語言優美,通過細致化描寫,充分展現了人物內心的掙扎和情感的復雜性。她運用藝術語言創造了感性外觀意象,精細、精準刻畫了人物的內心世界,展現了獨特的文學魅力。據此,本文以張愛玲小說藝術語言創造的視角,對感性外觀意象進行深入探討。
一、張愛玲小說概述
張愛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其小說因獨特的風格和深刻的主題而廣受贊譽。她的小說大多圍繞愛情、婚姻以及女性在男權社會中的生存困境展開,尤其是女性角色在這些關系中的心理變化和悲劇命運。[1]張愛玲的代表作包括《沉香屑·第一爐香》《茉莉香片》《紅玫瑰與白玫瑰》《金鎖記》《傾城之戀》《半生緣》《小團圓》以及作品集《傳奇》等。
張愛玲的小說中,意象豐富多樣,如月亮、鏡子、電車等,傳達特定的情感和主題。她善于借鑒電影、戲劇、繪畫等藝術手段,結合色彩、雕塑感的空間布局以及工筆圖式的藝術語言,巧妙地將傳統與現代、通俗與高雅融為一體,充分調動了色彩、聲音、味覺、觸覺、聽覺等感官印象,創造出既華麗又細膩的意象,在帶給讀者難以磨滅的意象感受的同時,反映出張愛玲對人情世故的洞察以及對都市生活方式和人物關系的感受。
二、張愛玲小說藝術語言創造感性外觀意象
(一)具有色彩感的“凄艷”意象
張愛玲對色彩有著獨特的敏感與偏愛,她認為顏色能夠賦予世界更真實的質感。在張愛玲的筆下,色彩不僅是背景與裝飾,更是表達人物內心世界的重要手段。她通過強烈的色彩對比、色彩與意象之間的密切關系,創造了具有色彩感的“凄艷”意象,增強了小說的視覺沖擊力,加深了讀者對人物命運的理解,并構筑了張愛玲筆下的“荒涼之城”,道盡了世界的愛與死、色與空、真與假。
1.運用雜色創設不和諧的圖景意象
雜色的運用,使意象更加具體、細致與形象,襯托出人物的內心情感、思想意識等。在《傾城之戀》中,“輕纖的褐色剪影”“是紅的么?”“把紫藍的天也熏紅了”等油畫般的色彩描繪,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斕卻“不和諧”的香港風景圖,映射出小說中主人公之間的愛情的“不和諧”,他們彼此的內心世界猶如濃重不和諧的色彩在時刻進行較量[2]。
2.運用色彩對比創設返場對抗意象
色彩的強烈對比,增強了作品的視覺沖擊力,鮮活地呈現了意象,同時揭示了主人公內心世界與社會環境的復雜性。在《金鎖記》中,“把那大鑲大滾的藍夏布衫袖高高挽起,專門露出那一雙雪白的手腕”的描寫,通過藍與白的對比,充分表現出曹七巧內心的悲哀和壓抑。[3]此外,張愛玲還巧妙地運用了參差對照法,如“蔥綠配桃紅”的錯落色彩對照,引導讀者對復雜的人性進行深度解讀。
3.運用色彩堆砌創設虛假繁花意象
色彩的堆砌,創設出了繁花意象、顏色絢麗的意象,使讀者能夠在閱讀過程中產生強烈的視覺與心理體驗。在《傾城之戀》中,張愛玲描繪了紅色的影樹、野杜鵑等意象,以及渡輪上的白流蘇,展現出一種狂熱的意象感受。再如《第一爐香》中,張愛玲運用紅色、橘色、粉紅等大塊顏色,堆砌了大紅大綠的意象,使讀者能夠直觀地感受到社會環境的復雜性與人物命運的無奈。
(二)構建雕塑感的“蒼涼”意象
張愛玲曾表示,她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張愛玲的“蒼涼美學”觀來源于其個人身世背景和其對社會的觀察。在張愛玲的小說中,蒼涼作為一種基本腔調與主題旋律,籠罩每個人物,并給定每個人物以獨特的人生圖景,以立體化、雕塑式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同時,張愛玲將“蒼涼”滲透在細節處理上,勾畫出新舊對撞、高低錯落的意象,并展現出張愛玲與現代性的一種深層次的無法厘清的“曖昧”關系。
1.市井中的生命意象
張愛玲的文學創作受到其個人經歷、時代背景的影響,以獨特的視角觀察和描繪了都市小人物及其生存狀態,構建出一種充滿蒼涼美感的意象。在描繪人物時,張愛玲通過對日常生活的觀察,捕捉人物的生存境遇、情感流動,以“蒼涼”的真實性描寫人物,使得其作品具有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及強烈的現代感。張愛玲善于應用月亮、鏡子等具有凄涼、孤寂等特定含義的意象,展現市井人物的悲慘與蒼涼。張愛玲的《金鎖記》以“月亮”開始,以“月亮”終,在人物命運的重要關頭,月亮意象均會出現。[4]如“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凄涼”。同時,張愛玲應用“無生命”意象,體現人物的悲慘命運,如“酸梅湯沿著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玄色花繡鞋與白絲襪”等,通過具體的“無生命”意象,展現出人物的心理狀態的悲涼。另外,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描繪了遺老家庭的窘境,這些家庭在末路窮途的生活中,表現出一種市井寒人的態度,平視對象,寫出了他們那種末路窮途的窘境,不僅反映了市井小人物的生活狀態,也映射出一種蒼涼的人生觀。
2.都市中的奢華意象
張愛玲善于應用豐富的象征意象和色彩語言,通過細膩的描寫和修辭手法,構建出一個充滿詩意的都市世界。在《傾城之戀》中,白流蘇與范柳原在香港到處游玩,但在游玩過程中兩人各懷心事,鉤心斗角。當范柳原去英國,白流蘇一個人在空蕩蕩的房間內,心也空了。而“空房子”意象正是給讀者最為震撼的雕塑感“蒼涼”意象。[5]在《半生緣》中,張愛玲運用全知全能的敘述視角,在描繪中滲透了自身的人生感悟。通過曼璐嫁給祝鴻才的豪華住宅描寫和曼璐悲劇下場的描繪,使其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構建出具有雕塑感的“蒼涼”意象,使讀者感受到人物生活中的滿目瘡痍。在《第一爐香》中,女主人公眼中的中國香港灣仔市場,盡管人頭攢動,卻給人一種奇異的蒼涼感;葛薇龍作為一個來自上海的女學生,初到中國香港時對奢華的生活感到陌生和不適應,但很快就被這種生活吸引,甚至沉迷其中。這種奢華的生活環境,如梁太太府邸中的布置,象征著一種亦洋亦舊、非中非西的復雜文化背景,這種背景下的奢華生活實際上是一種虛幻的表象,背后隱藏著無邊的荒涼和恐怖。[6]
3.迫不及待求生意象
“蒼涼”的意象構建是一個復雜、深刻的過程,不僅是一種情感表達,更是一種藝術手法的運用。張愛玲通過細膩的筆觸和豐富的意象,將“蒼涼”之感融入作品中。在《金鎖記》中,金鎖作為女主角,她的名字本身就象征著被束縛的狀態。她的裹小腳不僅是一種身體上的痛苦,更是一種社會對女性身體的控制和限制。裹小腳使得金鎖無法自由行動,也使她在家庭和社會中處于被動地位。同時,裹小腳也象征著傳統觀念對女性美的定義和審美的扭曲,使得女性為了迎合社會的期待而自我壓抑。[7]然而,金鎖和裹小腳不僅是物質上的束縛,更是人物內心不滿的象征。金鎖渴望自由和獨立,她對自己的命運感到不滿,并試圖通過與外界的交往和追求個人的夢想來尋找內心的自由。再如,在《半生緣》中,張愛玲通過細膩的心理描寫和生動的場景刻畫,展現了人物在復雜社會關系中的掙扎和求生欲望。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常常身處于家庭和婚姻的壓力之下,她們在追求個人幸福和自我認同的同時,也要面對社會對女性角色的期待和限制。她們的內心掙扎和求生欲望在作品中得到了生動的展現,使讀者能夠深入感受到她們的痛苦和無奈。
(三)形成工筆圖式“流動”意象
張愛玲注重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因此她對細節極為關注,對都市文化有獨特的理解,并能夠對人物命運進行細致描繪,對時間與空間進行創新處理,進而形成了工筆圖式“流動”意象。
1.白描人物身世
張愛玲善于運用意象化的手法處理抽象的東西,如人物的命運、心理、情緒、感覺等,給小說帶來濃郁的詩意。在《小團圓》中,張愛玲在意象的創構中夾雜與流動的個人情結,直觀人生的傷痛過往,盡管呈現于文本形式與結構中的表達方式不盡如人意,但在并不溫暖的回憶中努力尋求那點熱情的生命姿態,已經是一種圓滿[8]。因此,張愛玲的作品中,工筆圖式“流動”意象的形成,是她對人物身世的白描,以及對都市文化、實物細節、個人情結的深刻理解和運用的結果。
2.細描動態心緒
在小說創作中,張愛玲善于運用意象來渲染氣氛、烘托人物心境,并通過這些意象隱喻、象征和暗示人物命運。同時,張愛玲對細節的描寫極為細膩,將傳統文人意境與現代人潛在的意識流動融合在一起,以意象的連接方式展現動態心緒。在《傾城之戀》中,“白流蘇搖搖晃晃地走到了隔壁的屋里去”這一流動式的動態描寫,不僅展現了人物的行動,還反映了她內心的波動和情感的流動。同時,張愛玲通過“墻”這個喻體,暗示了人物心情的變化,表達了白流蘇對范柳原的失望和內心的墮落[9]。這些意象的運用,豐富了小說的層次,加深了讀者對人物心理的理解。
3.捕捉行為入畫
張愛玲在各類人物身上看到了“荒涼”的世界。通過人物行為描寫,使人物的情感更具有直觀性、隱喻性、氛圍性,進而傳達出人物的思想、情感、命運、心理等。在捕捉行為入畫中,張愛玲將抽象的概念具象化為流動的“畫面”,使讀者能夠感受到人物內心的變化和情感波動。《金鎖記》中,“玳珍探出頭來”“眾人連忙扯扯衣襟,摸摸鬢腳”“七巧直挺挺地站了起來,兩手扶著桌子,垂著眼皮,臉龐的下半部抖得像嘴里含著滾燙的蠟燭油似的”,這些行為的細致化捕捉和描寫,揭露了人物的無意識動作和潛意識心理,構建出了鮮明的人物意象和形象,增強了小說的藝術表現力,使讀者能夠更直觀地感受到人物的情感和命運。
三、結語
張愛玲小說中的藝術語言創造了豐富的感性外觀意象,通過具有色彩感的“凄艷”意象、構建雕塑感的“蒼涼”意象和形成工筆圖式“流動”意象,進而將讀者帶入了一個獨特的文學世界。同時,這些感性外觀意象的應用,不僅豐富了作品的藝術效果,也深刻地揭示了人物情感的復雜性和內心的掙扎。因此,張愛玲的藝術語言創造為她的作品增添了獨特的魅力,使讀者沉浸其中,感受其中蘊含的情感和美感。
作者簡介:李雯芮(2000—),女,回族,新疆喀什人,碩士,研究方向為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
注釋:
〔1〕王添棋. 論張愛玲散文作品中的比喻藝術[J].青年文學家,2024(17):151-153.
〔2〕李湘云. 都市敘述空間與人物生存的書寫——張愛玲《傾城之戀》和王安憶《長恨歌》比較[J].青年文學家,2023(9): 106-108.
〔3〕楊文斌. 探究張愛玲《金鎖記》中審美意象的功能[J].文化學刊,2024(6): 107-110.
〔4〕魏思劼. 談《金鎖記》月亮意象的悲劇意義[J].中華活頁文選(教師版),2022(4): 15-17.
〔5〕常廣遠. 淺析《傾城之戀》所體現的人生“飛揚”與“安穩”中的悲涼[J].名作欣賞,2023(9):127-129.
〔6〕劉立娟. 意象與張愛玲《第一爐香》的敘事藝術[J].作家天地,2024(8):16-18.
〔7〕王志鵬. 淺析張愛玲小說中的意象文學——以《金鎖記》為例[J].漢字文化,2021(18): 140-141.
〔8〕王佳禾. 探析張愛玲《小團圓》的蒼涼底色[J].作家天地,2023(15): 1-3.
〔9〕趙晗雯. 張愛玲小說中的婚戀悲劇性——以《傾城之戀》和《沉香屑·第一爐香》為例[J].嘉應文學,2024(6): 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