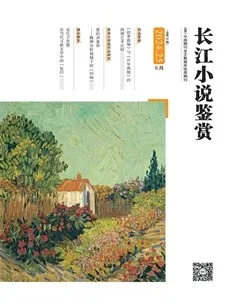陶淵明與華茲華斯詩歌中的生態美學思想比較研究
[摘要] 陶淵明與華茲華斯是中西詩壇吟詠自然的典范,二者跨越時空和文化的界限,建構出在內涵上驚人相似的生態書寫,詩作中均洋溢著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態思想,向往烏托邦式的社會生態思想,以及真善美并存的精神生態思想。從生態詩學視角出發,將陶淵明與華茲華斯詩歌中的生態美學思想進行平行比較研究,挖掘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和諧統一關系,為當下身處“工具理性”統治下的人們帶來一股思想上的清風,或可消減社會發展帶給人的異化現象和心靈矛盾。
[關鍵詞]陶淵明" "華茲華斯" "生態詩學" "自然和諧
[中圖分類號] I06"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5-0125-04
一、引言
我國東晉時期山水田園詩人陶淵明和英國“湖畔派”浪漫主義詩人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詩歌皆以吟詠自然著稱,陶淵明的詩歌生態深受其所處時代和道家思想的影響,流傳有“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表述。華茲華斯則受到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和生態文學家盧梭“返歸自然”與“追求真我”主張的影響,他久居湖畔,具有超越其時代的生態意識及對自然的倫理關懷。兩位詩人都以抒情化的詩句彰顯出人類對自然生態的崇拜,作品中所蘊含的生態美學思想為當下身處“工具理性”統治下的人們帶來一股思想上的清風,也為人們增添了一份應對精神生態危機的勇氣。
生態文學是20世紀生態思潮中極其重要的支流,它通過文學來重視人類文化。本文從生態詩學視角出發,根據魯樞元在《生態批評的空間》中提出的自然生態、社會生態與精神生態三分法,對陶淵明與華茲華斯詩歌中的生態美學思想進行平行比較研究,挖掘詩作中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態思想,向往烏托邦式的社會生態思想和真善美并存的精神生態思想,促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達到和諧平衡的狀態,“讓人類告別冷戰、戰爭、罪惡,走向新世紀綠色生態的自然和社會,讓人性更具有生命的綠色”[1],對于沖破理性的泛化、資本的擴張以及人類主體地位的高揚也具有一定的啟發。
二、田園與水仙: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態
人與自然的關系自古以來即為一種根本性存在,因而魯樞元將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問題看作一個“元問題”,它會“伴隨著其他問題的存在而一直存在,但它的解決也將自然而然地促成其他問題的有效解決”[2]。“天人合一”是生態詩學的一大重要思想元素,強調人類作為生命的存在體,與自然界始終保持著一種生命共同體的關系。陶淵明和華茲華斯筆下的田園、水仙等自然之物紛紛呈現出人與自然相互適應、和諧統一之感。他們以自然為詩,將自由閑適與物我交融的生生之韻表現得淋漓盡致。
作為中國田園詩歌的創始人,陶淵明在其作品中書寫花鳥草木之趣和躬耕田園之樂,用空靈的心境享受歸隱后愜意的田園鄉村生活。在他的生態意識里,對自由的追求可以說是在尋找一種能容納自我的外在生存空間,并在此契合大自然的秀麗景象和千變萬化。正因為擺脫了羈人的官場和“心為形役”的人生困境,陶淵明歸田參加勞動后體會到人之為人的本質力量,并創作了《歸園田居》組詩六首。“復得返自然”指向標題中的“歸”,作者逃離世俗的樊籠,所歸之處不僅僅是自然界,也是個體與天道合二為一的自然狀態。“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3]詩歌在描繪耕種生活的同時,也隱含了自然規律,荒草茂盛而豆苗稀少的自然之變是耕種者需要面對的,因而作者選擇早出晚歸躬耕田園來順應自然。人與山、人與月、人與身邊的一切和諧共存,詩人將其清新自然的心靈凈化為一種崇高的自然美,詩中所蘊含的返璞歸真、融入自然的生態思想在沖破陳舊的精神枷鎖的同時,贏得了后世的欽佩和效仿。陶淵明以描寫田園風光聞名,筆下的自然充滿詩情畫意,他在詩中所傳達的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天人合一”生態思想是“指導陶淵明生活和創作的最高準則”[4]。個體與自然界的互動,當是后人需要不斷傳承的生態理念。
現代工業文明高速發展的同時,人類與自然界原本的和諧關系也被無情打破,人竟在不知不覺中成了自然的對立面。華茲華斯的生態思想最初體現在1802年版《抒情歌謠集》的序言中,他將其詩歌體裁歸納為一種“微賤的田園生活”,“任何來自內心的強烈情感都能在此找到適合的土壤,能夠臻于完熟,少受一些約束,表達出更為質樸有力的語言。在這里,人們的熱情也恰能與自然的美和永恒的形式融為一體”[5]。詩人不僅以現實主義筆調描繪英倫三島獨特的田園風光,以追憶的方式再現已逝的田園生活畫卷,而且還營造了許多山水田園意象,包括落日的光輝、遼闊的碧海、鮮活的空氣以及湛藍的天空等一切自然之物。《丁登寺旁》將孩提到成人歷經的時光變化與詩人對自然的崇高敬意完美地糅合在一起,流露出詩人恬然自適的生活態度和對自然的獨特感悟。不管肉體是否存在,只有當人的靈魂真正融入自然,才能“永遠與巖石,石頭和樹木朝夕相伴”[6]。在《詠水仙》中,詩人以孤獨的流云自喻,“我獨自漫游,像山谷上空 / 悠然飄過的一朵云霓,/ 驀然舉目,我望見一叢 / 金黃的水仙,繽紛茂密”[5]。此處,水仙已然超越了植物學意義,是一種靈性的存在。作者托物言志,從言外之意與象外之境中把握住與大自然息息相通的契機;在物我交融的和諧中將心胸升華到崇高的境界。華茲華斯的諸多詩歌表現出天人合一之美,暗示作者孤獨迷惘,渴望在自然中找到內心所歸。
三、桃花源與割麥女:烏托邦式的社會生態
現代化社會發展的同時,生態系統也遭受嚴重破壞,人類開始構建一種愿景化的理想狀態。陶淵明和華茲華斯均非逍遙于世之人,他們深諳社會的黑暗和百姓的疾苦。陶淵明在憤懣之余用桃花源建構出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表達對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而華茲華斯塑造了割麥女等簡單淳樸的形象來消除資本對人和自然的異化。
陶淵明從小深受儒家正統思想的熏陶,然而其生活的六朝時期是一個佛學和玄學盛行的時代,社會動蕩,政治腐敗,門閥制度森嚴,出身庶族的陶淵明遭人輕視。混亂的社會政治環境之下,個人與社會、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顯露無遺。在陶淵明辭官歸田的第三年,詩人所居陋巷的草房“遇火”,全家人只好在門前的船上暫住。雖然詩中所寫乃詩人一家的遭遇,但客觀上反映了六朝百姓共同遭受的苦難,這種貧困潦倒的生活是當時社會黑暗的一個縮影,百姓的樸素愿望就是社會安定、天下太平。陶淵明遂借武陵漁人行蹤這一線索,采用寫實的手法將黑暗的現實和虛構的世外仙境聯系起來,通過對桃花源安寧和樂環境的描寫,以及對桃林山水阻隔戰火的巧妙設計,呈現出自己心中理想的社會,表現出其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桃花源記(并詩)》描述了一個烏托邦式的和諧社會,呈現出人人平等、人人勞作、人人自足的理想生活模式。“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余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3]桃花源中的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各遂其性的恬靜安詳之感是陶淵明恬澹自守的再現,政治上沒有君權壓制,經濟上沒有剝削壓迫,這一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桃花源深度契合人與社會和諧共處的理想之態。
華茲華斯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經歷了圈地運動等漫長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進而步入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無政府干預的市場自由競爭使得資本主義管理制度對勞動人民的壓榨到了極限,原本是自然之子的人類成為盧梭鄙夷的“最墮落的動物”,且必須面臨機器工業取代手工勞動的威脅,“人們的思維方式變得機械、狹隘、淺顯”[7]。在此背景下,詩人華茲華斯內心充斥著對工業革命的厭惡和對上層社會浮華虛幻的憎恨,渴望通過自己的詩歌去恢復那些被資本減損的自然感召力,化解現實社會暗藏的重重危機。他向夜空中的月亮求助,“請讓我在自己的想象中 / 追隨著你的航跡,/ 天上的光明之船哪,請原諒 / 我以你的榜樣對抗”[8],并且塑造了一群過著簡單淳樸生活的自然人。《孤獨的割麥女》通過角色自傳的方式傳達出對未受工業文明破壞和大機器生產影響的質樸田園生活的向往。“夜鶯也沒有更美的歌喉 / 來安慰那些困乏的旅客—— / 當他們找到了棲宿的綠洲,在那阿拉伯大漠; / 在赫布里底——天邊的海島,/ 春光里,聽得見杜鵑啼叫,/ 一聲聲叫破海上的沉靜,/ 也不及她的歌這樣動情。”[9]詩行中蘊含著冬去春來的和諧烏托邦景象,英格蘭西北邊疆區域的赫布里底群島在冬季沉睡,杜鵑嘹亮清澈的叫聲將群島從沉睡中喚醒,原本寂靜的海島又充滿勃勃生機。少女的歌是“一支被征服民族之歌”,深刻揭露了“殖民歷史的創傷和暴力”[10],反映了蘇格蘭生態農耕被破壞的社會現實,作者借少女之口表達出對生態災難的控訴。
四、安貧者與老乞丐:真善美并存的精神生態
精神作為一種心理狀態,彰顯出主體內在的、意向的、自由的生命活動。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生態領域的危機此起彼伏,“精神生態屬于地球生態循環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人的精神因素也屬于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變量”[11]。跳脫人類中心主義的束縛是正確處理人與自我關系的關鍵一步,當個人將生命與生態融為一體,心理達到平穩狀態,便能達到人類自我存在的最高境界。陶淵明安貧樂道、維持真我的超然精神以及華茲華斯化悲苦為審美的慰藉感詮釋了生態系統健康“精神圈”的真正內涵。
正值政局動蕩不安與思想自由開放相混雜的魏晉時期,以魏晉風度為開端的儒道互補的士大夫精神影響深遠。陶淵明詩歌中暗含的種種生態意識和生態境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現代人異化心靈中的綠色期待。詩人既懷有“有志不獲騁”的志向,又有著“性本愛山丘”的志趣,生性灑脫的他注定與紛擾的塵世格格不入,常有“誤入塵網”和“身居樊籠”的壓抑之感。在物質富裕與精神富足之間,陶淵明更看重后者,盡管深受貧苦困擾,詩人始終保持著高尚的品德和高潔的情操。“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歸去來兮辭》)[3],“望軒唐而永嘆,甘貧賤而辭榮”(《感士不遇賦》)[3],“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3]等詩句體現了他安貧樂道、不改本性的錚錚鐵骨。詩人始終保持著淡泊名利的心境,將躬耕之苦與收成之衰拋于腦后,擺脫“身在江海,心居魏闕”的矛盾心態,完全寄情山水、追求純真,化“‘小我’為‘大我’,渴望進入一個超脫的精神境界”[12]。人與自我的生態之美體現在人類身心和諧與真實的生存之態上,遵循本性,掀去生活的偽飾,才能實現詩意的棲居。陶淵明對“真我”的永恒之追,給予深受精神問題困擾的當代人一定的啟發。
法國大革命后,受啟蒙運動影響,人們的精神世界隨著基督教信仰的動搖變得混亂迷茫。詩人華茲華斯以詩歌為載體抒發內心的情感,以此促使精神生活復活重生。他以敏銳的眼光去發現普通人身上的閃光點,并借助詩歌頌揚其高貴品德。農夫、乞丐、獵人、老嫗等一批鄉村生活的苦難者形象在華茲華斯筆下被賦予特殊的含義,成為在精神迷茫時代中的一股淳樸之風。《坎伯蘭的老乞丐》中,老乞丐行走在自然中,并隨著詩的推進漸漸從一位有血肉之軀的社會邊緣人,獲得了與自然的同一性。18世紀90年代,湖區乞討現象十分普遍,華茲華斯將個體生命的悲涼感融合進詩中,給人“形而上學的慰藉”。詩歌真切地描繪了老乞丐啃食面餅的場景,一種真實的孤獨感躍然于紙上,“他坐在大路旁邊一個不高的 / 石墩上……獨自吃著他的食糧——/ 周圍是渺無人煙的野嶺荒山。/ 他風癱的手雖然避免浪費,/ 但是毫無辦法,事物的碎屑 / 依然像是小陣雨灑落在地上”[13]。華茲華斯將孤單的老人融進群山,栩栩如生而又超凡脫俗,他們雖然命運悲苦,但仍保持著人性的尊嚴。詩人的主觀情感與客觀物象在此處達到高度的融合,揭示出世界上每一個孤獨脆弱的個體都是踽踽獨行的悲苦乞丐。這些具有獨創性的詩歌被注入善良智慧的生命,而這個生命來自詩人自己的精神,“是一種在寧靜的回憶中喚起的慰藉感——這是一種希臘雕塑式的靜穆和悅感”[14]。
五、結語
詩歌本身有著獨立的內在美學價值和目的,雖然陶淵明與華茲華斯所處的時代,所接受的思想熏陶,以及人生經歷都有差異,但二者詩作中蘊含的生態思想卻極其相似,字里行間無不傳達出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好愿景,強調宇宙間萬事萬物應通過“調適”和“協同”達成統一。他們從自然的范式中不斷探索人類的發展動向,扭轉被羈人的官場和現代工業歪曲的人與自然關系,被戰爭與資本積累疏離的人與社會關系,被人類中心主義囚禁的人與自我關系。在文化重構進程中,生態文學的研究發出響亮的聲音,以建立生態文學觀念和審美觀念,尋找生態危機的思想根源為目的來推動生態文明建設。陶淵明與華茲華斯的生態書寫是對自然、社會、人性的思考,可為當代生態詩學的建構和生態文明的發展提供一條借鑒思路,鼓勵人們走出狹隘的自我意識(ego-consciousness),走向更為包容的生態意識(eco-consciousness),用“精神”超越“物質”,用“詩意的棲居”打敗“科技的棲居”,消減社會發展帶給人的異化現象和心靈矛盾,為飽受工具理性和身處精神危機下的人類開辟了一條復返自然之路。
參考文獻
[1] 王岳川.生態文化啟示與精神價值整體創新[J].江西社會科學,2008(4).
[2] 魯樞元.文學的跨界研究:文學與生態學[M].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
[3]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9.
[4]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5] Wordsworth W.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 1798 and 1802[M].Fiona Stafford,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6] 王諾.歐美生態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7] 李麗娜.華茲華斯:心靈生態的守護者[D].北京:北京大學,2005.
[8] 華茲華斯.華茲華斯抒情詩選[M].黃杲圻,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9] 華茲華斯.華茲華斯詩選:英漢對照[M].楊德豫,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
[10] Carruthers G.Scottish Literature[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
[11] 魯樞元.生態文藝學的原則[J].新東方,2001(1).
[12] 易春.陶淵明和華茲華斯田園詩歌的自然觀比較分析[J].文化產業,2018(18).
[13] Wordsworth W.Lyrical Ballads,and Other Poems,1797-1800[M].James Butler and Karen Green, ed.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
[14] 張旭春.“以詩證史”與“形而上學的慰藉”——以華茲華斯《康伯蘭的老乞丐》為例[J].外國文學研究,2020(2).
(特約編輯" 張"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