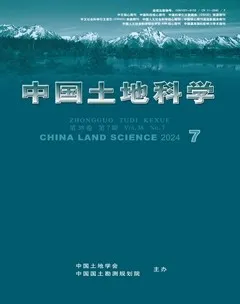論農村集體成員權與土地財產權分離與聯系的制度邏輯
摘要:研究目的:基于城鄉居民不同歷史階段的經濟與社會邊界的特征分析,揭示現階段農村集體成員權和土地財產權分離和聯系的制度邏輯,為類型化構造農村土地權利體系提供理論依據。研究方法:社科法學與概念法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研究結果:(1)現階段鄉村封閉的社會邊界和開放的經濟邊界是形成農村集體成員權與土地財產權分離與聯系的深層原因。(2)從權利分離來看,此兩種權利是法律性質迥然不同的權利,農村集體成員權是團體法上的權利,包括共益權和自益權兩部分,土地財產權是個體法上的權利,包括基于身份分配取得的社會保障導向的土地權利和基于價格機制取得的財產經營導向的土地權利。(3)從權利聯系來看,此兩種權利有著密切的法理聯系,農村集體成員權中的共益權和自益權分別與土地財產權中的集體土地所有權和含身份的用益物權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研究結論:農村集體成員權與土地財產權之間存在分離與聯系的制度邏輯,可以采用“一般法+特別法”的立法技術進行體系化構造,在《民法典》中構造農村集體成員權和土地財產權的基礎法律概念和土地權利關系的一般框架,在《土地管理法》等單行法中規定具體類型土地權利的權利義務、行使規則和救濟規則。
關鍵詞:農村土地制度;團體法;物權法;成員權;“三權分置”
中圖分類號:F30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158(2024)07-0012-10
基金項目: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年度課題(22NDJC070YB);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一般項目(42171254);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LQ22G030001);浙江省省屬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SJWY2022004)。
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問題,是國家與農民關系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1]。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國家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需要,調整農村土地制度以適應形勢的發展[2]。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構建了集行政、經濟、社會于一體的人民公社制度,提取農業剩余支持工業建設[3]。此時的鄉村社區是封閉的管理單元,鄉村成員的經濟邊界、社會邊界和地域邊界高度重疊,農民和土地緊密地捆綁在一起,不允許人員流動和土地流轉[4-5]。改革開放以后,國家逐步放松對鄉村的控制,實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機制,農民重獲勞動權和遷徙權,可在一定范圍內流轉富余的土地,鄉村由完全封閉轉向有限開放[6],鄉村成員的經濟邊界、社會邊界和地域邊界不再重合,對農村土地制度帶來挑戰[7]。鄉村的經濟邊界是開放的,在半工半農兼業化經營的情境下,成員經濟活動的邊界早已超越地域范圍,經常跨區域開展經濟活動;但鄉村的社會邊界是封閉的,一般與地域邊界重合,主體是本土村民[5-6,8]。相應地,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有兩條價值邏輯:一是追求土地利用的效率導向,通過開放、流動的市場化機制配置土地資源,實現土地產出和農民收入的增加;二是追求土地利用的公平導向,通過封閉、排他的福利化機制配置土地資源,保障農民耕種和居住的生活底線[9]。開放的經濟與封閉的社會之間潛藏著對立與統一的矛盾,協調兩者的關系是當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焦點和難點問題[9]。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是統籌公平與效率、封閉與開放的基層創舉[9-12],但目前制度的頂層設計還處于分散割裂的狀態,體系化構造農村土地權利是鄉村法治化整體治理的現實需求。
與本文緊密相關的研究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農村土地財產權改革。農村集體土地兩權分置之后,如何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進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成為迫切的現實需求。“三權分置”應需而生,但如何解釋成為學術難題。孫憲忠、蔡立東等創造性地將承包地“三權分置”的物權邏輯解釋為“所有權—承包經營權(用益物權)—經營權(次用益物權)”[10-11]。同此思路,宋志紅、徐忠國等將宅基地“三權分置”的物權邏輯解釋為“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9,12-14]。(2)農村集體成員權改革。陳小君、宋志紅等將土地承包權和宅基地資格權的權利性質論證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的子權利[15-16]。向前追溯,謝懷栻最早從民事權利體系的視角,論證成員權(社員權)的團體法權利的性質和私法性、限制性、復合性、專屬性等權利特點[17]。章光園、任中秀等系統性地對成員權(社員權)開展基礎研究,考察了國內外團體法權利的發展歷史,論證了成員權(社員權)的程序權與實體權相復合、身份權與財產權相復合等復合性特點[18-21]。在此基礎上,農村集體成員權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陳小君領銜的眾多學者論證了農村集體成員權的團體法權利的性質,并闡釋了農村集體成員權的資格標準、量化規則、權利行使與權利救濟等法理邏輯[15,22-26]。(3)集體成員權與土地財產權的協同改革。徐忠國、楊遂全等關注到集體成員權與土地財產權相對分離的問題,并分析了集體成員權變動與土地財產權變動的雙向影響[12,27-28],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還有提升空間。
綜上,農村土地財產權與集體成員權改革研究取得了豐富、深入的成果,兩者的協同改革研究也得到了初步論證,但研究的體系性還存在不足。針對此種不足,本文借鑒孫憲忠和陳小君的研究思路[11,15],采用社科法學與概念法學相結合的方法開展深化研究:首先從法的外在向度應用組織邊界理論分析和識別制度建構的社會背景和社會需求,然后從法的內在向度深化論證農村集體成員權與土地財產權分離與聯系的靜態和動態制度邏輯,最后從立法論的視角提出法律體系化構建的建議。
1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社會背景與需求:城鄉組織邊界與農村土地制度
按照社科法學的研究思路,本文試圖從歷史聯系和城鄉聯系的宏觀視角審視和識別現階段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社會需求,應用組織邊界理論分析各個歷史階段的城鄉組織管理模式以及相應的農村土地制度的特點。總體而言,我國城鄉組織管理在行政、經濟和社會等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從封閉轉向了開放,對農村土地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當前城鄉社會有限開放的階段性特征,決定了農村土地制度既要為進城農民留下返鄉的退路,又要為規模化高效利用土地創造制度條件。從法的外在向度而言,封閉的社會邊界和開放的經濟邊界對農村集體成員權與土地財產權的分離與聯系提出了制度創新的現實需求。
1.1 計劃經濟時期的城鄉組織邊界與農村土地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國家確立“農業支持工業、農村哺育城市”的發展戰略,通過戶籍、人民公社和統購統銷等三位一體的管理制度,提取農業農村剩余來保障工業城市建設[3]。從組織管理來看,對城市和農村采取二元封閉式管理策略,國家用戶籍制度嚴格限制人口流動[4,29]。在城市采取“單位制”的組織制度,全面采取計劃經濟和單位社會的一體化運作模式,以“國家—工作單位—單位成員”的基本方式組織城市生產和生活[30]。工作單位是行政、經濟和社會的綜合管理單元,單位成員的行政、經濟和社會邊界高度重合,單位與成員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單位為成員提供了低水平的工資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29,31-32]。類似地,農村采取“人民公社”的管理方式,以“國家—社隊—社員”為基本模式組織農村的生產和生活,其他方面與城市高度相似。相應的農村土地制度的特點是將農村的重要生產資料土地進行集體化改造,采取“集體所有、集體經營”的生產經營體制[5,8,33]。國家對城市和農村都采取行政、經濟和社會三位一體封閉化管理的總體支配模式,有利于通過綜合管理單元把社會成員有力地組織起來,避免舊中國“一盤散沙”組織能力弱的局面[4,34]。國家取得的突出成績是建設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城鄉生產效率低下,缺少調動社會成員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激勵機制[3]。
1.2 改革開放時期的城鄉組織邊界與農村土地制度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逐步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持續擴大地方政府和基層組織的自主經營決策的權利[4]。城市方面,改革“單位辦社會”的體制機制,放棄行政、經濟和社會三位一體化封閉式組織模式,行政、事業和企業單位分類強化行政服務、公益服務和經濟生產的職能[31-32]。單位與成員實現了松綁,單位人變成社會人,工作與生活的邊界逐步清晰起來,城市居民的行政、經濟和社會邊界不再高度重合[29-30]。農村方面,放棄了“集體所有、集體經營”的經營體制,建立了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賦予了農民更加充分的勞作權和遷徙權,農村富余勞動力采取半工半農兼業化經營的方式在城鄉間和區域間流動,農民經濟活動的邊界大為擴寬[5,8]。但我國地方政府是發展型政府,財政資源主要投向了城市、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等發展型項目,投向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資金相當有限,很難在農村建設類似城市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因此,替代性地保留了農村的行政和社會組織管理模式,仍然以農村集體封閉式管理的模式為集體成員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集體成員的行政邊界、社會邊界與地域邊界基本重合[6]。值得注意的是,現階段城鄉間的開放性和流動性是有限度的,影響城鄉融合的戶籍制度改革仍未完全實現,進城農民市民化還面臨諸多體制機制障礙,為進城農民保留集體成員權利和土地財產權利是保障他們城鄉之間可進可退的制度條件[35]。
1.3 新時期鄉村組織邊界與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黨和國家一直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形勢調整完善農村土地制度,將基層和群眾創造的先進適用經驗轉化為黨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1,36]。當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焦點和難點問題是統籌處理好鄉村經濟開放性與鄉村社會封閉性的問題,基層和群眾創造出農村承包地和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的實踐經驗[9,12-13,16],部分已經轉化為黨的政策或國家的法律,但從制度頂層設計的視角來看還沒有體系化、周延性地構建起農村土地權利體系,法制建設落后于社會需求,不能很好地適應現階段鄉村經濟邊界開放、社會邊界封閉的實際[33]。首先,物權法上的農村土地權利沒有完成體系化的構建。雖然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陸續在《農村土地承包法》、《物權法》和《民法典》物權篇中采用“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經營權”的物權邏輯進行了法律表達,但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依然只是黨的農村土地政策,沒有轉化為國家普適性的法律規定[12,35]。其次,團體法上的農村土地權利尚在構建過程中。團體法上的集體成員權包含著重要的土地權利,比如農村承包地、宅基地、土地征收補償費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金等的分配請求權等,但由于團體法上土地權利的研究不夠全面深入,重要的土地法律上還缺少對這些土地權利的法律表達[15,23,26]。《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正在制訂過程中,兩輪草案已經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但從公示的草案文本來看相關的制度規則還比較原則,只是粗略地列舉了部分集體成員土地權利,集體成員資格認定的標準與程序、各類集體成員權中土地權利的行使與救濟等規定還比較粗略。在開放的市場經濟體系下,城鄉人口流動日益頻繁,人口流動與成員封閉引起的集體成員權訴訟案一直處于高發態勢,法律規范的缺失和粗疏已經嚴重影響法律定分止爭的功能,部分特殊群體的合法權益長期受到侵害,遲遲得不到法律的正義保障[22,24-25]。最后,農村集體成員權和土地財產權雙向聯動的制度規則亟待建設。人口流動和家庭變化已是鄉村生活的常態,農村集體成員權與土地財產權之間一方變動后另一方進行聯動處置的法律規范尚處于薄弱的狀態,亟待強化研究和制度建設[12,28]。
2 靜態制度邏輯:成員權與財產權的分離與聯系
按照“潘德克吞”權利邏輯體系,需要對各種權利進行一般抽象進而類型化和體系化,形成內在邏輯清晰的權利體系,本文將應用概念法學的理論進行權利類型的邏輯構建。在“人—物”兩分的邏輯體系下,將法律權利劃分為“人”上之權利“人身權”與“物”上之權利“財產權”,遵循“人”之不可支配之普適價值將“人”排除在權利客體之外[17,21]。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越來越復雜,在體系化的視角下人身權根據“由己向外推”的社會化程度可進一步劃分為人格權、親屬權和成員權,表現出個體法上權利向團體法上權利延伸的導向,其中人格權是與本人緊密相關的人身權利(如姓名權、肖像權等),親屬權是人在家庭團體中的人身權利(如監管權、繼承權等),成員權是人在社會團體中的人身權利(如投票權、分配權等)[15,17,20-21,23]。財產權體現出個體法上權利的典型特征,但也加入了社會本位的限制,由絕對權利轉化為相對權利,按權利客體的形態劃分為有形財產權和知識產權,有形財產權按照權利作用相對人的范圍可進一步劃分為對世性的物權和對人性的債權[17]。與農村土地權利體系化構造緊密相關的權利類型是農村集體成員權和土地財產權[15,23,37],按照 “人—物”兩分的邏輯架構,需要對農村集體成員權和土地財產權進行分離和聯系(圖1)[12,28]。思想是行動的先導,長期以來人們對于團體法上的土地權利和財產法上的土地權利的性質認識不清,導致在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管理實踐中出現種種困惑和亂象[12-13,15,23],本文正本清源詳細論證兩者的區分與聯系。
2.1 成員權與財產權的分離

在大陸法體系下,集體成員權和土地財產權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權利。成員權是團體法上的人之權利,規范的是團體成員與成員團體的權利義務關系,需要著重分析成員團體的性質、團體成員的構成及團體與成員的法律關系[21,26]。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團體性質是以本土農民為主體構成的特別法人組織,現階段其主要功能是組織農村統分結合的兩層經營體系,一方面發展集體經濟為集體成員享受公益事業提供經濟基礎,另一方面以公平為導向的福利化分配政策向集體成員提供承包地和宅基地等基本生產和生活資料[26]。農村集體產權改革的目標是解決長期以來農村集體經濟主體虛化不實、賬目模糊不清的問題,加強集體經濟組織理事會和監事會等代理機構建設,清查核算資源性、經營性和公益性等集體資產,健全農村集體經營的體制機制[15,23,38]。與公司等一般法人不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特別法人是集體成員守望相助的福利性經濟組織,一經成立一般不予破產清算,除非合并等特別事由需要注銷其中的某個組織[26]。農村集體成員具有排他性的封閉團體邊界,其主體成員限定在土地集體化時期將土地等生產資料無償交由社隊的農戶及隨著時間推移這些農戶家庭中基于親屬權而獲得成員資格的其他家庭成員,補充性的集體成員限定在國家政策安置的移民人員[24-25]。在經濟開放、人員流動的背景下維持成員邊界的排他和封閉是比較困難的,需要明確歷史上征地安置、升學、參軍、刑事處罰、招工、離婚等原因造成的特殊人群的成員資格認定標準和程序等法律規則[24-25,38],這些特殊人員需要借由人格權與親屬權才能獲得成員資格,因此人格權和親屬權是成員身份的轉化器,與成員權有緊密的邏輯聯系。農村成員集體與集體成員之間的法律關系就是農村集體成員權,集體成員行使成員權利和履行成員義務從而獲得個人利益和壯大集體經濟[15]。其中,集體成員經由法定程序按照民主集中原則將個體意志匯總成集體意志經營總有資產的權利是成員共益權,典型的包括參與權、知情權、投票權、監督權等;集體成員經由法定程序向成員集體提出利益分配申請從而將集體財產轉化為個體財產的權利是成員自益權,典型的包括承包地、宅基地、征地補償費和土地出讓金的分配請求權[15,17,38]。因此,成員權是集體利益與成員利益的轉換器,特別是在將成員集體的土地物權轉換為集體成員的土地物權的過程中發揮著轉換器的作用,下文將重點論述。
土地財產權是財產法上的物之權利,規范的是物權法上和合同法上的受到法律保護的土地利益,作為有體物上的實體性權利需要處理好鄉村經濟的開放性和社會的封閉性的矛盾,統籌好公平導向的福利分配和效率導向的經營配置的矛盾[9-11,13]。按照大陸法土地財產權利分離的一般法理,所有權分離出用益物權,用益物權分離出擔保物權和債權,但由于不同種類的土地權利承擔了不同的經濟社會功能,其產權流轉的邊界受到了差別化的限制[10,12]。根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處分權利,土地所有權分離出用益物權,根據分離過程中是否涉及公益性或身份性權益,可以區分不受限用益物權和受限用益物權。在不涉及公益性或身份性權益的情況下,經法定公開的程序所有權分離出不受流轉限制的出讓用益物權,其權利主體的邊界是開放和流動的。比如,集體土地所有權分離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和四荒地使用權。在涉及公益性權益的情況下,用益物權主體的邊界限定在農村集體的下屬機構。比如,土地所有權分離出劃撥性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與國有建設用地相似的邏輯,在補繳土地出讓金后劃撥使用權可以轉換為出讓使用權,獲得開放流轉的權利。在涉及身份性權益的情況下,這種用益物權的主體邊界是封閉和排他的[10,13]。比如,經過集體決策程序土地所有權分離出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因含有身份性權利,這兩種用益物權的社會邊界限定在農村集體組織成員的范圍。為了適應鄉村經濟開放和社會封閉的階段特征,人員流動后閑置的承包地和宅基地需要得到市場化配置的規模經營,受限制的用益物權分離出不受限的次級用益物權,身份性的權益保留在受限制的用益物權中,財產性權益轉移到不受限的次級用益物權中。這兩種權利是獨立平等的權利,受限用益物權在集體組織中的調整或流轉不影響次級用益物權的行使[10-14]。典型地,土地承包經營權分離出土地經營權[13],宅基地使用權分離出宅基地經營權(權利名稱獲得學界較多認可,但法律中尚無表述)[12]。“所有權—用益物權—次級用益物權”三級權利分置,統籌了社會保障與財產經營的對立統一的矛盾,為鄉村的共同富裕提供了法律保障[12-13,35]。此外,不受限制的用益物權和次級用益物權可以進一步分離出擔保法上的權利“抵押權”,不受限制的物權可以進一步分離出合同法上的權利“債權”,抵押權和債權按照市場經濟的價值導向進行配置,其社會邊界是開放和流動的[12,35]。
2.2 成員權與財產權的聯系
盡管農村集體成員權與土地財產權是兩種性質不同、功能各異的權利,但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邏輯聯系[12,28]。第一,成員共益權的有效行使保障了集體所有權的有效行使。成員共益權是集體成員個體就公共經濟事務享有的個體性權利,具有程序權和形成權的典型特征,成員共益權的有效行使在經過公開合法的法律程序下按照民主集中原則將個人意志轉換成具有法律效力的集體意志,有效保障成員集體的實體化和集體所有權的有效行使,克服長期以來存在的集體所有權的主體虛化、成員權利模糊的問題[17,37-38]。成員共益權作用的土地財產權主要包括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征地補償費所有權和集體土地出讓金所有權,集體成員按法律和組織章程規定的程序行使共益權對這些集體資產的運營和分配做出集體決策。為提高組織運行效率,成員行使共益權建立理事會和監事會等常設機構,代理處理成員集體的公共日常事務。第二,成員自益權的有效行使保障了集體財產向成員個體的福利性分配。成員自益權是集體財產轉變成個體財產的轉換器,經集體成員申請并經成員集體(或代理機構)審核同意,按照組織章程確定的公開分配規則,將集體財產轉換為個體財產,具有實體權和請求權的典型特征[17,19,26]。這種轉換存在著兩種情形:一是將集體共有所有權轉換為成員個體所有權。典型的是在成員權中的征款補償費和土地出讓金分配請求權的作用下,將集體所有的征款補償費和土地出讓金按照成員集體確定的分配規則轉換成集體成員個體所有的征款補償費和土地出讓金。二是將集體所有權轉換為個體的受限用益物權。典型的是在成員權中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分配請求權的作用下,從集體所有的土地所有權中分離出農戶所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因此這兩種受限用益物權都含有身份福利性的財產權利,正如前文所言其流轉邊界是成員集體的范圍。
3 動態制度邏輯:成員權與財產權的變動與銜接
在開放的鄉村經濟中保持封閉的鄉村社會對農村土地制度帶來了艱巨的挑戰,鄉村人員的社會流動和家庭變動或早或遲會對集體成員權和土地財產權帶來變化[28]。在深入討論之前要先把吸收人員變化的容器“農戶”給引入進來。農戶是鄉村社會的細胞,鄉村成員的生老病死主要是在家庭中完成,以血緣為紐帶的家庭承擔著養老、撫幼和教化的社會功能。家庭成員的經濟資源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整體配置,青壯年農閑外出務工經商、農忙返鄉務農,老弱孕在家務農節約家庭開支,農戶根據城鄉資源差異以家庭為單元進行半工半農兼業經營的理性行為選擇[39-40]。因此,現階段把農戶作為配置和登記集體成員權和土地財產權的基本單位,也是實施“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土地權益固化的基本單位,以此統籌和平衡社會流動和家庭變動帶來的土地利益的變化[41]。可以在兩個方向上研究兩者的變動與銜接問題:(1)家庭人員變動引起成員權和財產權的聯動;(2)農戶離開鄉村退出財產權引起成員權的聯動(圖2)。
3.1 集體成員權的變動帶來土地財產權動態銜接的問題

家庭因種種原因發生增加或減少家庭成員的情況,常見增加家庭成員的情形包括合法結婚增加女方(男方)成員、合法生育或收養子女等,減少家庭成員的情形包括合法離婚減少女方(男方)成員、各種原因家庭成員死亡和家庭成員進城成為公職人員等[24-25,42]。家庭成員的增減,需要經過成員集體規定的法律程序,借由本人的人格權和與家庭的親屬權的轉化變更集體成員的成員權。家庭中集體成員變化帶來的土地權利變化是:在家庭的成員共益權方面,根據成員變化增加或減少對集體所有土地和其他資產相應的權利份額;在家庭的成員自益權方面,雖然在集體成員登記簿上登記農戶的成員和成員權變化,但為了穩定產權預期、引導土地高效利用,一般采取“生不增、死不減”權益固化的原則,家庭成員增減帶來的土地利益變化一般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整體性吸收[28],比如說征地補償費和土地出讓金分配的家庭總體份額不變、成員間的份額調整由家庭內部確定。在土地財產權方面,家庭成員增加所需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由其他家庭成員調配,家庭成員減少釋放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由其他家庭成員繼承或接收[12,28]。在農戶分戶時,承包地方面由農戶內部商定各個新家庭的承包地的份額,宅基地方面按“一戶一宅”原則配置宅基地使用權,新分出戶以戶為單元基于集體成員自益權向成員集體提出分配宅基地的申請。當農戶整體滅失時,根據組織章程的規定確定土地財產權是由成員集體收回還是由農戶的集體成員直系親屬繼承,收回或繼承按組織章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執行;對于農戶的非集體成員,失去繼承土地承包經營的權利和參與承包地的二輪延包的資格,可以依親屬權繼承農房所有權,補繳土地出讓金后獲得宅基地使用權,可以根據組織章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繼承集體公共財產的分配請求權。
3.2 土地財產權變動帶來集體成員權的動態銜接的問題
在開放的市場經濟體系中,進城農民將農村中不能移動土地權利轉化為流動資產或城市資產,有利于農民帶資進城實現深度市民化[22]。總體制度導向是堅持自愿有償原則推動實現市民化的進城農戶退出在農村保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現階段城鄉二元體制尚未完全破除,進城農民完全融入城市尚存在種種體制機制障礙,因此需要保留城鄉兩棲人員在城鄉之間可進可退的制度安排[22-33]。農戶退出農村土地權利主要有永久退出和保留退出兩種方式。永久退出是指農戶既退出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等土地財產權,又自愿有償退出集體成員權;保留退出是指農戶自愿有償退出土地財產權但保留集體成員權。對于永久退出,農村集體支付農戶“雙退出”的對價后,只要在不動產登記簿和集體成員登記簿上同時注銷登記相應的土地權利即可。對于保留退出,農村集體支付農戶退出土地財產權的對價后,農戶退出了土地承包經營權或宅基地使用權等土地財產權,但保留重新分配取得相應土地財產權的成員權利,相應地在不動產登記簿上分類注銷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等土地權利,同時在集體成員登記簿的附記上要登記土地財產權利的退出情況。在保留集體成員資格的條件下,為進城失敗的農戶保留了按一定條件和程序重新獲得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等土地財產權的機會[22]。農戶在保留成員資格退出宅基地使用權后,農戶集體成員權中的宅基地分配請求權恢復為圓滿狀態,它的實現形式可以多樣化,除了分配宅基地的方式外還可以有貨幣、住房、“房票”、“權票”等多種實現形式[27-28]。
3.3 集體成員權登記與土地財產權登記的一致性問題
農村集體成員權和土地財產權是兩類性質不同、功能各異、聯系緊密的權利。農村集體成員權是團體法上的權利,保護的是待實現的土地利益;農村土地財產權是財產法上的權利,保護的是已實現的土地利益[12,35]。這兩種權利都需要有良好的制度工具予以法律保障,因此需要建立健全農村集體成員權登記和不動產登記制度[12]。從兩類登記有效協同的視角來看,農村集體成員權登記要詳細記錄成員土地自益權的實現情況和實現結果,不動產登記要詳細記錄農戶的財產權情況,一方登記信息發生變化的,另一方登記信息要相應變更,特別是在農戶分戶申請宅基地和農戶消戶退出宅基地時,要加強雙方登記信息的有效銜接[12]。盡管戶籍改革逐步剝離社會管理而增強公共服務的功能,但兩類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信息時應同時主動與戶籍登記信息保持一致。
4 研究結論與立法建議
4.1 研究結論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和封閉社會管理,在城市和鄉村分別以“單位制”和“公社制”組織社會生活和生產,行政、經濟和社會邊界高度統一。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在城市實現行政、經濟和社會的開放和流動,行政、經濟和社會邊界出現分化,在鄉村的經濟方面實現開放和流動,但在行政和社會方面仍然保持封閉和排他,保留的原因在于城鄉二元體制仍未根本破除,需要為城鄉兩棲人員提供可進可退的制度保障。統籌鄉村經濟開放和社會封閉之間對立統一的矛盾是當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社會需求。農村集體成員權是團體法上的權利,制度功能是保障農民獲得農民集體經濟的福利分配,其共益權保障集體成員參與決策壯大集體經濟,自益權保障集體資產公平福利性分配給成員。農村土地財產權是個體法上的權利,制度功能包括福利保障和經濟運營等兩個方面。經由集體成員權獲得的土地財產權(如土地承包經營權),具有身份和財產雙重屬性,產權流轉邊界封閉限定在成員集體;基于市場價格機制獲得的土地財產權(如四荒地使用權),不具有身份屬性,產權流轉邊界不受限制。盡管成員權和財產權在性質上有明顯差別,但兩者存在緊密的聯系。成員共益權的有效行使保障了集體所有權的有效行使,成員自益權的有效行使保障了集體財產轉化為個體財產。在開放流動的市場經濟中,要以農戶為中介來吸收社會流動和家庭變化帶來的家庭集體成員權和土地財產權的雙向變化,構建雙向動態變更登記制度。
4.2 立法建議
《民法典》編纂的成功經驗是先構建統一的規則框架《民法總則》,然后逐步建構和完善民法分則的《合同法》、《物權法》、《婚姻法》、《繼承法》和《侵權責任法》等,最后進行“潘德克吞”式法典編纂[43]。從立法體系論的視角,當前在立法技術選擇上存在著“單純特別法”“先特別法后一般法”“一般法+特別法”的方案選項,借鑒謝懷栻的“潘德克吞”式體系化權利構造的思路,本文推薦采用“一般法+特別法”的立法技術[17]。理由是當前中國鄉村經濟社會正處于傳統邁入現代的轉型階段,經濟社會結構具有普遍性與階段性的顯著特點。為更好地兼顧新法律規則建構和舊法律規則修改的現實,可以采用提取最大公因式的立法技術在《民法典》中創制普遍性的規則,而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土地管理法》和《農村土地承包法》等單行法中創制個性化和改革性的規則,同時保障農村土地權利的體系性和階段性,最終完成《民法典》中農村土地權利體系化構造的目標。
針對現階段農村土地法律對農村土地權利保護體系化和周延性不充分的問題,按照實施從易到難的程度提出以下立法建議:首先,在《民法典》總則篇中建構兩種權利分離與聯系的一般性制度框架。在《民法典》總則篇中建構框架性的權利種類及邏輯聯系,引入成員權、農村集體成員權和各類子權利的法律概念,抽象性地規定成員權的取得、退出、流轉和繼承的一般性規則,一般性地規定集體成員權中共益權和自益權與土地財產權中集體所有權和含身份用益物權的法理邏輯。其次,在單行法中分類保障團體法和個體法上土地權利的程序性權利。權利分離方面,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和《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中分類規定各類土地權利的行使程序和法律效力。權利聯系方面,從制度上和技術上保障農村集體成員權與土地財產權之間登記記錄的一致性。再次,在單行法中分類保護土地的社會保障和經濟運營的實體性權利。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中重點保障成員邊界封閉導向下共益權與自益權的種類和行使方式、各類權利行使結果與土地財產權的關系及權利受到侵害的救濟方式和途徑。在《農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中規定基于集體成員身份取得的土地產權和基于市場價格機制取的土地產權的種類及其產權流轉的社會邊界。最后,采取“一般法+特別法”的法典化立法技術體系化地構造農村集體成員權和土地財產權制度。按照“潘德克吞”式的立法體系,采用提取最大公因式的立法技術在《民法典》中創制普遍性的規則,而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等單行法中創制個性化的規則。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俞明軒,谷雨佳,李睿哲. 黨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土地政策:百年沿革與發展[J] . 管理世界,2021,37(4):24 -35.
[2] 孫樂強. 農民土地問題與中國道路選擇的歷史邏輯——透視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的一個重要維度[J] . 中國社會科學,2021(6):49 - 76.
[3] 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M] .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41 - 46.
[4] 李春根,羅家為. 從動員到統合:中國共產黨百年基層治理的回顧與前瞻[J] . 管理世界,2021,37(10):13 - 26.
[5] 李增元,李洪強. 封閉集體產權到開放集體產權:治理現代化中的農民自由及權利保障[J] .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6(2):1 - 14.
[6] 劉玉照,田青. “集體”成員身份界定中的多重社會邊界[J] . 學海,2017(2):115 - 122.
[7] 折曉葉. 村莊邊界的多元化——經濟邊界開放與社會邊界封閉的沖突與共生[J] . 中國社會科學,1996(3):66 -78.
[8] 李增元,葛云霞. 集體產權與封閉鄉村社會結構:社會流動背景下的農村社區治理——基于溫州的調查分析[J] .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4(3):78 - 87.
[9] 徐忠國,卓躍飛,吳次芳,等. 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的經濟解釋與法理演繹[J] . 中國土地科學,2018,32(8):16 - 22.
[10] 蔡立東,姜楠. 農地三權分置的法實現[J] . 中國社會科學,2017(5):102 - 122.
[11] 孫憲忠. 推進農地三權分置經營模式的立法研究[J] . 中國社會科學,2016(7):145 - 163.
[12] 徐忠國,卓躍飛,李冠,等. 宅基地三權分置的制度需求、實現形式與法律表達[J] . 中國土地科學,2022,36(1):1 - 9.
[13] 宋志紅. 宅基地“三權分置”的法律內涵和制度設計[J] .法學評論,2018,36(4):142 - 153.
[14] 宋志紅. 鄉村振興背景下的宅基地權利制度重構[J] . 法學研究,2019,41(3):73 - 92.
[15] 陳小君. 我國農民集體成員權的立法抉擇[J] . 清華法學,2017,11(2):46 - 55.
[16] 宋志紅. 宅基地資格權:內涵、實踐探索與制度構建[J] .法學評論,2021,39(1):78 - 93.
[17] 謝懷栻. 論民事權利體系[J] . 法學研究,1996,18(2):67 - 76.
[18] 任中秀. 民法典編纂中成員權入典之立法構想[J] . 江海學刊,2019(4):163 - 168.
[19] 任中秀. 成員權基本理論問題辨析[J] . 社會科學家,2019(2):129 - 134.
[20] 章光園. 再論社員權——以其演變、意義與保護為視角[J] . 寧德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1 - 7.
[21] 章光圓. 論社員權的概念、性質與立法[J] . 寧德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4):7 - 11.
[22] 陳美球,廖彩榮,馮廣京,等.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的實現研究——基于“土地征收視角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實現研討會”的思考[J] . 中國土地科學,2018,32(1):58 - 64.
[23] 戴威,陳小君. 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的實現——基于法律的角度[J] . 人民論壇,2012(2):20 - 23.
[24] 江曉華.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司法認定——基于372份裁判文書的整理與研究[J] . 中國農村觀察,2017(6):14 - 27.
[25] 馬翠萍,郜亮亮.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理論與實踐——以全國首批29個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為例[J] . 中國農村觀察,2019(3):25 - 38.
[26] 楊一介.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解釋[J] .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44(9):51 - 63.
[27] 郭忠興,王燕楠,王明生. 基于“人 - 地”二分視角的宅基地資格權探析[J] . 中國農村觀察,2022(1):2 - 15.
[28] 楊遂全,耿敬杰. 論農村集體成員身份和土地產權相對分離——以成員土地資格權的收回或轉讓及繼承為視角[J] . 中國土地科學,2022,36(7):10 - 18.
[29] 李珮瑤. 從“閉合”到“開放”:單位組織內外邊界的形塑與消解[J] . 社會科學戰線,2021(2):222 - 232.
[30] 李漢林. 變遷中的中國單位制度:回顧中的思考[J] . 社會,2008,28(3):31 - 40.
[31] 李路路. 論“單位”研究[J] . 社會學研究,2002(5):23 -32.
[32] 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曉. 市場轉型與“單位”變遷:再論“單位”研究[J] . 社會,2009,29(4):1 - 25.
[33] 陳世偉. 地權變動、村界流動與治理轉型——土地流轉背景下的鄉村治理研究[J] . 求實,2011(4):93 - 96.
[34] 渠敬東,周飛舟,應星. 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J] . 中國社會科學,2009(6):104 - 127.
[35] 高飛. 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法理闡釋與制度意蘊[J] .法學研究,2016,38(3):3 - 19.
[36] 王敬堯,魏來. 當代中國農地制度的存續與變遷[J] . 中國社會科學,2016(2):73 - 92.
[37] 王利明,周友軍. 論我國農村土地權利制度的完善[J] .中國法學,2012(1):45 - 54.
[38] 韓松. 論成員集體與集體成員——集體所有權的主體[J] . 法學,2005(8):41 - 50.
[39] 費孝通. 江村經濟[M] .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29 - 42,55 - 62.
[40] 黃宗智.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M] . 北京:中華書局,2000:304 - 308.
[41] 周其仁. 城鄉中國(上)[M]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24 - 233.
[42] 童航.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標準——基于地方立法文本和規范性文件的分析[J] . 農業經濟問題,2023(8):73 - 85.
[43] 孫憲忠.中國民法典總則與分則之間的統轄遵從關系[J] .法學研究,2020,42(3):20 - 38.
Institutional Logic of Separation and Connection between Membership Rights and Land Property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s
XU Zhongguo, ZHUO Yuefei, LI Guan, WANG Xueqi, CHEN Yang
(Law School,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reveal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the separation and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embership rights and land property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s in the current stage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oundarie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urther construction of rural land rights system. The research method combining sociology of law and conceptualist jurisprudence is employ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at the current stage, the closed social boundary and open economic boundary in rural areas a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separation and connection between membership rights and land property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s.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ghts separation, these two types of rights are of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legal nature. Membership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s pertain to group law, encompassing collective benefit rights and individual benefit rights.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are rights of individual law, including social security-oriented land property rights based on membership and management-oriented real rights based on price mechanism.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ghts connection, these two kinds of rights have close legal relations. The collective benefit right and individual benefit right in membership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and usufructuary right with identity, respectively. In conclusion, there is a systematic logic of separation and connection between membership rights and land property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s, which will be systematically proposed by the legislative technology of “general law + special law”. The basic legal concepts of membership rights and land property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s and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land right relations are constructed in the Civil Code. The Land Administration Law and other separate laws stipulate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exercise rules and relief rules of specific land rights.
Key words: rural land policy; group law; property law; membership right; “tripartite entitlement system”
(本文責編:郎海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