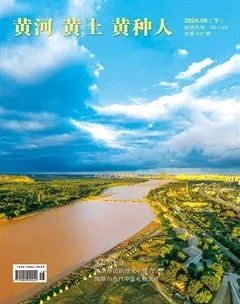論大河村遺址一件彩陶盆的圖像藝術(shù)及其內(nèi)涵








大河村遺址是一處著名的仰韶文化遺址,幾十年來發(fā)掘出土了一批豐富的器物,尤其是其中的彩陶,非常重要,是大河村文化的一項代表性內(nèi)容。近年來,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大河村遺址博物館在配合大河村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發(fā)掘過程中,于2014年8月出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彩陶盆(圖1)。這件彩陶盆特別突出的一個特點是圖案非常完整,構(gòu)圖特別新穎,非常具有藝術(shù)性(圖2)。這件彩陶盆一經(jīng)出土,立即引起了學術(shù)界的高度關(guān)注,有不少學者紛紛就該件彩陶盆發(fā)表了自己的意見和看法。但是,對于該件彩陶盆圖像的具體解讀卻比較少,因此,筆者撰文對這一問題進行初步論證。
彩陶盆出土背景及時代
該彩陶盆(W189:2),口徑45.7厘米、底徑13.5厘米、高15.7厘米。泥質(zhì),黃色陶胎,淡黃色陶衣。寬沿軟折,弧腹內(nèi)收,小平底,底部殘失。上腹近口沿處有兩對鉆孔。
該彩陶盆出土于大河村遺址2014DHT1西南部,屬于一個甕棺的組成器物之一。該甕棺為三件一組(圖3-1),其他兩件是一個陶罐(圖3-2)、一個陶缽(圖3-3),順序是陶罐、彩陶盆、陶缽。
陶罐(W189:1),夾砂灰陶。斂口,折沿近平,方圓唇,矮領(lǐng),領(lǐng)內(nèi)壁內(nèi)凹,肩部近領(lǐng)處有一周凹槽,鼓肩,腹部斜收,平底。肩部飾5周凹弦紋。頸部有2個鉆孔。口徑43厘米、肩徑49.5厘米、底徑16.5厘米、高31.3厘米。
陶缽(W189:3),泥質(zhì)紅陶。敞口,圓唇,折腹,上腹近直,下腹斜收,平底。素面。口徑32厘米、肩徑33厘米、底徑11厘米、高12.6厘米。
從3件器物特征來看,與大河村遺址發(fā)掘報告中二期晚段或者三期早段同類陶器非常相似。其中的陶盆,實際上是從西安半坡類型就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在廟底溝類型時較為常見,往西傳播到甘肅、青海地區(qū),馬家窯文化較為多見,往東傳播到鄭州地區(qū)。大河村文化中該類器物有一定發(fā)現(xiàn),主要在大河村文化二期、三期,即仰韶文化的中期晚段。
彩陶盆圖像的藝術(shù)分析
這些彩陶圖像主要分布于陶盆的沿面和腹部。沿面的圖案分為8段,腹部的圖案以變形花瓣紋形成的斜向軸為間隔,分為4組(圖4)。從上面的8段和下面的4組來看,每一段里面都有對稱的兩組。
筆者認為,這些圖案的藝術(shù)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大家關(guān)注:
一是圖像框架的設(shè)計和繪制心理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在盆面分的8段,嚴謹?shù)凰腊澹砻鬟@個制作者在繪制的時候,雖然不是隨心所欲,但是絕對不是中規(guī)中矩,而是非常老練和成熟。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有兩段距離有點偏小,顯然是這個繪制者在這個地方有點失誤。在這8段里面的圖案,可以看到繪制者在繪制的時候則是非常的嚴謹,基本上沒有再出現(xiàn)失誤,可能因為他在分段的時候有過失誤,所以在下一步的繪制過程中,就顯得比較認真。從圖像的變化,我們可以觀察到這位繪制者在繪制這一圖像的過程中可能的行為和心理。
腹部圖案總體可以視為以花瓣紋為間隔的4組旋紋組合。每組旋紋組合之間的造型實際是花瓣紋的變體。我們在半坡類型以來的仰韶文化中發(fā)現(xiàn)諸多不變體的花瓣紋,如果按照中規(guī)中矩的模型設(shè)計,會使得整個畫面產(chǎn)生斷層。4組旋紋為非常具有流線型色彩的圖案,作為位于它們中間的圖像,由于是花瓣紋,非常明顯,極容易使得整個畫面氣息不通,各組無法呼應(yīng)。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繪制者獨運匠心,令人驚奇地運用了有學者稱之為“斜向軸對稱”的錯位表達方法。同時,在對花瓣紋進行斜向錯位之后,在這個斜向軸的地方竟然還繪制了一組線,簡直就是繪制者錯位裁剪時的示意線。這一組線條畫法隨形就勢,與旋紋做到了很好的協(xié)調(diào),使得整個畫面一氣呵成,渾然天成,非常完美。這一設(shè)計方式也顯示出這個繪制者具有很高的整體藝術(shù)審美觀。
二是繪畫技法的嫻熟方面。陶盆的另一組圖像,是在白色地紋即白衣上以黑彩和紅彩進行繪制的。黑彩繪制的主要是旋紋,具有非常藝術(shù)化的流動性。在每兩組之間作為間隔的花瓣紋,錯位表現(xiàn),其間隔有人認為是斜向軸對稱軸的,并不是簡單的直線,而是隨著黑色圖像自然走形,若行云流水,非常自然。從顯微鏡里看,幾乎都是一筆成型。從這些細節(jié)看,繪制者若沒有熟練的繪畫技術(shù),是不可能做到的。
三是整個彩陶圖像色彩的藝術(shù)搭配方面。仰韶時代的彩陶,總體是黑彩居多。鄭州地區(qū)以西的彩陶以及大河村文化三期以前的彩陶,紅彩很少。從大河村文化二期—三期起,鄭州地區(qū)就開始在黑白色彩運用的同時應(yīng)用紅彩。
在色彩學上,黑白的色調(diào),一般會使畫面的對比度顯得非常明顯,格調(diào)冷峻,適宜于特定的場景。這時若有紅色等淺色出現(xiàn),則會降低這個對比度。大河村遺址這件彩陶盆的整個圖像都是在白衣彩陶盆上繪制的黑彩圖案和紅彩圖案,既不失黑紅配這一自古以來藝術(shù)色彩經(jīng)典搭配的沉穩(wěn)感,又由于白衣底色的出現(xiàn)使得畫面平添幾分明朗。
在色彩和具體圖像的位置搭配方面也是獨具匠心。該陶盆的沿面圖案,每一段中左右整體造型對稱的單元,每個都是由黑彩和紅彩繪制的,但是其左邊和右邊單元的具體圖案并不是對稱的,明顯方向是顛倒的,并且每個單元是用兩種顏色繪制的,這一色彩顛倒、具體構(gòu)圖顛倒但是整個面積對稱的藝術(shù)形式,立即為整個畫面增加了自然的韻律和靈動,同時也在視覺上給觀者一種移步換景的印象和感覺。
彩陶盆圖像的內(nèi)涵解讀
關(guān)于這件彩陶盆的圖案,不少學者予以了關(guān)注。有學者描述為:“口沿飾紅彩直線紋、白彩弧形三角紋、紅彩圓點紋、黑彩弧線紋,上腹施白地,飾紅彩彗星紋、黑彩月亮紋、黑彩弧形三角紋、黑彩圓點紋、紅彩弧線紋。”這是一種傳統(tǒng)的解讀和命名方式。也有學者就其中的圖案予以了論證。不過目前都還沒有從細節(jié)上予以詳論。
首先看大河村彩陶盆口沿的圖案,共分8段,每段的圖案都是一樣的。按照常規(guī)的講法,其左右單元即最早由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命名的西陰紋。該彩陶西陰紋,基本特征是上端弧,左端弧,有圓點。從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王仁湘先生的分類看(圖5),其與棗陽雕龍碑遺址發(fā)現(xiàn)的c型西陰紋最像,其次與泉護村的b型、c型,廟底溝的c型,晉南地區(qū)芮城西王村的d型較近似。總體看,該陶盆的西陰紋應(yīng)該直接來自陜縣廟底溝地區(qū)或者晉南地區(qū),關(guān)中地區(qū)是其更遠的非直接來源地。棗陽雕龍碑的西陰紋少部分是受大河村文化的影響而出現(xiàn)的,另一部分可能受到關(guān)中地區(qū)泉護村文化沿著漢水流域的影響而形成。不過大河村文化的這種西陰紋排列方式、用色方法、組合方式,在同時期的文化中卻是獨樹一幟的,單就西陰紋的文化而言很是獨特。
關(guān)于西陰紋的內(nèi)涵,早年學術(shù)界對其并沒有過多關(guān)注,倒是著名文化學者張朋川先生在其專著中作了一個明確判斷,他認為西陰紋是神鳥紋的簡化。近些年,王仁湘先生對這一問題予以了不少關(guān)注,不過在其兩篇論及西陰紋的文章中依然沒有確認其含義(《彩陶“西陰紋”細說》《仰韶文化在江南的蹤影》)。2011年,在其代表性新著作中(《史前中國的藝術(shù)浪潮——廟底溝文化彩陶研究》),他提出了自己的最新認識:“現(xiàn)在看來,它最有可能是魚嘴圖形的局部輪廓,它就是魚的嘴部的一個象征,是彩陶紋飾以嘴代面代體的又一個例證。”
筆者曾認為,其是以部分即1/4魚代表除去魚頭的整個魚的造型(《大地灣等遺址出土特殊彩繪的構(gòu)圖規(guī)則及相關(guān)問題——彩陶新詮之一》),現(xiàn)在看來,王仁湘先生的認識確實是西陰紋的一種內(nèi)涵。
彩陶盆沿面兩個西陰紋中間的圖案較為特別,目前只在鄭州和禹州(圖6)有發(fā)現(xiàn),看來是一種地方色彩的創(chuàng)新紋樣。由于其數(shù)量非常少,對于其含義不容易解讀。仰韶文化彩陶旋紋中有不少是與太陽有關(guān)的圖案或者是神鳥紋,筆者認為,其是太陽大氣光象的造型。
彩陶盆腹部的圖像較為復雜。為利于解讀,依然先把整個圖案視為有間隔的4組。
作為間隔的這一圖案,在廟底溝文化、大汶口文化中都有發(fā)現(xiàn),雕龍碑遺址發(fā)現(xiàn)過其變體(圖7)。分布地域也非常廣,甘肅隴東、關(guān)中地域、河南、江蘇北方、湖北漢水流域都有發(fā)現(xiàn),目前以秦安大地灣遺址的發(fā)現(xiàn)較早。
這一間隔圖案,學術(shù)界目前還沒有特別清晰的解讀,多數(shù)認為是旋紋的地紋,筆者原來認為其是簡化魚的造型,現(xiàn)認為應(yīng)該是花瓣紋的變體。因為若把斜向軸線兩側(cè)的圖像規(guī)整起來,正是一個典型的花瓣紋。之所以錯位設(shè)計,主要是為了畫面的協(xié)調(diào)。
至于花瓣紋的含義,學術(shù)界有的認為其是與河姆渡文化有芽葉紋有關(guān)的一種紋樣(方向明:《崧澤文化的圓和弧邊三角組合紋樣——構(gòu)成、含義和意義》,仰韶文化發(fā)現(xiàn)九十周年紀念大會提交論文),有的認為就是花瓣紋。王仁湘先生認為,花瓣紋與魚紋有聯(lián)系,其可以和圓盤紋組合代表魚頭,甚至認為其是魚的一個象征符號(《史前中國的藝術(shù)浪潮——廟底溝文化彩陶研究》)。
每兩個間隔之間的圖像,宏觀上讀陽紋的話,實際是兩個旋紋,并且是單旋臂的。有關(guān)這種圖案的稱謂、讀法都較為復雜。我們現(xiàn)在依照王仁湘先生的定名方式論之。這種旋紋在全國分布面積非常廣,與本文提及的變體花瓣紋地域類似。其出現(xiàn)的時代較早,依照王仁湘先生的看法,可以早到6000年前即廟底溝類型早期(《史前中國的藝術(shù)浪潮——廟底溝文化彩陶研究》)。
這類旋紋數(shù)量非常多,造型也有所區(qū)別,大河村這一彩繪陶盆的單旋紋,其與晉南、關(guān)中和洛陽的有關(guān)彩陶的旋紋較為相似。單從圓盤紋論,其與廟底溝、泉護村、大地灣遺址的最為相似,以圓盤紋與單旋紋組合來看,其與河津固鎮(zhèn)、汾陽段家莊的最為相似,與陜縣廟底溝、新安槐林的也有少量較為相似,不過主要還是與晉南地區(qū)的最為相似(圖8)。
關(guān)于旋紋內(nèi)涵,認為與花、與魚或與神鳥有關(guān)的都有,并且這些觀點還多把其與圖騰的表現(xiàn)形式予以了聯(lián)系。王仁湘先生則認為其應(yīng)是太陽造型,可以用作魚的眼睛,并認為其總體屬于旋目神的特征(王仁湘:《史前中國的藝術(shù)浪潮——廟底溝文化彩陶研究》)。依照其描述,旋目神或就是太陽神。筆者認為應(yīng)該結(jié)合其中的圓盤紋來判斷。筆者認為,圓盤紋是太陽22度暈上端的切弧和帕瑞弧的組合,仰韶文化中的旋紋可能是表示氣或能量的流行和匯聚(《論大河村遺址一件特殊彩陶上的神圣圖像》)。
大河村遺址這一彩陶盆的圖像,繪制技藝高超,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強,并且人文內(nèi)涵豐富。其已不只是反映了那一時代的技藝,更表明那一時代具有相當水平的藝術(shù)和信仰。從符號學的角度講,這一彩繪圖像及其關(guān)聯(lián)的意旨,不只是達到了藝術(shù)審美的效果,還成為所有與甕棺關(guān)聯(lián)場景中所有具備常規(guī)思考力的人共同希望的表意符號。這一彩陶盆顯然原來不是專門為了這一甕棺而制作的,可能平時是用于禮儀等重要場合,其本身圖像的與精氣神、太陽以及魚可能有關(guān)的符號,都與表現(xiàn)生命力的光華、光芒有關(guān)。其被用于死者甕棺的組成之一,很可能是希望死者能夠獲得生命力,從而獲得關(guān)照和新生!
附記:本項目得到中華文明探源研究項目“中原和海岱地區(qū)文明進程研究”(2020YFC1521602)、2019年度河南省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中原千人計劃”——中原基礎(chǔ)研究領(lǐng)軍人才專項資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