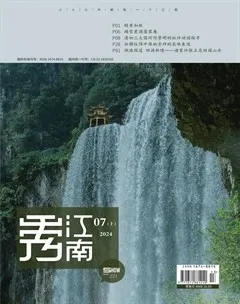暗香如故


園林路的黃昏,斜陽從法國梧桐的濃蔭里漏下來,閃閃爍爍,如掛在枝頭的小星星。光線到底暗淡了。從獅子林出來的游人正在一撥撥地散去,他們如退潮一般很快就會消失。賣水果、小紀念品的流動小販倒格外活躍,在為一天營業額作收官的努力。
忽有暗香飄過,我心中一動。果然看到擦肩而過的阿婆,臂彎里挎著一只不大不小的竹籃。
白蘭花。我收住腳步,還沒喊出聲,她已經轉身,撩開籃子上的蓋布,對我含笑道:“妹妹,阿要白蘭花?”地道的蘇州口音,地道的蘇州阿婆,年輕一點的都叫“妹妹”,年長的喊“阿姨”。
籃子里有一只金屬托盤,鋪著濕紗布,放了兩朵白蘭花和一只茉莉花手環。一根細鐵絲從中間一折為二,兩朵白蘭花正好串在兩頭,又可佩在胸前的紐扣上。茉莉花香味細淡,七八朵串成一只手環,那是戴在手腕上的。她提起白蘭花,道:“妹妹,兩朵都買了吧,就三塊洋鈿。”
清晨的花新鮮、誘人,這時已過了佳期,顏色開始泛黃如老玉,瓣尖隱隱顯出枯焦,到明早,基本就是殘花了。“還有嗎?”我急切問道,阿婆移開托盤,從下層的飯盒里摸出一個沾濕的粉色手絹小布包,托在掌心打開,果然包了最后一朵瑩白光潔的白蘭花,因為水的滋潤,因為沒有風和光的摧殘,還是新鮮粉嫩的模樣。驚喜之下,我爽利地掏出兩個硬幣,她笑著對我說:“謝謝倷!”裙子沒有紐扣,我不知所措,阿婆笑盈盈地說:“我有辦法咯!”她只把鐵絲頂部稍稍向下掰了一下,變成一個小鉤子,果然就妥妥地掛在領口了。我也開心地對她微笑“謝謝倷!”
忽然想起來問她:“這是自家種的嗎?”其實心里已有不抱希望的答案,果然,她低下頭,道:“我自家種的還要好,就是嘸不地方種哉。”
人和花,都是舊時溫和的樣子,又似乎早就不是了。體溫和晚風,激發花香慢慢彌散出來,一低頭就可以聞到熟悉又久遠的渺渺幽香,勾連起一片遙遠的隔世記憶。
白蘭花是她一生唯一擁有過的奢侈品。對我來說,這花香就是她的味道。
大概40年前吧,采光不良的木地板、木板壁房間里,靠窗掛著一個栗棕色的木質相框,形質清妍的年輕女子,旗袍、短發、細細的眉,眼神迷茫,翩然而沉靜,恬淡而清寂,靜如寒潭秋水。這幀照片是我記憶里那團濃重深色畫面的高光點,小時候每天都會盯著看幾眼。那是40年前的她。
她和周圍老太太不太一樣,纖瘦單薄,總穿著立領斜襟收腰的中式褂子,夏天是白色或淡藍的府綢、棉布,春天和秋天是燈芯絨、咔嘰布,冬天藍布罩衫下有駝絨棉襖,永遠的中式黑色闊腿褲、黑色布鞋,她從來沒有穿過皮鞋,沒有穿過列寧裝、滑雪衫……即便進入20世紀90年代依然如此,卻又毫無違和感。可能因為她動作太慢,走路慢,說話也慢,所以跟不上北京時間了。可她明明每天都戴著一只“上海牌”手表呀,不知道是金屬表帶松了還是手腕太細,總像藏在袖子深處,每次看時間都得扒拉下來再塞回去。
她的生活規律本分得近乎禁錮。固定習慣是一早起床后一邊穿衣一邊走到客廳的月份牌前,撕掉昨天的日歷,瞇起眼睛怔怔地愣神,有時念叨“今朝老和尚過江,要落雨哉”“哦,后日立秋哉”……然后洗漱、燒好早飯,從五斗櫥抽屜里找出當天買菜要用的各種副食品供應券,用小剪刀仔細剪下幾張,再挎上菜籃出門去。回來后第一件事是煮貓食,那時有專門賣貓魚的小攤,和蔥姜攤一樣,寸把長的小雜魚一份份分好了攤在巴掌大的樹葉上,她每天買菜的最后一站必是光顧這個攤子,每天的菜籃最上面總有一張樹葉。老屋進深,有時很難聽到動靜,聞到那股清水煮貓魚的腥味,就知道她回來了。
可是她買的菜常受到爺爺的數落,因為蘿卜空心了、茭白發青了、菠菜根好長好老……但這只是單方面的質疑,一般不會引發爭端。菜農都認識她,有的急著回家,就把剩下的便宜賣給她,也難免有不厚道的硬塞一些下腳貨,誰叫她好說話、不精明計較呢?
擇菜、洗菜、揀米(那時的米雜質多,要把混進去的沙子、雜草、稻糠等揀出來)、淘米、切菜、下鍋、上桌……一切按部就班,幾十年如一日。午飯后收拾妥當,她就在客堂間的老沙發上養神,靜坐參妙般,似睡非睡,桌上半導體里的“廣播書場”正說著《啼笑因緣》或是《描金鳳》,冬天半堂的陽光包裹了她,夏天濃蔭覆窗讓人清心寡欲,慢慢地真睡著了。一寣醒來,或是洗刷,或是燒煮百合湯、綠豆湯、山芋湯之類的點心,依時而定。偶爾會等我放學回來,一起到巷口的飲食店吃一碗七分錢的泡泡小餛飩,文火吊的骨頭湯,透明如紗翼的皮子,勺尖蘸一點點水辣椒醬,熱乎乎的,鮮香微辣,殺饞。
她寡言少語又嚴重暈車,活動半徑十分有限,基本不出500米范圍,從不去街坊串門,和左鄰右舍都是“點頭之交”,親戚家也很少去,似乎只有一次偏離了軌道。某個初冬的下午,她直到晚飯前才回來,難得稍帶興奮地講述:“排隊格人多是多得唻,儕為仔看看老法頭里皇帝用格物事,格個西洋鐘真咯好看……”她的表達能力不足以再現蘇州博物館那次舉辦的“故宮生活文物展”的盛況以及描繪展品的水準,但是在我家相當令人震撼,因為我們不知道她何以知曉這個展覽,也不知道她還有這樣的興致和好奇。
其實這樣想是不公平的,如今我剛剛開始理解。她的一生都在蘇州城里度過,作為一個小綢布商的長女,這位大小姐的待遇是幫著家庭照料弟妹,以致成為終生職業。婚后,丈夫長期在上海南京路的老字號工作,她一個人獨自拉扯了4個孩子、7個孫輩,甚至還在特殊時期為弟弟帶大了兩個女兒。她一生的職業就是“家庭婦女”,一生的社會角色是“胡師母”。可是歲月并非靜好,她也有過幼子夭折的痛,有過婚姻的危機,有過一個人帶著一幫孩子“逃難”的驚魂,有過丈夫和女兒失和引發的苦惱,但是她從來不爭不怨、不悲不喜、不提不說,似一口古井,深邃無波。那些從前,我只能從長輩的閑談中抓取一些碎片,卻猶如水面的閃金碎玉,虛浮遙遠。
只有她身上的一縷暗香是清晰且真實的。
在春夏濕答答的梅雨中,老房子里終日彌漫著令人抑郁的霉塵氣,所幸這時江南“夏日三白”開始出現在街頭。茉莉香淡,如二八少女,羞怯柔弱;梔子芬芳,如二十多的青年急于引人注目,凋零快還引蟲。只有白蘭花才是真正的主角。它不妖不艷,優雅沉靜,花型別致,即便盛放,厚實的花瓣始終內斂低垂,不恣肆、不張揚,每朵花的內心似乎都收藏了一份雅致而又寂靜的心事,不愿意讓人看到。即便焦枯死亡,仍保持著最初尊嚴的形狀,香氣沉靜、從容而溫和,正如中年以后的女子。她隔天就會買一朵掛在衣襟的盤扣上,晚上用手絹包好放在枕邊,這縷幽香和藥水肥皂、花露水一道,構成了我記憶中關于夏天的味道。
還有秋天的桂花、冬天的蠟梅,她都會折來插在客廳的天然幾上,香氣四溢,即便落花也收集在一只小白瓷碟里清供。她會在醬汁肉上市的第一天去排隊,會在清明前后去巷口的茶葉店給爺爺買上二兩新焙的碧螺春,會在端午編一只小巧的五彩絲線袋,裝一只最大的咸鴨蛋掛在我的胸口……
每天午后或黃昏,她還是坐在那只舊沙發上,不過手里是一把蒲扇或一只鹽水瓶的輪換而已,蘇白、三弦和琵琶叮叮咚咚地飄來又飄去,她的一年似乎就是一天,一生也就是一年而已。
我曾經如此不屑于這樣的人生,沉悶、單調、閉塞、蒼白……毫無光彩,但是當生命的年輪一圈圈加密,我開始明白自以為是的荒唐。她不貪嗔、不執念,從容安詳,每天活在自己的責任和義務里;她不苛己、不責人,自在靜美,千般滋味歸于一處;她懂得惜時惜福,用順其自然、心甘情愿的態度過隨遇而安的生活。
歲月靜好,不在歲月里,在心里。
她胸前的那朵白蘭花,似乎也帶了拈花微笑的禪意。40年過去了,暗香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