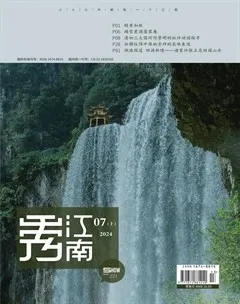踏雪煮酒蓮蓉庵

明萬歷年間,千年京杭大運河依然滔滔不絕。它流經江南水鄉時,分汊出一條錫澄運河,由南向北,通江入海。古老的蓮蓉村,被運河孕育的蓮溪滋養了數百年,隨著華氏大族的興盛,名字改成了北七房。歲月悠悠,北七房人才輩出,古村演變為與附近的秦巷、禮舍齊名的街鎮。
古鎮出名士。有史記載:街東的鄉紳華義中,字叔卿,號瑤階,生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四月十一日,卒于天啟四年(1624年)二月初二,享年七十七歲。華義中少時考取縣學,擅詩文,精通佛、老二學,深得同鄉大賢葉茂才、武進名士錢啟新先生贊譽。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華義中斥資建造蓮蓉庵,落成后占地十畝有余,其中,各類建筑物有七畝之多,莊嚴肅穆,氣魄宏偉。庵內供有彌勒佛、三世佛、觀世音菩薩、伽藍菩薩、文昌菩薩、地藏菩薩。另建別院,供有玉皇大帝、大老爺和福祿壽三星。未久,蓮蓉庵改稱蓮蓉禪院。
四百多年前的某個冬日,大雪飄飄揚揚,整個蓮蓉庵粉妝玉砌。65歲的瑤階先生禮佛之心甚堅,不顧天寒地凍,仍如往常一般赴蓮蓉庵早課。早課結束,步入殿旁廂房少歇,房內有銅鏡一枚,先生對鏡稍整衣冠,見鏡中人已是皓首蒼顏,想起李白的《秋浦歌》中“不知明鏡里,何處得秋霜”,未免暗生喟嘆。稍坐即起,行至室外,見院中植有梅樹數株,殷紅點點,暗香徐徐。瑤階先生精神為之一振,遂令仆人溫酒。凜冽之中,瑤階先生腳踏皚皚白雪,手執銅壺自斟自飲,三杯米酒入喉,一首《白發吟》油然而生。詩云:
白發生頭三十年,而今鏡里盡皤然。
歌聲日日如狂叟,酒興年年似醉仙。
八戒堅持香火印,六時莊詠樂師篇。
其余都被春收拾,不是閑游即醉眠。
吟罷,取筆墨紙硯,一揮而就。吩咐下人,急送隱居于運河之畔、石幢橋下的同鄉大賢葉茂才點評。
據《明史·卷二百三十一》記載:葉茂才,字參之,號玄室,世稱閑適先生,無錫北鄉石幢人。萬歷十七年,與同鄉高攀龍、陳幼學赴京會試中舉,初授刑部主事,累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生平以正直醇德著稱,為東林八君子之一。
萬歷四十年(1612年),葉茂才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上任不久,興利除弊。但此時官場亂象叢生,朝廷官員以權謀私,黨爭十分激烈。葉茂才義憤填膺,先上《國事宜參公論》,駁斥“扶小人抑君子,護奸雄而禍天下”的行為;又上《早賜禎斥以釋群疑》,聲明自己素無依傍,更沒有受任何人主使;續而再作《旁囂說》,指斥某些官員身居臺諫要職,自以為天子耳目,只有他們才有權論是非、議朝政,其他官員的建言都被視為“旁囂”。最后,就“年例考選”中的嚴重弊端,上書鄭太宰說,考選官應由正直的人擔任。然而,官場黑暗,耿直的葉茂才不斷受到攻擊和排擠,自覺孤掌難鳴,無法施展才學,只好稱病辭職。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年初,葉茂才離職回到無錫,隱居于石幢。因欣賞瑤階先生才學,常攜同錢啟新等名士到蓮蓉禪院與瑤階先生喝茶、飲酒、作詩、論文。
華義中的《白發吟》送到葉府,葉茂才讀后感慨萬千。雖然石幢距蓮蓉庵只有數里,但天寒地凍,行路不便,葉茂才執意踏雪前往,急欲與瑤階先生相見。一路上,寒風凜冽,又飄揚起鵝毛大雪,57歲的葉茂才先生左搖右擺,喃喃自語,幾首《和瑤階華溫白發吟》隨口而出,詩云:
(一)
記得高門坦腹年,雙眸炯炯發黟然。
紅顏笑我成槁木,白首隨翁訪赤仙。
休沐喜聞招隱曲,延齡欲叩養生篇。
蓮蓉湖上春常在,好傍花蔭一醉眠。
(二)
自古豪華有盡年,休爭腐風各囂然。
紅塵萬里迷歸客,苦海千重隔洞仙。
往圣最嚴迷復戒,后儒誰識訂頑篇。
堪嗟皓首沉酣者,何日長風醒醉眠。
(三)
少壯骎骎到暮年,邯鄲夢里未醒然。
衡門望盡黃金屋,鼎食還期姑射仙。
稚子便教鼁黽讀,白頭猶戀蠧魚篇。
不思石火流光短,郤笑希夷日日眠。
(四)
老去追思少壯年,舊游風致尚依然。
難將白發回青鬢,只合嬰兒學老仙。
多病或因馳妄想,息妄兼欲廢詩篇。
從今徹底澄清去,愿法真人醒亦眠。
(五)
憶昔垂髫總角年,心如秋水意超然。
俄從文苑塵多士,漸入膻途近醉仙。
蒙養已非初筮質,還丹幸有識仁篇。
年來衰病渾無事,只向南窗枕藉眠。
華義中得知葉茂才前來,早已煮酒相候。兩位名士惺惺相惜,把酒言歡。興之所至,渾然忘卻身份、年紀,在雪地里手舞足蹈,如癡如醉。最后酒意上涌,互執雙手,醉臥在蓮蓉禪院的草堂之上。
四百多年后,我有幸讀到華義中、葉茂才兩位先生的大作,聯想到故鄉的蓮溪、蓮蓉橋和那座早已失去暮鼓晨鐘的蓮蓉庵以及大運河畔的各種文化遺存,不禁為家鄉厚重的歷史文化感到深深的自豪。在詩情畫意之中,我亦當回到夢里的北七房,喝一壺鄉人自制的老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