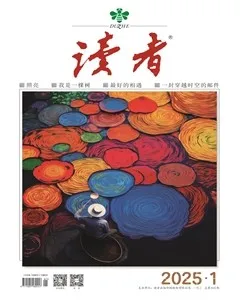《西游記》悟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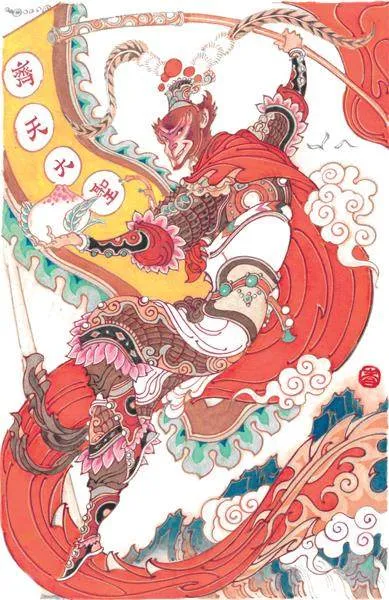
◆孫悟空天不怕,地不怕,玉皇大帝不怕,龍王不怕,閻羅王不怕,是真的無所畏懼。然而,他敬畏唐僧。之所以敬畏,不僅是因為唐僧會念《緊箍咒》,更為重要的是唐僧擁有慈無量心、悲無量心。正是因為有這種心,唐僧才能把孫悟空從五行山的重壓下解放出來,也才能把豬八戒、沙悟凈和孫悟空吸引到身邊,組建起一支尋找真理的隊伍。而孫悟空之所以令人佩服,也在于他不僅“無畏”,還“有所敬畏”。
◆在中國的神話故事中,人神之間及神魔之間只有一步之遙,人隨時可以變成魔,神也隨時可以變成魔。豬八戒原是天神,號稱天蓬元帥,因犯了錯誤(調戲嫦娥),就被罰入下界,成了妖魔,并鬧出入贅高老莊的丑劇。但他走上取經之路后,逐步改邪歸正,最后成為“凈壇使者”。沙悟凈原是天上的卷簾大將,只因摔破了玻璃盞,被貶入下界變成了河妖。中國文化相信天人合一,神與人、神與魔當然也可以合一。與孫悟空搏殺的妖魔,很多原來是神與佛的坐騎、侍從或弟子。《西游記》告訴人們:沒有永恒的神仙,也沒有永恒的妖魔,只有永恒的人性。
◆在中國文學中,我最愛兩顆心靈:一顆是柔性的——《紅樓夢》中賈寶玉的;一顆是剛性的——《西游記》中孫悟空的。兩顆心靈原先都是石頭,通靈后卻變得至柔與至剛。至柔者在脂粉釵環的包圍中生活,至剛者在妖魔鬼怪的包圍中打拼。盡管環境極為不同,但二者都是通向至真、至善、至美的詩心。所謂詩心,乃是我們所夢想、所向往的跳動于未來的心靈,是人類此刻還不具備,但以后可能擁有的心靈。這種心靈,簡單混沌,卻很豐實。這種心靈的現實感并不強,但它又傳達了生活在現實中的人的向往。
◆歌德筆下的浮士德,與魔鬼打賭:浮士德一生進取,倘若愿望被滿足即成魔鬼的俘虜。孫悟空一路打過去,也在與魔鬼打賭,但從未當過魔鬼的俘虜。他與魔鬼賭的首先是眼睛,能看穿偽形即勝利,不能看穿即失敗。唐僧看不穿,因為他只有經書的潤澤,缺少煉丹爐的煎熬。孫悟空之所以戰無不勝,除了仰仗老師的傳授,還仰仗煉丹爐的磨煉和對手帶來的磨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中讓主人公講了一句話:“我只想證明一件事,就是,那時魔鬼引誘我,后來又告訴我,我沒有權利走那條路。”讀《西游記》,看到唐僧戰勝各種誘惑時,我總是想起這句話。唐僧之所以神圣,就是因為他明了自己選擇的那條路是正確的,而且一路走到底;并明了,從此之后他再也沒有權利走別的路,包括榮華富貴之路。
◆孫悟空到西天取經,一路打拼,一路吃苦,但也一路成長,尤其是心靈的成長。他西行的最大成果,不是被封為“斗戰勝佛”,而是發現了宇宙和人間的真理——天地不全。天不全,所以要補天;地不全,所以要填海;佛經不全,所以經書被打濕了也不必懊喪;人不全,所以往往辨別不出妖魔;自我也不全,所以才會自稱“齊天大圣”。孫悟空道破的“天地不全”哲學,乃是無字真經,這是孫悟空悟到的真理,也是吳承恩悟到的真經。
◆唐三藏、孫悟空、豬悟能、沙悟凈,我們可稱他們為“西游中人”。盡管他們性格、性情差異很大,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沒有機心。《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劉備、孫權、司馬懿等,其性格、性情同樣差異很大,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充滿機心,全是“巧偽人”。他們不是會“變”,而是會“裝”,每個人都有一百副以上的面孔。
◆《紅樓夢》的基調為優美,《西游記》的基調為壯美。前者典雅,后者崇高。兩部小說的美學風格雖不同,但都有大慈悲,均佛光彌漫。《紅樓夢》告訴人們,若要解脫,唯有放棄,放棄功名利祿等妄念。《西游記》則告訴人們,若要擺脫苦海,唯有拼搏。二者都有道理,只是《西游記》更積極。
◆唐僧師徒以為走到靈山,取了經書,這些經書便可普度眾生,拯救世界。但他們沒想到,在靈山竟有人向他們索取禮物(人事),這些人也無法超越功利之局限。小說最后這一筆,是極深刻的一筆,它提醒人們,靈山也并非絕對光明之地。光明在哪里?光明或許在我們自己身上。
(曼 殊摘自湖南文藝出版社《西游記悟語》一書,陳岱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