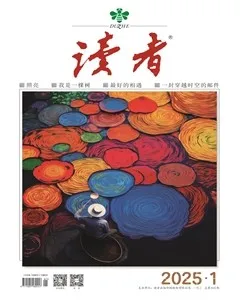白色扶郎

一個人褪去最后青澀的階段,有點兒像螃蟹發育的尾聲。當最后那層殼行將脫落,年輕人憋不住,會變得更加張揚、更有主張。我一進入那一時段,就遇到了麻煩。
一九八二年大學畢業后,在一所中學教了近一年語文的我,覺得應該離開了。當時,凡向學校提出調動的,幾乎都不被允許。校長對我說:“你一進校,我們就讓你一個新教師教高三,這在本校史無前例,你還不珍惜。”
我當時擬調去的單位,是鄰區的一所業余大學。我看重的是,在那兒我的時間將相對自由,不用坐班。經介紹,我上門去拜見該校姓金的校長。當時,我還是稚嫩的。談了一個小時,就自動拎著秤桿,把自己的全部斤兩,都稱給金校長看了。他一直在微笑。
我第二次去時,金校長說:“你所在的中學有位副校長姓姚,你們區教育局局長姓陳,對嗎?”他在暗示,為了我的調動,他已在第一時間出手了。他還說,調動工作不容易,做兩手準備,是最好的。
這次,我在他的家里,發現了兩本刊有我寫的小說的雜志。
金校長當時五十歲,未有婚配。家里的打理,并非長期單身男人的經典范式。既不是細致到似有潔癖,又不見散漫隨意。那天,他家的圓桌上有一個水晶玻璃花瓶,應是老貨,插著滿滿一束白色扶郎。花很新鮮,水也清澈。白色扶郎,淺綠的單支根莖,像天鵝修長的脖子一樣脫俗;那上面的純色花朵,不艷不媚;率真的白色,讓人心動,含有異樣的張力。
他的家里,沒有字畫和擺飾,墻面空空白白。唯有一張泛黃的照片,裝在書桌上一個小鏡框里:后生戴金絲邊眼鏡,穿戴齊整,頭發向后反梳,有世家子弟氣息。這應是他留洋時期的照片。
一躍,他已年過半百。
調動成功的概率很小,但這位不來半點客套,又善解人意的前輩,真的特別。他考慮問題時,切入方式非比尋常;做事直逼目標,又不輕慢他人;該有原則時,他也會堅持。比如,他說:“是的,我不喜歡有人在這里抽煙。”
我被分配到這所中學后,到此時下半學期就快結束了。
在三樓的外廊,我看著下面三塊無人的籃球場,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多久。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下,是人事干部,她通知我盡快去局里辦理調動手續。一件難事,就這樣沒頭沒腦地做成了。
到業余大學報到,我以為金校長會說起,商調是如何實現的,他卻只字不提。當初我們共同面對一個難題,最后完全靠他一人破局,他卻不愿讓我知道他的付出。他讓我領教了什么叫淡泊。從記事起,我始終都在很濃烈地追逐,未見識過這樣的處事境界。金校長像魚缸里最從容的那尾魚,飄然的長尾,總是逸逸擺動,仿佛生存從無緊急。
我開課后,金校長來聽了三次,沒有一句點評——他應該是滿意的。
有一次下班,我和他一起步行回家。他問:“你有興趣成為一個教育管理者嗎?”我說:“我太崇尚自由自在,不合適的。”他說:“你更想當作家吧?”我尷尬地笑了。有句俗語叫“三根手指捏田螺”,此刻,我這只田螺在自己身上感覺到了金校長的五根手指,不止三根。
我所授的課,會安排一個去外地采風的環節,全班同學去了普陀山。當晚在招待所,大家舉杯暢飲,氣氛非常熱烈。雖是班主任,但學生都比我年長,我心里是沒有師生界線的。
大家還是喝過了頭,有位長我多歲的女學生哭了。可能另有心事,那一刻,她需要一點兒安慰。她擁住我,我確實不可能因怕被誤會,就刻意避讓。我輕拍了她的肩頭。大家都在桌邊,我想這樣應該不會被曲解。但是,這個場景后來有了三種以上的描述。而且側重點不同,再加上一些夸張和暗示,性質就截然不同了,尤其對不在現場的人而言。
回到上海,有好事者興奮地做了點兒傳播上的努力。三傳兩傳,這事就說不清楚了,影響真的不太好。我想,等待我的,可能是一次警示性約談。多天過去,沒有動靜。有人告訴我,校長直接找學生了解過情況,人數不少于十名。最后,事實清晰了,校方對我無任何責難。我明白,金校長是有所擔當的。并非所有校長,都會這么做。
上了兩年課后,我對金校長說:“我的成長期全部局限在學校、局限于上海,我想去一個遙遠的地方。”他一下沉默了。
我聯絡好支邊事宜后,新疆有關部門的干部來學校致謝。金校長說:“也許新疆更需要他,他也更需要新疆,學校只有支持他。”
我在他的話里,不只聽到一個校長的辭令,還感受到父輩的厚愛。金校長,是我見過的肌肉很不發達的男子,但他富有洞穿現象的智慧。他沒有雄渾的揮灑,卻有一種精致的力量。
兩年后,我從新疆回來,決定出國。辦妥后,我去和金校長話別。他還是那樣,在可說可不說的地方,一定是不說的;在可以微笑,也可以不微笑的時候,他一定是微笑的。
臨別,他說:“你每年寄一張新年賀卡給我,我不一定回復,這并不意味著我沒有收到。”此后,我每年依約寄出給金校長的賀卡。有一年,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告訴我他換了新址。接著,又一切照舊。
在海外很多年后,我回到上海。沒想到,金校長已去世多年。我的賀卡,一直朝著他而去,其實他早已不在。
有情感的地方,就會有離別之苦。
我和金校長的交往,無一餐一飲,平淡到僅是一些對話的碎片。然而,他極其純凈的人格,如光芒照耀過我。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給了我第二雙眼睛,用以關切庸常中的清濁。人世的畫面,由此而不同。
我一直在尋找他的墓地。他沒有子嗣,學校的職員也數度更替,漸漸地,我就失去了頭緒。我問過很多上海的陵園,都沒有他的名字。
相信有一天,我會找到他的安息之地。
在墓地,我總是說不出話來。在他的墓前,我也會無言。但我手里會有一束白色扶郎,它將是我追念他的全部語言。
校長,我會來見你的!盡管,你沒有再告訴我新址。
(思 心摘自文匯出版社《第一個離別者》一書,黃思思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