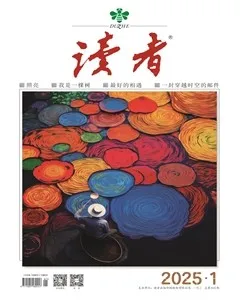情書

我一個哥們兒,大學時瘋狂追求他們系的“系花”,那個女孩是富家千金。當然在那個年紀,我們這些“廢材”無法對與所謂的富家女交往有任何具體的考慮,以為就是偶像劇里的窮小子騎車帶小公主在山路上歡快地騎行。若到我現在這個年紀,便不會再感到驚訝,知道這種階層上的差距,是物理學意義上的,時間到了他們必然分手。
我這哥們兒是個非常重情義的人,我們都喊他“蕭峰”。真要分手的時候他非常痛苦,時間拖得頗長。后來是那女孩竟懷了別人的孩子,他才決定放棄。我們這些兄弟多少都受過他仗義的幫助。比如,考試時試卷讓我們看一下,或者我們惹到一群學長,學長們來教室找麻煩時,他堵在門口,展現出武松那樣的氣勢,學長們摸摸鼻子走了。這時看他一個英雄好漢,喝醉了哭成那樣,像玉山崩頹,我們都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他拿了一個大紙袋,里頭塞滿厚厚的信。他說那女孩真夠絕情,把從相戀之初到分手,他寫給她的情書全退了回來。他不想再看到這些靈魂已被吸光的情書,請我幫他保管,也許等很多年后再還他。
幾年后,我們各自結婚。他的妻子是個好女人,我們也替他開心。后來我搬了家,從陽明山搬至深坑,之后妻子生了兩個孩子,當時生活真是亂成一團。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我好像把他托我保管的那一袋情書搞丟了。我完全想不起我把那袋情書擱哪兒了。我爬上收舊物的閣樓找了好多次,就是找不著。但轉念一想,他們夫妻現在感情很好,他應該不會再來要那段情傷的證物了吧。后來他們一家來我家做客,兩家的小孩在一塊兒玩,大人們則坐在沙發上聊天,我心里也晃過一個念頭,他的妻兒們不知這屋子里的某處,藏著他們家男主人生命中的一段時光,最刻骨銘心的愛之證物。
幾年后我又搬家了,搬進城內。那房子借給一個好友住了幾年,之后這個好友也搬走了。他留下的雜物,和我們當初留在那房子里的雜物,像時光的化石巖層。當初搬離時舍不得丟的嬰兒車和小孩的衣服、玩具,現在都因孩子們已經長大,根本用不著了。還有一摞一摞的書,發霉的,被白蟻蛀成粉屑的。有一天,我找了清理公司,把屋里垃圾似的東西都清理掉了。那房子像一顆蛀牙被拔掉后留下的槽洞,空在那兒。
有一天,這哥們兒突然約我到咖啡屋,聊了幾句,問起當年那一大袋子情書。我一時反應不過來,不知怎么解釋它們在好多年前,可能就混雜在雜物之中被清理掉了。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是在哪一次搬家中找不見了。但我也有點兒惱,我們的孩子都十五六歲了,眼下我們就是兩個挺著大肚腩的大叔,你這時來跟我要當年托我保管的那些年輕時的玩意兒。確實是我沒好好收藏它們,但這和這十五六年難以言喻的艱難生命,根本無法相提并論嘛。我騙他說,我把它們藏在深坑鄉下房子的閣樓里,要找可能得費些力氣。
我哥們兒說,他之所以會在這時突然想到那沓情書,是因為輾轉從先前的大學同學那兒聽到,那個女孩,不,女人,那些十幾年前情書原本的主人,在不久前,罹癌過世了。說來四十五六歲,不前也不后,不知這樣算過了一生,還是半生。
(西 陸摘自河南文藝出版社《純真的擔憂》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