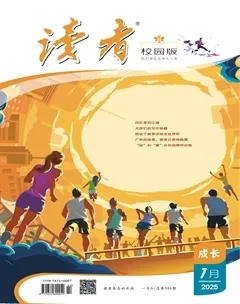那些讓人垂涎的課文

有位未曾謀面的朋友說:“看你把菜園里再平常不過的蘿卜青菜寫得津津有味,就知道你也在鄉(xiāng)野長大,想問你一個問題。你當年念書時,有沒有因為課本里寫的那些好吃的而把口水滴在課本上?就算我經(jīng)常吃咸鴨蛋,可讀到課文里汪曾祺寫的高郵咸鴨蛋,還是口水直冒啊!”
我盯著這封郵件看了很久,身體有點癱軟,像是被人隔空抓了現(xiàn)行,雖然時過境遷,依然有點手足無措。不過,我那時雖然常常垂涎欲滴,可還不至于把口水滴在課本上。主要是因為,課文里講的大部分吃的,我沒聽過也沒見過,無論我怎么發(fā)揮想象力,也無從知曉它們的味道。
我們那時的課本里沒有講咸鴨蛋的這篇,我一直記得的是《草地晚餐》里有一句:“藍色的火苗舔著鍋底。”這個“舔”字,老師說作者用了比擬的修辭手法,把火苗的樣子逼真地描摹出來了。我當時想的卻是:火苗舔鍋底,就像我舔玉米糊湯碗一樣,火苗也餓嗎?
有篇課文里寫道,列寧在監(jiān)獄里寫秘密文件,要是被看守發(fā)現(xiàn)了,就得延長監(jiān)禁期。列寧想了個非常巧妙的辦法,他把面包捏成墨水瓶狀,裝上牛奶,在書上空白的地方寫字。等牛奶干了,什么也看不出來。書送到外邊,被同志們拿到后,只需要在火上烤一下,字就會顯出來。看守來了,他就把“墨水瓶”放進嘴里大嚼起來。
這一段描寫讓我的嘴巴動了好幾次,同桌張二狗打小報告說,他聽見我咽了口水,“咕嚕”一聲。老師回了一句我們聽不懂的話——“過屠門不大嚼才不正常咧。”
老師也沒有見過面包,不過他努力跟我們解釋說,面包就像我們家里蒸的苞谷面發(fā)糕,軟塌塌的。我們問他:“面包要是軟塌塌的,列寧能裝得住牛奶嗎?”老師攤開手笑了笑,鼓勵我們好好念書,將來“面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后來,我才曉得,他說的是一句電影臺詞。
課文里的楊梅、荔枝、茴香豆,我之前都沒有聽說過。《挖薺菜》里說:“最好吃的是薺菜。把它下在玉米糊糊里,再放上點鹽花,真是無上的美味啊!”我們也吃薺菜玉米糊糊,我卻沒覺得它好吃。倒是《麥琪的禮物》里所說的,“到了七點鐘,咖啡已經(jīng)煮好,煎鍋也放在爐子后面熱著,隨時可以煎肉排”,我想,那一定是無上美味。
魯迅先生在《閏土》里寫閏土手持鋼叉朝猹扎去,并沒有讓我感到驚奇,我更喜歡前一句:“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
我們這兒有南瓜、黃瓜、葫蘆瓜,可誰也沒見過西瓜。那時我已大一些了,總問老師吃的,有些不好意思,西瓜的事情就放在了心里。
有一年學校來了一位年輕的老師,剛剛從師范畢業(yè),姓龍。龍老師教數(shù)學,考試時他不監(jiān)考,每次都在蠟版上刻四句話:“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因為他寫了“瓜田”,我有一次就問他瓜田里種的是啥瓜。他笑著說,可能是香瓜,跟西瓜一樣,都是甜的。那時,我們對“甜”這個字簡直著迷。他老家在商州,那里有西瓜,他比畫著:圓圓的,個頭好像比南瓜還大。我們問他好不好吃,他說:“甜得太太——”他的意思是比“很甜”還要甜。我吃到西瓜時,已經(jīng)念初二了,我們那兒新修了公路。有一回,姑父去西安,買了一個西瓜,翻過秦嶺運回來。等他回來,瓜瓤已經(jīng)化了,倒出了一大盆汁水,有點餿了的味道。這讓我對西瓜的印象不佳。不過,后來吃到的一個新鮮西瓜立刻叫我服帖了。
那時的秦巴山地,看山是山。沒有公路之前,偶爾來個貨郎,哪怕就是拿出一卷花線,都足以讓我們感到稀奇。如果大人肯從他那兒買幾顆水果糖,我們能高興好幾天。后來看張岱在《西湖夢尋序》里寫:“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盛稱海錯之美,鄉(xiāng)人競來共舐其眼。”我想,這心情我們也有過,不過“共舐其眼”就有點兒過了。
好像是上高中時,有一篇課文叫《我的叔叔于勒》,莫泊桑寫的。我老是忘不了吃牡蠣那一段:
“父親忽然看見兩位先生在請兩位打扮得很漂亮的太太吃牡蠣。她們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著牡蠣,頭稍向前伸,免得弄臟長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動,就把汁水吸進去,蠣殼扔到海里……”
我們這兒離江遠,離海更遠。我十分好奇——牡蠣到底是啥啊?
我好奇了很多年。頭一回去廣東,朋友請食生蠔,我差點吃吐了,那軟軟的東西真是讓人不踏實。朋友說,牡蠣和生蠔差不多。我努力多次,想把它吃出點兒味道來,可實在做不到。一個在山里長大的人,味覺始終忠實于山野。
(本刊原創(chuàng)稿件,老老老魚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