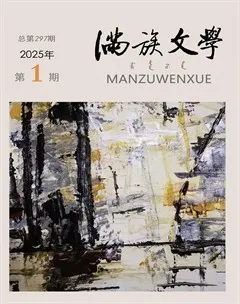那件事情,先鋒小說
于曉威:陳鵬兄好,很久就想跟您聊聊了,惜乎多年您居云南,我居東北,相隔太遠。上次云南開會,也是匆匆一見,我們似乎都太忙了。好在多年,我覺得我們彼此還算是心氣相通。這次讀到您的中篇新作《下午,翠湖》,我很興奮,您對自己的文字和小說要求很嚴,寫得也不多,這部小說讓我有一種久違的感覺,它仿佛集合了羅伯-格里耶、略薩、米蘭·昆德拉以及元小說和反小說的很多后現代主義敘述特點,用您文中反復嵌入的句子來說,“那件事情”,套用一下,我覺得這是一次事件,是關于當下小說的一次美妙的事件。作為先鋒派小說家之一,您覺得自己這么干的心得是什么?您是否在意別人能否讀懂這部小說?
陳 鵬:謝謝曉威兄對這個小說的肯定。其實我對自己每一部小說都有要求——盡量,盡量不太一樣。既和諸多同行小說不太一樣,和自己上一部小說也不太一樣,雖然,很難,也多有線性的“講故事”的小說,但基本上,我每一個中短篇都盡可能體現“元敘述”特色,即關于小說的小說,袒露寫作者的小說。這個觀念在我小說中根深蒂固,我想,這既是馬原對我的影響(我從不避諱他對我的影響。了不起的馬原),更與我十余年記者經歷有關。新聞是對事實的再現,但這行干久了,你會越來越困惑于你面對的現實——到底何為現實?你選擇的就是現實?還是,你沒寫下來的才是現實?這就很讓人沮喪了。也就是說,它逐步構建了我的世界觀:怎么看待世界。我認為現實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所謂真相,永遠不可觸及。這構成我諸多小說的底色,法國“自我虛構”一派也給了我重大啟發。是啊,就應該這么寫小說,把自己也寫進小說,讓你虛實難辨,真假難分,這不就是敘事的快樂之一?至于格里耶,他的《為了一種新小說》是革命性的,我最近創辦發行的刊物就叫《新小說手冊》,就為了一種“不太一樣的”小說。略薩的結構主義對我影響不大,米蘭·昆德拉的哲理或復調小說更是另一個路子了……我的確不太在意讀者能否“讀懂”,實際上,小說家最在乎的還是自我完成,不會考慮讀者,這么說絕非夜郎自大。試想,自己都不滿意不盡興,寫作還有意義嗎?其實因為二十年記者經歷,我的小說向來是“好看”的。
于曉威: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您覺得先鋒文學的使命完成了嗎?它當下是否還有意義,有的話,是什么?
陳 鵬: 某種程度上完成了,以莫言獲獎為標志。但骨子里,從更深遠的文學史意義上看,又遠沒有完成。當年馬原洪峰蘇童余華格非們的寫作抵達過世界級高峰,足以與最優秀的文學等量齊觀。我這么說不是瞎吹,自信有海量的閱讀撐著。我相信馬原的“敘事圈套”、蘇童的“人性之惡”、余華的“死亡敘事”……都好,都是了不起的突圍,讓中國的小說突然掙脫桎梏呈現出應有的精湛的敘事面目,而非僅僅只有“革命現實主義”一脈。惜乎后來沒走下去,沒能走得更遠(馬原小說例外),個中原因太復雜,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文學自身的……先鋒之后,“新寫實”崛起,一種向世俗立即投懷送抱的小說運動開始了。先鋒小說最大局限或許在于,小說的“技”被當成了小說的全部。但技術是不可窮盡的。小說,說白了關乎人類最本質的存在,因此如何以“技”言“道”,尤其講述人類共通的存在之道,更考驗作家的雄心與能力。這的確是一項長跑賽事,不容馬虎,也不容游移、取巧,要的就應該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在這一點上,我不太喜歡的喬伊斯反倒是個正面典型——死磕到底,語不驚人死不休,必須撂出震世駭俗的文本,充滿想象力和原創性。不得不說,當年我們的先鋒作家短時間內博得大名之后,過于輕巧、急切地退回了世俗敘事一路,這與美國的唐·德里羅、約翰·巴思、巴塞爾姆們一輩子孜孜以求比起來,就太讓人遺憾了……固然,作家自己沒有所謂“先鋒的義務”,但先鋒運動不該過早凋謝,先鋒小說和先鋒技法早該成為我們傳統的一部分,應該有更多“好事者”跟上來。可惜啊,我們好像輕輕松松就為先鋒派們留下的遺產投了反對票,雖然嘴巴上常說,那些玩意兒早就是常識了,還有什么稀奇?問題是,一旦很多有先鋒氣息的小說出來,大多會遭到主流期刊的拒絕。先鋒遺產,逐漸成為被埋葬被憑吊的殘骸,僅供觀瞻而已。實際上,好小說大多基于反叛,否則原創性就無從談起。這方面我多次聊過,法國小說就是很好的榜樣,一直在反叛,在前進,如去年諾獎得主安妮·埃爾諾的小說,多么新鮮生猛,多么深刻而本質。相比之下,我們太偷懶了。原因很多,如國情、觀念,等等。莫言說我們都是講故事的人也誤導了很多人。實際上他正話反說,一位一流的小說家又怎么可能僅僅滿足于講故事呢?當下,我們還是需要往前走,繼續探索,繼續反叛。好,問題來了,眼下到底該反叛什么呢?——對一種庸俗的故事性寫作發起挑戰,算不算?向埃爾諾這樣的寫作致敬,算不算?答案是肯定的。它們將逐漸改變我們的文學生態。
于曉威:從您這部小說散漫而精致的敘述中,我讀到了每一個人物生命的某種無力感以及尖銳的疼痛(包括敘述者),包括況味,它是一個復調的東西,折射許多“能指”與“所指”,結構或解構。呂克·赫爾曼和巴特·維瓦克在其所著的《敘事分析手冊》里,提到過“敘述代理人”的問題,這部小說的視點、人稱都有很多變化,您覺得在小說創作中,敘述者以及敘述重要嗎?假設一下,它在一篇現代小說創作中占有多大比重?為什么?
陳 鵬:這個問題太具體了,我持保留意見。哈哈。簡單說吧,敘述者的聲音有時退居幕后完全讓位于小說敘述,比如加繆的小說。也有敘述者的聲音遠大于小說敘述的,比如我推崇備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種極致的個性強調小說人物、故事的獨一無二,它必然構成一部偉大的獨具個性的藝術品。注意,小說是最難最復雜的藝術,絕不僅僅是故事。它是它自身,不會是某種功能性使用手冊或人間生活指南,因此,個性,藝術性,豐富,內省,終將構成一部小說杰作的全部。
于曉威: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對當下文壇的小說寫作滿意嗎?為什么?
陳 鵬:不太滿意。這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寫作,我們不能隨便就把自己摘出去。我上面大概說了原因,我們的文學確有單一之嫌,太重視線性的現實主義法則,可是,別忘了,卡夫卡也是現實主義之一種啊,我們應該把諸多現代派后現代派的豐富遺產都“拿來”,不是拒絕,不是僅僅保留某一種“故事現實主義”,那會成為“故事會”的升級版甚至不如“故事會”。
于曉威:您什么時候想當作家的?您自己寫小說時的初衷是什么?
陳 鵬:大概十四五歲就在做作家夢啦。我從小踢球,大概就是從初二初三開始吧,訓練之余我埋頭寫小說,胡編各種好玩的故事,古代的現代的。隊友爭相傳閱,這種寫和讀的互動對我都是刺激。寫小說的初衷簡單至極,就是迷戀文學創造的那個無與倫比的世界,它和現實截然不同,太獨特了。我記得高二高三我不是忙于高考(那時候一邊訓練一邊備考),而是拼命看小說,《小說月報》每期都買,同時也讀經典,沉醉不已。一邊讀一邊繼續寫,十七歲在《滇池》發處女作,激動壞了。一個中學生能在《滇池》上發小說,算是大事件了,我從此“入坑”,哈哈。
于曉威:您曾做過著名的《大家》文學雜志主編,文壇經常奇怪這么一本瑰麗而迷幻的、具有文本實驗性寫作特點的刊物,怎么會產生于云南,它的偶然性或必然性是什么?
陳 鵬:云南偏居中國西南一隅,有點山高皇帝遠的意思,所以云南人行事難免天馬行空;再就是,云南是高原,缺氧,就更容易讓人胡思亂想了。其三,這地方生活著二十五個少數民族,所謂多民族大雜居小聚居,自然而然有碰撞有溝通有交融,文學肯定是不一樣的。其四,兼容并包的西南聯大精神對昆明影響甚巨,迄今不絕,所以云南、昆明一直就自帶某種先天的魔幻先鋒氣質,誕生一兩部先鋒雜志再正常不過。當年《大家》創刊就得益于之前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美文學書系的鋪墊。那套書系,影響太大了。
于曉威:您喜歡跟人打交道嗎?
陳 鵬:不喜歡。從小就在集體長大,對人群煩不勝煩。少年時期的記憶也多苦澀,嚴重影響了我成年后的性格,人際交往一直有缺陷。還是喜歡一個人待著,讀,寫。當然,身邊也有二三最好的哥們,能偶爾小聚,足夠了。人其實是不需要朋友的,人生而孤獨,是常態也是本質。為了應對孤獨,寫作是其一,擇一二友人,算是其二。
于曉威:您對顏色敏感嗎?您最喜歡什么顏色?它會給你帶來特別的記憶嗎?
陳 鵬:還算敏感吧。最喜歡的還是球場的綠色。從小水泥地上、黃土地上摸爬滾打,一旦上了真草球場,那叫一個幸福!堪比現在突然發一個長篇。哈哈。所以每周還是要踢球,要擁抱九百平方米的濃綠,呼吸昆明真草球場濃烈刺鼻的香氣,會讓我覺得活著,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于曉威:遇見作者寫得不令您滿意的小說時,您經常會跟他們說什么?
陳 鵬:是我在編輯《新小說手冊》的境況吧?會遇到,會讓他們改一改,朝某個方向,再試試看……如果是朋友的小說,偶爾讀到,不滿意,說不說,兩可。有的老友是能說的,我就直接告訴他哪哪很棒,哪哪還不太好。當然,這純屬業務交流了。
于曉威:您對寫作場所要求很高嗎?比如,不得不出差或旅行的時候,您能寫作嗎?
陳 鵬:不高。我通常在家寫作,書房,大多站著寫——效仿海明威。我隨時可以進入,這是當記者時訓練出來的,任何時候都能寫。出差、旅行也如此,房間里寫,毫無問題。
于曉威:您二十歲之前讀到的印象最深的文學作品是什么?還記得嗎?
陳 鵬:十七歲,讀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從此愛上老海。愛了一輩子。后來發現《老人與海》還不是他最好的小說,他最好的還是那些短篇,精妙無比。再就是《永別了武器》《太陽照常升起》。當時,我記得當時第一次讀海明威整個兒蒙了,太強大了,多簡單的故事啊,基本上沒什么故事,就一個老頭,一條大魚,居然寫得如此驚心動魄,沒一處敗筆,沒一句廢話,這不是最棒的小說是什么?我還記得我讀完之后久久佇立在陽臺上,那地方也是我睡覺的地盤,遙望昆明天空,鴿群起起落落,遙想那個叫圣地亞哥的老人獨自駕著小船在大海里飄蕩……
于曉威:據我所知,您還是國家二級足球運動員,可以同時講講您的相關履歷?
陳 鵬:我很小就踢球,差不多十歲進了準專業隊,也叫體校校外班,一撥伙伴從小一起生活,訓練,比賽。我們那一撥孩子是昆明最好的,1988年曾締造昆明校園足球歷史,一舉在幼苗杯西南賽區比賽中出線,躋身全國四強。后來1989年、1990年也都躋身全國四強。但是我們整隊都沒有選擇進專業隊(職業隊),我高二高三之后太厭倦足球了,又忙于高考,順利考上武漢體育學院體育管理專業,也在院隊踢過,但基本上,大學之后,算是正式向專業化足球道別了。大學期間拼命寫小說讀小說,大批經典就是那時候讀的,如饑似渴。武漢體院圖書館的名著挺多,我徜徉其間樂此不疲。周末就寫小說,在《青春》《萌芽》發了幾個。1995年去《大家》實習,對我影響太大,你突然進入文學現場了。從未離開足球,一輩子的摯愛啊,其哲學與老海的精神多么相似,你可以毀滅我,不可以打敗我。
于曉威:您的小說寫完或發表后,家人們每次都讀嗎?他們(她們)如何評價?
陳 鵬:一概不讀。他們熱衷電視劇。哈哈。
于曉威:您看電視嗎?所有的電視節目中,您最喜歡看什么節目?為什么?
陳 鵬:偶爾。主要看足球比賽。間或也看《十三邀》《圓桌派》和陳丹青《局部》之類,其余,我最愛的是關于美術的紀錄片。我熱愛名畫。對古典派、印象派、后印象派、現代派、后現代派情感頗深。每次去巴黎都要泡在盧浮宮、奧賽、蓬皮杜。尤其熱愛英國的弗朗西斯科·培根,這家伙畫出了人類邪惡又天真的潛意識,太棒了。戈雅后期也多棒啊!2019年我去蓬皮杜剛好撞上培根個展,極震撼。當然,梵高也是我的摯愛。哎,誰又不愛梵高呢?
于曉威:我記得斯拉沃熱·齊澤克在《無身體的器官:論德勒茲及其推論》里,論述過“愛欲”或“性”與“思維機器”之間存在的悖論。文學作品從不應該回避寫“性”,這是一個常識了,然而,我還是想饒舌一下,您覺得真正的文學作品中寫性,究竟是為了什么?
陳 鵬: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性要寫好太難了,所以不如點到即止。勞倫斯是正面寫還能寫那么好的典范,但中國語境大不同,凡性描寫,都不免有博眼球之嫌。優秀的文學經典中的性描寫,應該與最具體的人和人的處境水乳交融,比如《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它與勞倫斯以自然抵御工業的想法高度契合。否則,不如不寫。
于曉威:如果可能的話,您最想跟國外的哪一位作家成為同時代的好朋友?為什么?
陳 鵬:海明威。他知行合一,他充滿力量,他如此慷慨……
于曉威:您覺得什么情境或標準之下,您自己的寫作才是成功的?
陳 鵬:我想,首先還是要能寫出堪與經典較量的文本吧。我說的經典一定是19世紀以來的經典。大經典。要能寫出《罪與罰》《太陽照常升起》《堂吉訶德》《白鯨》這樣的東西,你還有什么可遺憾的?但是現在衡量標準不一,好的往往被說成不好的,不好的又被奉為新的經典……但文學是有標準的,有絕對標準。這種絕對標準基于經典之上,也就是說,你的反叛,你的原創性,是踩在巨人肩膀上的,你不能跳離那只肩膀,不能怪力亂神自說自話。繼承然后創新,這就是文學最難的地方啊。
于曉威:您的業余愛好還有什么?
陳 鵬:堅持踢球。再就是游泳,看畫冊,練習書法,聽搖滾樂。對,我熱愛搖滾樂。
于曉威:您會一直寫下去嗎?
陳 鵬:會,這是最大的人生樂趣與意義所在,干嗎放棄?
于曉威:好,最后一個問題,您最想跟寫小說的同道們說些什么?
陳 鵬:好好活著,認真寫。對,認真,請務必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