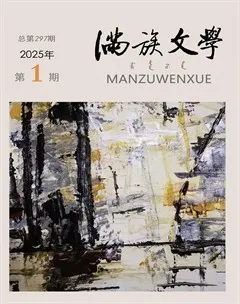風箱
樹枝的燃燒發出噼里啪啦的聲響,那些忽明忽暗的節奏讓生活慢下來。火的烘烤讓一顆心始終保暖。多么好,你生起的人間煙火也像一些勾連的引線穿過我心底的盲點,讓我看到了一些發亮的事物,它們不再模糊。幻滅的事物都在復出。這些年四處奔走,遠離了土地,遠離了故鄉,也遠離了一架陳舊的風箱。隔著幾十年的時空已沒有再走近過一架風箱,我早已忘記了它曾經的存在。承認遺忘使我再次向一架風箱靠近。我彎曲著身體也學著祖母的樣子,拉動著風箱,扇動著火苗,讓日子也像一團火,有了滋味,有了五谷雜糧的味道。鍋里汩汩冒出的水汽,讓我淚流滿面。
不知道從兩歲還是三歲起,我便在鍋臺旁燒火,不為別的,只為去拉動風箱。風箱在農村家家都有,只是大小各不相同。要根據自家的灶臺大小去找木匠定做。我不記得我家是哪位巧手的木匠做的,我拉的永遠是那一架原木風箱。它不會壞,也不會變老,只會越用越靈。風箱和灶臺有一個管道用來通風,風力越大,火苗就越高。隨著身體慢慢長大,我的力氣也越來越大了。小時候拉風箱需要兩只胳膊一起用力,母親不讓我拉,我卻非要拉。一是可以隨時討要到一些好吃的,比如燒火時需要隨時劈柴,父親發現里面有能吃的蟲子就會單獨放在一個小的鐵鍬上在火上烤給我吃。那樣的白色的蛤蟲是可以吃的。窮日子里聞到它就是聞到肉的香味,我總是美得不亦樂乎。在秋天,有時也會燒點紅薯和玉米還有花生什么的。總之可以燒的,母親也總會給我燒一點吃。當然我也吃過燒的麥穗,無論是燒什么我都是要求親自拉著風箱,聽著風箱呼噠呼噠地響,像一頭賣力的老黃牛在一個勁地喘息著。我不記得那時的天是如何黑下來的,日子是如何熬過來的,覺得也很快樂。有吃有喝的很是滿足,最主要的是一架風箱,隨時可以充當一個玩具。最為調皮的事是,即便不燒火做飯我也想拉它,煙灰從爐口直接冒出來,一定會被母親罵上一頓。還是再說說那燒熟的糧食吧,無論是紅薯還是玉米還是麥穗,它們都有獨到的味道,這些年我再也沒有吃過,也沒有再摸過一次風箱。味覺和記憶好像是捆綁在一起的。現在我的口角在流著口水,似乎會滴落在我敲打的鍵盤上。只是我確實是一個嘴饞的孩子。日子過好了,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可此刻,我好想把一架風箱安放在樓房中,雖然這想法是那么不合時宜。
拉風箱是一個力氣活,但我從來不覺得累,我一個人可以全包下這個活。后來家里有了妹妹,她要和我搶著拉,我的手和她的手一起拉。有時候我也會和她一起吃爐火里燒的好吃的。有時候母親還會燒一塊包裹在玉米葉子上的咸魚,魚在火堆里冒油并且還會滋滋地響,我和妹妹都在舔著舌頭,等著魚快點燒熟。只是吃魚一定要連玉米片片一起吃,那時我是很不情愿再吃玉米片片了,若不是因為有魚,我很不想咽下去的,還不如吃紅薯好吃。只是沒有別的更好的吃的了。幸好還有風箱,它的呼噠呼噠聲讓我覺得童年還是有一個玩伴的,它推動著生活不斷向前。我慢慢也能吃上饅頭和包子了。飯碗里也有了肉,有了更多的菜,菜的品種也在不斷地變化增多。
風箱家家都有,它好像一個住家過日子的象征或標識,每一家都需要這么一個物件,我一直喜歡聽它的聲響。記得上小學時,母親總是早起做飯,我在夢里也會聽到風箱的呼噠呼噠聲,它讓我覺得幸福和踏實,在睡夢里聽到風箱的聲音睡得更香了。那個時候時間過得好像很慢,我每天早晨都能聽到母親拉著風箱在燒火做飯。風箱在角落中似乎無人去關注它太多,但是它的手柄被母親的掌紋越摩越光滑,光滑得發亮,我的小手也不知道拉過它多少次。
風箱在灶臺最不起眼的地方,很少有人關注,它不像誰家有一個像樣的家具還能被人觀賞,風箱大都是一個模樣,仿佛沒有什么不同之處,只是木質不一樣,它拉動的風力也不一樣。父親說過梧桐木是不適合做風箱的,因為梧桐木太輕。刺槐還可以,只是要把木頭晾干了才能做,而且這種風箱會很沉。最好是楸木,不輕也不重,做出的風箱也不會風干有裂紋,用幾十年都不會壞的。只是楸木很少有,因為長得慢,也不容易成材。大多數人家用的都是刺槐木,它是比較粗糙一些,需要用砂紙把那些紋理打平了才可以,做好了也不用刷漆就可以直接用了。只是一定要找一個手藝好的人打做一架風箱,這樣用的年頭才會久。打造風箱也是一手絕活,只是很少有人學這門手藝,估計現在很少有人會了。因為風箱好多年不再用了。
確切地說有了電風機,它就慢慢退出了歷史舞臺。鄉村有一些老人不舍得用電,也不舍得買一臺電風機,就一直還用風箱。我家買了一臺電風機后,把風箱放在另一個灶臺上用,只是那個灶臺很少起火,它用的機會就少了很多。電風機也會有一個風的聲響,是發動機的嗚嗚聲,像飛輪在不停地飛旋著大風或小風,它可以調節風速大小,顯然是比風箱方便多了。我也很少有機會再拉動風箱,母親也不用那么賣力地做飯了,生活一下子方便多了。有了電,一切也都在改變之中。不知又過了多少年,我家的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再也不用風箱了,有了煤氣灶臺。風箱像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有了時代的滄桑,你看到它滿身的塵埃,時間的褶皺都在它的皮膚上表露出來。父親把它放在一個角落,還沒有想它有什么用,是把它劈成柴火,還是用來當個架子,或是把它當成廢品賣了呢?好像還沒有考慮好,它就一直放在那里,身上堆滿了東西,好像它僅有的一點用途,就是可以放一些雜物。因為它不是很礙眼,所以父親也一直沒有扔掉它。
風箱拉動著風將時間推移,回憶總會覺得模糊了許多,但又在某一個時刻清晰起來。那些串鄉的師傅去村里爆爆米花,通常都會帶一臺風箱。在大街上找一個沒風的地方,安排好火爐,一個鐵制的橢圓形的匣子上面還有秒表。我們幾個小孩一直圍著那個人打轉轉,怎么也不肯走開。看著他拉動風箱,他的風箱大,大風也嗚嗚地響。他的力氣大,一手拉著風箱,一手往火爐下填柴。誰家要爆爆米花,要自己帶著柴火,各式各樣的都有。有的是柴草,有的是玉米棒子,還有的是果樹枝條,最好的要數玉米棒子,那樣的火焰不高也不低,正好適合爆爆米花,這樣不會煳鍋,爆米花會又脆又大。爆爆米花還要加上幾顆糖精,這樣爆出的爆米花甜甜的。我們幾個小孩子就是要圍著那個人的,看著爆米花機的秒表在跑動,當它的轉速越來越快,就快要爆炸時,我們個個撒腿就跑開。那個人會把大炮似的匣子放進一個麻袋里,然后砰的一聲打開了,爆米花在袋子里飛。誰家的誰就去接過口袋,大人們總會分給我們小孩一人一把,我們把爆米花裝在口袋里,等著回頭慢慢品嘗。聽著風箱的呼呼聲,再聽著爆米花的開鍋爆炸聲,別提是多么歡快了。我喜歡吃糖精多一點的爆米花,滿嘴的甜味和香味兒。我們把沒有完全爆開的叫啞巴,連啞巴都是很好吃的,越嚼越香。去村里爆爆米花的師傅很多,誰能爆出好的爆米花,要先看他的行頭,是不是帶來一架又結實又大的風箱,是不是風箱拉起來呼呼地響,要是小的風箱,就不會有多少人理會他,他就會冷冷地站在那兒。年紀大的老人會告訴他,讓他打一架大風箱再來。
閑暇的時光是在農忙之后,在哪一個村子都會見到拉著風箱爆爆米花的師傅,很是熱鬧。拉風箱的師傅還有走街串巷打鐵的。打鐵的師傅通常是兩個人,有一個專門拉風箱填煤塊的,有一個人負責打鐵。拉風箱的和打鐵的都會穿一個大的皮圍裙,他們的裝扮和爆爆米花的不同,看起來威嚴多了。這次小孩一定不肯靠前的,打起鐵來,鐵花會亂竄的。不小心火花會濺到衣服上,甚至皮膚上的。
我看到打鐵的師傅在用力拉著風箱,大風也是呼呼地響,看起來是最大風力,煤火很旺,另一個人在叮叮當當地用一個大的鐵錘子砸鐵,要什么農具他就會打出什么樣的鐵農具來。鐵在煤火的烘烤下變軟,火星四射,看起來也很是壯觀。但他是不同于爆爆米花的,不是特別熱鬧。只是一群大人圍在邊上,來來回回打農具,我們小孩在遠處聽個動靜就好了,也不是特別感興趣。但是風箱的風力還是讓我們覺得很有力度,好像從來沒有聽到這么大的呼呼聲,像一個神奇的武士,使出全身的力量把大風吹出來。在那個時代,風箱是不可缺席的,當然我們的圍觀也不可缺席,它聚攏了一個鄉村的快樂。打鐵的風箱是巨大的,比家用的大了一倍的體積,像一個大的箱子,木頭的質地堅硬,也許是楸木的吧。等到他們要把打鐵的工具搬到拖拉機上時,一定是需要兩個師傅抬上去的,普通的風箱一個人就可以抱起來。它這個看起來很重,是我見過最大最沉的風箱了。
好多年過去了,我好想再拉一拉風箱燒火做飯,像一匹馬拉回舊時的日子。風箱的天空一定升起了煙火,那是許多人的鄉愁。
母親說,村里極少有人再用風箱了,老人拉得費力,年輕人又不肯用。現在的很多小孩不曾見過一架風箱,更別說拉風箱了。當然我也許久沒有再拉過它。我是多么想聽聽它的呼噠呼噠聲,那熟悉的聲音,便是親切的故鄉。
【責任編輯】涉 祺
紫藤晴兒,本名張楠。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東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魯迅文學院第四十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學員,作品發表于《詩刊》《星星詩刊》《揚子江詩刊》《草堂》《詩選刊》等。出版詩集《返回鏡中》《大風勁吹》。獲冰心兒童文學新作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