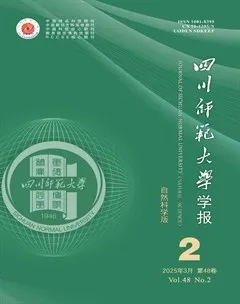基于夜間燈光數據的四川省縣域經濟差異時空格局演變及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四川省183個縣域單元2013—2021年夜間燈光數據,采用空間自相關、重心轉移、標準差橢圓分析等方法來探究四川省縣域經濟的時空格局演變,并利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造成四川省縣域經濟差異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研究表明:從整體上看,四川省縣域經濟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格局,四川盆地地區經濟發展態勢良好,川西高原地區經濟發展則不明顯;標準差橢圓總體上呈現“東北-西南”分布格局,同時四川省經濟重心變動幅度較小,且變動速度呈現遞減趨勢;從空間關聯性來看,四川省縣域經濟發展存在顯著的正相關,空間關聯程度呈現出波動上升趨勢,具有較強的空間異質性和區域集聚性;根據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測定影響因素,正向因素中城鎮化水平是最主要的正向影響因素,而產業結構則是次要的正向影響因素,投資水平、教育水平以及市場規模是四川省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正向影響因素,政府作用力則為限制性因素.
夜間燈光數據; 四川省縣域; 經濟差異; 時空格局
F127; K902 A 0231-11 02.008
縣域經濟是中國國民經濟的基本單元,是中國式現代化的蓄水池,其能否實現平衡高效發展直接影響到中國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成效.當前,中國發展縣域經濟面臨著一系列困難和挑戰,其中縣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最為突出[1],已是中國目前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其中四川省的縣域經濟差異最為典型[2].原因在于,四川省的產業結構合理程度不同以及政策傾斜程度不一等影響因素,造就了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經濟發達地區和以三州地區為主的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顯著經濟差異,四川省縣域經濟現狀與中國縣域經濟現狀高度契合,通過對四川省縣域經濟差異的研究能夠為解決中國縣域經濟存在差異的問題提供新思路.因此,對四川省縣域經濟差異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當前,學界對縣域經濟發展研究較為豐富,主要分為2個方面.一方面,一些學者通過描述縣域經濟時空分布變化來探究縣域經濟發展差異.例如:王東清[3]刻畫了成渝雙城經濟圈縣域經濟空間格局演化過程,得出了成渝極化現象明顯,不發達地區集中分布的結論;莊成祥等[4]通過分析黑龍江省時空演變特征并探討其成因,得出了黑龍江省呈“南高北低,東高西低”的空間格局,不發達型縣域在中心集聚的結論;武文超[5]分析黃河流域縣域經濟發展不均衡性的時空演化情況,結果顯示黃河流域縣域經濟發展不均衡性的絕對程度擴大,相對程度縮小;馬存霞等[6]利用GIS空間分析等方法探究了寧夏縣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演變趨勢及其空間分布特征,發現寧夏南北縣域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顯著.另一方面,一些學者認為僅從時空差異出發,并不能對造成差異的成因做出解釋,故進一步,在對縣域經濟時空分布變化分析的基礎上,運用計量回歸模型來探究導致縣域經濟差異形成的原因.例如:常迎輝等[7]運用地理探測器方法分析了河南省縣域經濟差異的主導影響因子,結果顯示第二產業增加值、經濟基礎等是主導因素;吳瑋怡等[8]通過地理探測器定量分析影響廣東省縣域經濟差異的主導因子和交互作用,得出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產業產值等是影響廣東省縣域經濟差異的主要因素;張佰發等[9]利用回歸模型,得出了自然稟賦、產業結構等為主要影響因素的結論;史利江等[10]運用數理統計分析,對汾河流域縣域經濟差異的驅動因素進行探究,結論顯示自然條件、資源稟賦與產業結構是主要因素.綜上所述,前人研究為我們探究縣域經濟差異的時空格局及其影響因素提供了一定的參考,然而以上研究均采用統計年鑒中獲得的人均GDP數據來衡量縣域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數據受人為干預影響的可能性較大,且存在統計數據時標準不一、統計數據遺漏或缺失、統計結果滯后性強、獲取成本高等諸多問題,且GDP指標的核算都是建立在各種人為統計資料、報表之上,并且以行政單元為基礎,缺乏準確、合理有效的空間位置信息[11]等,不利于對縣域經濟差異的客觀掌握.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完善和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選擇利用夜間燈光數據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代理變量,與傳統的GDP統計數據相比,夜間燈光數據最大限度地消除了GDP統計中的人為因素,相對來說更為客觀且不受價格因素干擾,且夜間燈光數據還具有明確的地理空間屬性[12].鑒于此,夜間燈光數據開始被用作GDP的替代變量用于研究經濟差異的相關研究中.例如:斯麗娟等[13]基于十大城市群的夜間燈光數據,得出了外商投資、人力資本、科技創新對城市群經濟收斂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而工業化水平具有顯著負向影響的結論;崔百勝等[14]基于長三角地區夜間燈光數據,探究長三角地區空間溢出效應,研究發現長三角地區各省市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為正的空間溢出效應;晁靜等[15]基于長江經濟帶三大城市群比較分析不同時段長江經濟帶三大城市群經濟差異時空演變及影響因素,結果表明總體差異、群內差異及群間差異均逐年縮小,政府投資、市場水平及對外開放是推動三大城市群之間及各城市群內部經濟差異的核心因素.前人基于夜間燈光數據,在研究區域經濟差異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目前還極少有學者基于夜間燈光數據,以縣域單元為研究樣本探究其經濟差異,涉及四川省的研究則更為缺乏.因此,本文將基于夜間燈光數據探究四川省縣域經濟差異.
截止2021年,四川省常住人口為8 372萬人,全省GDP總量達53 850.79億元,同比增長8.2%,人均GDP為64 326元.基于地級市視角,從GDP總量來看,位于發展水平首位的是成都市,GDP總量達19 916.98億元,同比增長8.6%,人均GDP達到94 622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市(州).基于縣域單元視角,截止2021年,武侯區人均GDP居于全省首位,達18.28萬元,最低的為美姑縣,人均GDP為1.70萬元,極差為16.58萬元,前者是后者的10.75倍.四川省是中國西部地區第一大省,是中國西南地區的經濟、科技、人才、政治、文化、教育中心.四川省存在成都平原等經濟發達地區;同時也存在“三州”地區等經濟欠發達地區,川東平原地區經濟普遍好于川西高原地區[16].由此可見,四川省內部各縣域之間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存在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兩極分化格局明顯的特征.因此,研究四川省縣域經濟差異能夠以小見大的為中國縣域經濟實現平衡、健康發展提供有效建議.基于此,本文將以四川省為研究區域,基于2013—2021年NPP/VIIRS夜間燈光數據,用其表征經濟發展,運用標準差橢圓、空間相關性分析等方法,分析四川省縣域層面經濟差異的動態演化特征,并借助多元線性回歸法分析經濟差異的影響機制,以期為四川省乃至全國實現共同富裕、區域協調發展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政策制定提供科學化的依據和參考.
1 研究區域范圍與數據來源
1.1 四川省區域概況
四川省,位于中國西南部,地處長江上游,面積居全國第5位.全省面積48.6萬km2,轄21個市(州)、183個縣(市、區),與重慶、貴州、云南、西藏、青海、甘肅和陜西等7省(自治區、直轄市)接壤,有全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第二大藏族聚居區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區.因此,本文選取了四川省所囊括的183個縣域單元作為研究尺度,對NPP-VIIRS夜間燈光數據做預處理,構建時間序列的四川省縣域經濟夜間燈光數據集,來對四川省范圍進行縣域經濟發展時空演變特征分析.
1.2 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包括夜間燈光數據、行政邊界矢量數據和社會經濟統計數據,3類數據的詳細來源如下.
1) 夜間燈光數據.夜間燈光數據以其具有的高度客觀性、時序穩定性與尺度全面性三大優點,被學界當作GDP替代指標,廣泛地用在衡量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研究中[17-18].當前,學界所使用的夜間燈光數據主要有2種,分別為DMSP/OLS數據和NPP/VIIRS數據.本文將使用NPP/VIIRS數據用于衡量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原因如下:首先,在數據時效性上,NPP/VIIRS數據相比于DMSP/OLS數據更好[18],雖然后者時間序列較長,但卻只提供1992—2013年的數據,而前者卻能提供2012—2021年的數據.其次,在數據分辨率上,NPP/VIIRS數據相比于DMSP/OLS數據更高,后者的空間分辨率僅為1 km,而前者的空間分辨率則提升至500 m,能夠更為準確地刻畫小尺度地表照明分布[19],使NPP/VIIRS數據的輻射范圍更廣.最后,在數據靈敏度上,NPP/VIIRS數據相比于DMSP/OLS數據更高,能有效克服DMSP/OLS數據存在的夜間燈光值過飽和問題,進而使NPP/VIIRS數據的燈光總量和燈光面積與經濟數據的相關性要強于DMSP/OLS數據[20],能更客觀準確地反映經濟發展情況.
綜上所述,本文使用NPP/VIIRS數據,數據處理如下:首先,使用Google Earth Engine平臺下載得到四川省2013—2021年夜間燈光數據,數據版本為Annual VNL V2.1.其次,借助ArcGIS軟件賦予其Albers投影坐標系,并采取臨近法重采樣得到500 m分辨率.再次,基于四川省183個縣域矢量圖,借助ArcGIS軟件中的“以表格顯示分區統計”工具得到相應縣域的夜間燈光值總量.最后,參考陳洪章等[21]的研究,將各縣域夜間燈光值總量與相應縣域面積的比值,用作衡量四川省各縣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
2) 行政邊界矢量數據.本文所使用的四川省縣域行政邊界矢量數據下載于全國地理信息資源目錄服務系統所發布的1∶100萬全國基礎地理數據庫(https://www.webmap.cn/commres.do?method=result100W).
3) 社會經濟統計數據.本文所使用的四川省縣域社會經濟統計數據整理于四川省統計局公布的《四川省統計年鑒(2014—2022)》,數據下載地址為:http://tjj.sc.gov.cn/scstjj/c105855/nj.shtml.對于缺失數據,通過查詢各地級市統計年鑒和中國縣域統計年鑒獲取,依然缺失的數據通過插值法加以補充.
2 研究方法
2.1 空間自相關分析
空間自相關是反映空間變量在同一個分布區內的觀測數據之間潛在的相互依賴性的空間分析方法,分為全局空間自相關(IGM)和局部空間自相關(ILM).
2.1.1 全局空間自相關
以四川省縣域單元作為空間單元,采用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四川省縣域夜間燈光數據的空間相關性,公式[22]為:
IGM=n∑ni=1∑nj=1Wij(Xi-)(Xj-)∑ni=1∑nj=1Wij∑ni=1(Xi-)2,
(1)
式中,Xi、Xj分別為i縣(市、區)和j縣(市、區)的夜間燈光數值;n為縣級行政單元數量;為平均值;Wij為空間權重.全局空間自相關系數取值范圍為[-1,1].當IGMgt;0時,表示空間正相關,代表四川省縣域經濟發展格局在空間上呈現集聚;當IGMlt;0時,表示空間負相關,代表四川省縣域經濟發展格局在空間上呈現離散;倘若IGM=0,則表現為四川省縣域經濟發展格局在空間內隨機分布.
2.1.2 局部自相關分析
用局部空間自相關來衡量研究區域的夜間燈光觀測值與周邊區域的聚集程度,公式[22]為:
ILM=(Xi-)S2i∑nj=1,j≠iWij(Xj-),
(2)
式中,S2i代表各縣夜間燈光數值的方差.ILM能夠反映空間變量分布中空間異質性與不穩定性等局部空間特性.ILM可分為4類模式:高高集聚型(HH)、低低集聚型(LL)、高低離散型(HL)和低高離散型(LH).
2.2 標準差橢圓模型分析
標準差橢圓模型(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SDE)是一種反映評價要素空間分布的整體特征及演變過程的空間統計方法,主要通過中心、長軸、短軸、方位角等參數直觀地表達要素空間分布的相對位置、離散程度以及發展趨勢[23].橢圓的長半軸表示的是數據分布的方向,短半軸表示的是數據分布的范圍,長短半軸的值差距越大(扁率越大),表示數據的方向性越明顯;短半軸表示數據分布范圍,越短表示數據向心力越明顯;中心點表示數據中心位置,該模型主要參數計算公式[24]如下.
標準差橢圓的中心:
DSE,x=∑ni=1(xi-)2/n,
DSE,y=∑ni=1(yi-)2/n,
(3)
式中,DSE,x和DSE,y代表標準差橢圓的中心點坐標;(xi,yi)表示研究對象的區位坐標;(,)表示研究對象的平均中心;n為研究對象的總個數.
標準差橢圓軸的方向:
tan θ=A+BC, A=∑ni=12i-∑ni=12i,
(4)
B=(∑ni=12i-∑ni=12i)2+4(∑ii)2,C=2(∑ii)2,
(5)
式中,θ為標準差橢圓的方位角,即正北方向順時針旋轉到橢圓長軸的角度;i和i分別表示各研究對象坐標到平均中心的坐標偏差.
標準差橢圓軸長的標準差距離:
σx=2∑ni=1(icos θ-isin θ)2n,
σy=2∑ni=1(isin θ-icos θ)2n,
(6)
式中,σx和σy分別表示為x軸和y軸的長度.
2.3 經濟重心分析
經濟重心是指在區域經濟空間里的某一個點,在該點各方向上的經濟力量能夠維持均衡.通過研究經濟重心的轉移可以有助于研究觀察某一經濟變量在區域內部的時序空間變化[20],了解經濟變量在一個經濟區域中的發展方向.本文引入夜間燈光數據來測算經濟重心坐標.經濟重心主要計算公式[21]如下:
X=∑ni=1Ni×xi∑ni=1Ni, Y=∑ni=1Ni×yi∑ni=1Ni,
(7)
式中,X、Y表示燈光重心坐標;Ni表示第i個影像單元夜間燈光數據值;(xi,yi)表示第i個次行政區域中心的坐標;n為影像單元個數.
經濟重心的轉移可以反映區域發展軌跡,利用不同年份經濟重心轉移的距離和角度來描述經濟重心轉移規律.經濟重心轉移及角度計算公式為:
Dt=(xt1-xt2)2+(yt1-yt2)2,
θt=t=arctanyt2-yt1xt2-xt1,
(8)
式中,xti、yti表示t年的區域重心坐標.
2.4 影響因素分析方法
經濟發展的水平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本文在參考前人研究[25-31]的基礎上,根據四川省實際情況,選取了產業結構、投資水平、城鎮化水平、教育水平、市場規模、政府作用力6方面作為探究影響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表1).因四川省自然地理條件復雜且自然環境統計數據的獲取難度較大,本文將不選取自然環境變量.本文將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檢驗上述因素對四川省縣域經濟差異的具體影響.
基于以上變量,構建以經濟發展水平為被解釋變量,產業結構、投資水平、城鎮化水平、教育水平、市場規模、政府作用力為解釋變量的面板數據最小二乘回歸估計模型,為了增強數據可視化程度,減少個別極端值影響,消除異方差.現對模型中各個指標分別進行對數處理,模型構建[21]如下:
ln nilit=α+β1ln insit+β2ln invit+
β3ln urbanit+β4ln eduit+β5ln marketit+
β6ln govit+εit,
(9)
式中,ln nilit為被解釋變量;i代表縣(市、區);t代表年份,ln nilit則就是i區域第t年的夜間燈光數據的自然對數;α為常數項;β1~β6為解釋變量線性部分回歸系數;εit為計算中存在的隨機誤差項.
3 結果分析
3.1 整體結果分析
將2013—2021年四川省夜間燈光數據關聯到四川省縣域空間矢量圖上,制定相同標準分析空間分布格局差異,將四川省各年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按照相同標準劃分為高水平(gt;35.01),較高水平(25.01~35.00),中等水平(15.01~25.00),較低水平(5.01~15.00),低水平(lt;5.00)5個等級(圖1).由圖1知,經濟發展的高水平區域集中在成都市下轄的縣級行政區以及攀枝花市下轄行政區;經濟發展的較高水平區域則主要環繞成都呈現環形分布;經濟發展中等水平以及較低水平區域則廣泛分布在四川盆地的縣級單位;經濟發展低水平區域集中在川西高原以三州地區為主.從各個等級所對應的縣級單位數量上來看,低水平的縣(市、區)的數量要遠遠大于其余等級的數量,等級越高所對應的數量就越少.從時間趨勢上來看,與2013年相比,2021年經濟發展高水平以及較高水平的縣(市、區)的數量有明顯增加,表明經濟持續向上向好發展,但經濟發展不平衡依然顯著.從劃分區域來看,四川省內各縣(市、區)差異增強,四川盆地各縣(市、區)經濟增長速率較快,成效顯著,西部川西高原地區經濟增長效果不明顯.
3.2 空間方向性結構分析
為進一步明確四川省縣域經濟在地理空間上的變動方向和集中程度,本文利用ArcGIS軟件空間統計模塊中的Directional Distribution(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工具和Mean Center工具,對2013—2021年四川省縣域經濟的重心和標準差橢圓進行了測算.結果如表2和圖2所示.夜間燈光數據與人類活動、人口數量、社會經濟之間存在正相關,可以客觀反映經濟發展,用于社會經濟研究.四川省縣域經濟的標準差橢圓覆蓋范圍主要是樂山市、眉山市、成都市、德陽市、綿陽市.全省經濟標準差橢圓總體變化較小,以成都市為中心向外擴張.四川省經濟發展的熱點區域主要集中于該區域,是四川省經濟最發達的區域.
從轉角θ來看,四川省縣域經濟總體上呈現較為穩定的“東北-西南”分布格局,但也有一定擺動.2013—2016年,橢圓θ角由33.70°擴大到34.26°,表明總體上呈現“東北-西南”分布格局,并且該格局有向逆時針方向的變動趨勢,“東北-西南”分布格局進一步強化.2016—2019年,橢圓θ角由34.26°擴大到39.30°,表明“東北-西南”分布格局進一步強化,逆時針方向上變動趨勢進一步加強.2019—2021年,橢圓θ角由39.30°縮小到39.10°,表明分布格局順時針回擺,“東北-西南”分布格局弱化.
從橢圓長短軸長度看,橢圓長半軸長度呈現波動縮小的趨勢,2013—2021年長軸長度由185.05 km減少至179.52 km,表明在研究區間和時段經濟發展集中度略有增強;橢圓短半軸長度呈現波動擴大的趨勢,2013—2021年短軸長度由102.14 km增加至122.15 km,表明經濟發展的離心力增強,離散程度加大.基于夜間燈光數據的標準差橢圓短軸伸縮變化度遠遠強于長軸,表明推動四川省縣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來自于南北方向上的縣域經濟增長.
根據重心變化分析,經濟重心主要在成都市雙流區境內移動且變動幅度較小.根據重心運動的軌跡以及距離分析,經濟重心大致沿東南-東北-東南的方向變動,2013—2021年重心共移動29.55 km,其中2013—2014年向東方向移動了3.25 km,2014—2016年,向北方向移動了11.96 km,2016—2017年向南方向移動了3.55 km,2017—2018年向東方向移動了3.49 km,2018—2019年向北方向移動了1.43 km,2019—2020年向南方向移動了4.48 km,2020—2021年向西方向移動了1.39 km,總體上重心南北移動幅度大于東西移動幅度,且速度呈現遞減趨勢.
3.3 空間關聯性結果分析
3.3.1 全局自相關分析
利用ArcGIS軟件空間統計模塊中的Moran’s I工具,以各年夜間燈光數據為基準,從縣域尺度計算四川省夜間燈光數據的全局Moran’s I指數(表3),表示區域間差異.表3結果展示,2013—2021年夜間燈光的全局Moran’s I指數均為正,Z值均在17.00以上,并且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四川省縣域經濟發展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全局Moran’s I指數總體呈現上升趨勢,表明四川省縣域夜間燈光數值的空間關聯程度呈現增強趨勢.從全局Moran’s I指數來看,其數值均在0.7以上,數值較大,表明四川省總體空間集聚程度較高.此外,夜間燈光數值高值區集中在省會城市成都下轄的縣級行政區周邊,其他縣域燈光數值較低,尤其是三州地區,表現出經濟發展水平欠發達地區空間集聚的特征.
3.3.2 局部自相關分析
為了進一步闡釋四川省縣域經濟局部空間差異性,利用ArcGIS軟件空間統計模塊中的Anselin Local Moran’s I工具,基于夜間燈光數據計算了2013、2016、2019以及2021年四川省縣域夜間燈光數據的局部Moran’s I指數,將局部空間格局分為了高高集聚區(HH)、高低離散區(HL)、低低集聚區(LL)、低高離散區(LH)4類(圖3),
顯著性空間特征以正相關為主.從空間趨勢分布來看,高高集聚區主要分布在成都市所下轄的縣級行政區以及周邊地區,低低集聚區則主要分布在三州地區以及廣元市和巴中市,低高離散區主要分布在高高集聚區周邊并呈環繞狀,高低離散區在四川省沒有分布.從時間趨勢上來看,顯著性集聚空間單元從2013年的79個降低到2021年的75個.其中,高高集聚區由2013年的13個增加到了2021年的16個,低低集聚區由2013年的55個減少到了2021年的51個,2種集聚類型占比超過89%.結果表示,四川省縣域經濟發展的顯著性空間特征以正相關為主,總體來看,有較強的空間異質性和區域集聚性.
3.4 影響因素結果分析
3.4.1 描述性統計
考慮到各個縣域在不同年份可能會出現撤縣設區,更名,合并等多種情況,本文將分析影響因素研究的時間跨度定為2013—2021年,研究區域定為四川省183個縣(市、區),共計1 647條數據.為了增強數據可視化程度,且為了縮小數據之間的絕對差異,避免個別極端值的影響,對原始數據取了對數.表4展示了主要指標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3.4.2 回歸結果及分析
本文運用Stata軟件根據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來探究四川省縣域2013—2021年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城鎮化水平對四川省經濟發展具有正向作用.具體而言,城鎮化水平每增加1%,經濟發展水平增加1.163%,且在1%水平上顯著.城鎮化是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城鎮化過程也是生產要素在城鎮的集聚,要素的集聚帶來規模效應,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32].根據四川省統計年鑒中城鎮化水平數據表明,城鎮化水平較高地區集中在成都平原地區,如錦江區、金牛區、武侯區等區縣,城鎮化率達到了100%,而三州地區城鎮化水平則明顯較低,如甘洛縣、美姑縣、雷波縣等城鎮化率均在30%以下.由此可見,城鎮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具有互動性.
產業結構對四川省經濟發展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具體而言,產業結構每增加1%,經濟發展水平則會提升0.779%,且在1%水平上顯著.經濟增長離不開新興的產業體系支撐.已有的研究表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對于經濟增長有顯著影響.隨著技術的進步和比較優勢的變化,生產要素從低端基礎部門向高端技術部門移動,生產力向更高水平邁進,從而帶來的產業結構調整優化促進經濟持續高質量健康發展[21].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對于四川省縣域經濟可持續化健康高效發展有重要作用.以四川省宜賓市為例,宜賓市全力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快培育新興產業并完成產教融合趨勢,培養吸引人才.宜賓市進行了積極的產業結構調整,這切實有效地推動了當地經濟發展.
教育水平、市場規模以及投資水平都是四川省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正向促進因素.
教育水平每增加1%,經濟發展水平則會提升0.233%,且在1%水平上顯著.教育是影響人力資本結構的主要影響因素,也是人力資本構成的核心.人力資本質量是影響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教育是提升人力資本質量的重要手段[33].例如,成都市和綿陽市是四川省教育資源較為集中的地區,基礎教育十分發達,同時也是四川省經濟較發達地區發展前兩位的地區.由此可見,教育水平的提升對經濟增長具有良好的推動作用.
市場規模每增加1%,經濟發展水平則會提升0.19%,且在1%水平上顯著.市場規模的擴大可以推動消費水平提高,消費結構優化升級.以成都市為例,成都市人均消費位居全省第一位,成都市消費市場的日益活躍,為成都市的發展提供動力.根據供求關系定律,消費水平提高,消費結構優化升級可以促進生產者生產的產品符合人民消費需求,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投資水平每增加1%,經濟發展水平則會提升0.12%,且在1%水平上顯著.投資水平越高對經濟增長越有利,這表明投資水平是對經濟增長的巨大推動力.投資水平的提高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促進經濟的良性發展,對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產生顯著作用[21].例如,成都市優越的政策條件、區位優勢以及營商環境吸引了大量投資,使其成長為西部重要的經濟中心城市.
政府作用力回歸系數顯著為負,是四川省經濟發展的限制性因素.政府作用力每增加1%,經濟發展水平則會下降0.116%,且在1%水平上顯著.可能的原因是行政的過度干預擾亂正常市場經濟秩序,阻礙了經濟的正常有序發展.過度的政府干預可能促進經濟增長,也可能因過多的行政干預舉措如行政審批過程中的繁瑣程序而降低效率,阻礙經濟增長,誘發類似權錢交易等一些尋租活動[31].
4 結論與對策
4.1 結論
為避免人為因素的干擾,本文區別于以往以人均GDP指標來衡量縣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研究,而是基于夜間燈光數據來測度縣域經濟發展水平,運用空間自相關、重心轉移、標準差橢圓分析方法,對四川省縣域經濟空間格局進行可視化分析.此外,還結合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討論了產業結構、投資水平、城鎮化水平、教育水平、市場規模、政府作用力這6種影響因素與四川省縣域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聯.本文得到的主要結論如下.
1) 對四川省縣域經濟差異的空間格局分析可得,四川省經濟發展的重心位于成都平原地區,經濟重心發展方向沿東南-東北-東南的方向變動.標準差橢圓長半軸長度波動縮小,短半軸長度波動擴大,呈現“東北-西南”分布格局,這表明在研究時段四川省縣域經濟發展集中度略有增強,經濟離心力增強,離散程度加大.
2) 對四川省縣域經濟差異的空間關聯性分析可得,全局莫蘭指數顯著反映了四川省縣域經濟呈現出正的空間自相關,且數值較大,表明集聚程度較高.局部空間自相關檢驗結果則表示四川省縣域經濟發展具有較強的空間異質性和區域差異性.高高集聚區集中在成都平原地區,而三州地區則長期處在低低集聚區呈現出連片特困的表現特征.
3) 對四川省縣域經濟差異的影響因素分析可得,城鎮化水平、產業結構、教育水平、市場規模、投資水平以及政府作用力都在不同影響程度下影響四川省縣域經濟發展.其中城鎮化水平、產業結構、教育水平、市場規模、投資水平與經濟發展呈正相關是促進因素,政府作用力呈負相關為限制性因素.
4.2 政策建議
縣域連城帶鄉,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支撐.擁有183個縣(市、區)、數量居全國首位的四川,將發展縣域經濟作為暢通城鄉經濟循環的重要切入點.為了更好發展四川省縣域經濟,使四川省縣域經濟發展更平衡、更充分,綜上,提出以下建議.
1) 根據對四川省縣域經濟空間自相關的分析,發現四川省各縣域之間存在較強的空間關聯性.基于此,首先應當繼續推動強化經濟發展優勢地區發展,以優勢地區輻射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發揮發達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真正實現“先富帶動后富”[34].以成都市為例,大力發展成都市經濟,在虹吸效應的作用下,周邊地區資源要素會向成都市集聚,形成四川省經濟發展的中心城市,而后以成都市為中心向外發散和溢出帶動周邊地區經濟增長[35-36].其次應當建立四川省縣域協同機制,深化區域合作,打破行政區劃壁壘與市場分割.在制度層面上推動各縣市的信息流通與資源整合,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利益分配機制,從而推動縣域經濟全面協調發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局面[21].
2) 通過對四川省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的分析,得出了資金、技術以及教育等因素對縣域經濟發展起正向的推動作用.因此,應當深化對三州地區等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政策扶持,推動資金、技術、教育等資源向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動,推動經濟平衡健康發展.為此,可具體從以下3個方面入手:首先,針對資金因素,應加大招商引資力度,推動更多大型項目、新興產業等落戶欠發達地區,為重大項目開展綠色通道[18].通過資金流入可以緩解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的資金需求,開闊市場,促進消費結構升級,拉動經濟增長,并創造就業崗位避免勞動力流失,為欠發達地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同時,資金流入還能夠有效促進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推動要素集聚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37].其次,針對技術因素,考慮到三州地區等地區礦產、水利資源豐富,技術資源流入能夠幫助有效的將自身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并通過促進產業技術結構的優化升級來促進經濟增長.最后,基于教育因素,三州地區等經濟欠發達地區教育水平較為落后,優化中小學設點布局,同時建設一批中等、高等職業學校培養適應縣域發展需要的高水平技能型人才.促進教育資源的流入能夠有效提升該地區人口素質,培養高水平的勞動者,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致謝 四川輕化工大學2023年校級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項目(CX2023108)和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川南發展研究院一般項目(CYQCNY20234)對本文給予了資助,河北大學經濟學院侯孟陽對本文修改提供了幫助,謹致謝意.
參考文獻
[1] 文雁兵,郭瑞,史晉川. 用賢則理:治理能力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百強縣和貧困縣的經驗證據[J]. 經濟研究,2020,55(3):18-34.
[2] 鄧小菲. 四川省縣域經濟差異時空演化特征分析[J]. 西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9,41(10):72-78.
[3] 王東清. 廣西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時空演變分析[D].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2023.
[4] 莊成祥,姜麗麗,焦子毓,等. 黑龍江省縣域經濟差異時空演變分析[J]. 合作經濟與科技,2022(15):19-22.
[5] 武文超. 黃河流域縣域經濟發展不均衡性的時空演化分析[J]. 統計與決策,2021,37(21):132-135.
[6] 馬存霞,魏麗,張小紅. 寧夏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時空差異研究[J]. 農業科學研究,2021,42(3):27-33.
[7] 常迎輝,朱慶偉,蘇德國,等. 2005—2019年河南省縣域經濟空間差異及影響因素探測[J]. 測繪通報,2022(2):149-153.
[8] 吳瑋怡,鐘凱文,許劍輝. 廣東省縣域經濟差異時空演化及影響因素研究[J]. 測繪科學,2021,46(6):156-163.
[9] 張佰發,苗長虹,冉釗,等. 核心—邊緣視角下的黃河流域縣域經濟差異研究[J]. 地理學報,2023,78(6):1355-1375.
[10] 史利江,劉敏,李艷萍,等. 汾河流域縣域經濟差異的時空格局演變及驅動因素[J]. 地理研究,2020,39(10):2361-2378.
[11] 陳穎彪,鄭子豪,吳志峰,等. 夜間燈光遙感數據應用綜述和展望[J]. 地理科學進展,2019,38(2):205-223.
[12] 王賢彬,黃亮雄. 夜間燈光數據及其在經濟學研究中的應用[J]. 經濟學動態,2018(10):75-87.
[13] 斯麗娟,王超群. 中國城市群區域經濟差異、動態演變與收斂性:基于十大城市群夜間燈光數據的研究[J]. 上海經濟研究,2021,33(10):38-52.
[14] 崔百勝,李家琪. 長三角地區經濟差異動態變化以及空間溢出效應:基于夜間燈光數據[J]. 經濟地理,2022,42(10):10-18.
[15] 晁靜,趙新正,李同昇,等. 長江經濟帶三大城市群經濟差異演變及影響因素:基于多源燈光數據的比較研究[J]. 經濟地理,2019,39(5):92-100.
[16] 曾永明,張果. 基于GIS和BP神經網絡的區域農村貧困空間模擬分析:一種區域貧困程度測度新方法[J]. 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11,27(2):70-75.
[17] 曾冰,邱志萍. 省際交界區經濟網絡空間結構研究:以湘鄂贛的燈光數據為實證[J]. 財經科學,2018(11):110-121.
[18] 曾冰. 基于NPP-VIIRS夜間燈光數據的湘鄂贛省際交界區縣域經濟空間格局及影響因素[J]. 地理科學,2020,40(6):900-907.
[19] 羅慶,李小建. 基于VIIRS夜間燈光的中國城市中心的分異特征及其影響因素[J]. 地理研究,2019,38(1):155-166.
[20] 曾冰,謝琦. 基于夜間燈光數據的黃河流域經濟發展空間特征與影響機制分析[J]. 中國沙漠,2022,42(3):41-50.
[21] 陳洪章,曾冰,郭虹. 黃河流域縣域經濟時空分異及影響因素:來自夜間燈光數據的檢驗[J]. 經濟地理,2022,42(11):37-44.
[22] 王明杰,顏梓晗,余斌,等. 電子商務專業村空間格局演化及影響因素研究:基于2015—2020年中國淘寶村數據[J]. 地理科學進展,2022,41(5):838-853.
[23] 唐健雄,何慶,劉雨婧. 長三角城市群城鎮化質量與規模的時空錯位及影響因素分析[J].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2,56(4):703-716.
[24] 毛豐付,高雨晨,周燦. 長江經濟帶數字產業空間格局演化及驅動因素[J]. 地理研究,2022,41(6):1593-1609.
[25] 吳建祖,王碧瑩. 政績考核與環境治理效率:基于政績考核新規的準實驗研究[J]. 公共管理評論,2023,5(2):117-137.
[26] 張暉,李靖,權天舒. 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嗎?基于“寬帶中國”戰略的準自然實驗[J]. 經濟問題探索,2023(10):1-15.
[27] 杜明軍. 區域能源轉型的綠色金融策略研究[J]. 區域經濟評論,2023(5):108-119.
[28] 沈湘平. 朝向涵養全部生命的城市化[J]. 新視野,2022(5):38-44.
[29] 方蔚瓊,魏國江. 我國教育資源集聚收斂及其對區域經濟的影響[J]. 經濟研究參考,2022(8):120-133.
[30] 孫昌盛,胡欣琪,張春英,等. 廣西壯族自治區縣域經濟發展差異及影響因素分析[J]. 浙江大學學報(理學版),2023,50(5):619-627.
[31] 黃慶杰. 試論政府能力與有效性[J]. 寧夏社會科學,2003(1):4-9.
[32] 王新越,秦素貞,吳寧寧. 新型城鎮化的內涵、測度及其區域差異研究[J]. 地域研究與開發,2014,33(4):69-75.
[33] 王士紅. 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新進展[J]. 經濟學動態,2017(8):124-134.
[34] 李子聯. 中國式減貧的邏輯[J]. 當代經濟研究,2020(6):32-38.
[35] 祝樹金,彭彬,段凡,等. 要素流動視角下縣域高鐵開通對中國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研究[J]. 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37(6):62-73.
[36] 王鴿. 長三角城市群產業功能協同效應研究[D]. 杭州:浙江財經大學,2020.
[37] 胡洋,陳聞君. 新疆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研究[J]. 經濟論壇,2014(4):52-55.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for County Economic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ichuan Province Based on Night Light Data
HAI Yifeng1, CHEN Hang1, ZHANG He1, ZHOU Jiani1,
GAO Linshuang1, YANG Fan1, CHEN Xiyong1,2, DENG Yuanjie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mp;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Sichuan;
2. Agricultural Economy Research Centre,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mp;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Sichuan)
Based on the 2013—2021 nighttime lighting data of 183 county units in Sichuan Province, this paper uses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center of gravity shift,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for the county economy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us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to do 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at caus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unty economy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study shows that: as a whole, the county economy of Sichuan Province shows a polarized patter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ichuan Basin area is good, whil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Sichuan Plateau area is not obviou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shows a “northeast-southwest”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general,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in Sichuan Province shows a small change, and the speed of change shows a gradual change. The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generally shows a “northeast-southwest” distribution pattern, while the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of Sichuan Province shows a small change in the magnitude of the change, and the rate of change shows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patial correlat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unties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 degree of spatial correlation shows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with strong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regional agglomeration. Based on the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for determin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urbanization level of the positive fact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ve influencing factor, whil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the secondary positive influencing factor.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the market size are important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ies in Sichuan Province, while the government’s power is a limiting factor.
nighttime lighting data; Sichuan province counties; economic differences;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編輯 周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