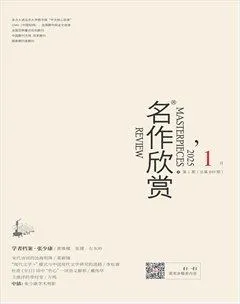從上都到仙都(Chandu)到仙乸都(Xanadu)
羅新教授的歷史語言學考察讓我生出更多疑問
2024年7月31日,我們前往錫林浩特市區之前,去參觀了我夢寐以求的上都遺址。這是目前內蒙古境內唯一的一處世界文化遺產,當然是我們此行的首選旅游目的地。我長期工作生活在大都(在元朝的歷史中心地帶即最近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北京中軸線一帶,曾有十年上班經歷),多年前曾經去看過尚未開發為旅游景點的中都遺址(位于張家口境內),因此對上都的好奇心或興趣非常大,也因此,無論是造型別致、展品豐富的上都博物館還是已成一片荒丘的遺址,我都興致勃勃,看得相當仔細,聽得非常認真。
我注意到:在上都博物館的英文名稱中,“上都”一詞用的是“Xanadu”,而不是音譯的“Shangdu”。我腦海里一下子閃過幾個問題:“上都”是如何音變成“Xanadu”的?兩者真的可以劃等號嗎?為何主事者決定用“Xanadu”,而不是音譯的“Shangdu”或其他英文譯名?
文史專家羅新教授對這些問題有過一些思考和解答,在其歷史地理散文著作《從大都到上都》的長篇前言中,他提出了幾乎跟我一樣的思考:“今日西方語言特別是英語中,上都的寫法是Xanadu(以及在形式和詞義兩個方面都略有變化的Zanadu),雖語源還是漢語的‘上都’,讀音卻已大相徑庭(由兩個音節變成了三個音節)。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他對這個詞在西方語言中的變化做了一番考察,主要提出三個關鍵點(三個人的三部作品):1.“《馬可·波羅行紀》的老法文原版把上都音譯拼寫為Chandu,是基本忠實于上都本來讀音的。”2.“英國旅行記作家與編撰者珀切斯(SamuelPurchas,1577—1626)首先在1614年出版了簡本的《珀切斯游記》,其中有關上都簡介的部分,取材于《馬可·波羅行紀》,但上都的拼寫改成了Xandu,這種改動可以認為是因為從法語進入了英語。珀切斯于1625年又出版了20卷本《珀切斯游記》,其中第11卷有對上都的詳細描寫,繼續用Xandu拼寫上都。”3.“英國著名湖畔派詩人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1772—1834)寫出了英國文學史上的浪漫主義名篇《忽必烈汗》(KublaKhan)……在這首詩中,柯勒律治把《珀切斯游記》的Xandu寫為Xanadu,不知是出于一種誤讀還是有意的創制。由于柯勒律治在英國文學史上的盛名及此詩的廣泛流行,Xanadu不僅成為上都的標準譯名,而且還具備了桃花源一般的特殊意義。”(新星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羅新指出了這一語詞演化的基本脈絡,即馬可·波羅把“Shangdu”讀寫為“Chandu”,珀切斯改寫為“Xandu”,柯勒律治進而改寫為“Xanadu”。
不過,對他的這些論述,我有不少疑問。
比如:“基本忠實”具體如何理解?馬可·波羅為何把“上”這個卷舌音和后鼻音發作“Chan”(在法語中的讀音類似于“仙”)這個非卷舌音和前鼻音?這算“忠實”嗎?“老法文”是什么樣的法文?
再如:珀切斯是旅行記作家還是編撰者,抑或編者?所謂《珀切斯游記》是他自己寫的旅行記嗎?他在1614年出版的《珀切斯游記》是1625年的簡本嗎?兩者都用“游記”命名嗎?珀切斯于1625年出版的《珀切斯游記》是20卷本嗎?他為何以及如何取材于《馬可·波羅行紀》?所謂《珀切斯游記》真相如何?珀切斯只用“Xandu”這一個英文名來指代“上都”嗎?
還如:柯勒律治的詩取材于《珀切斯游記》的哪一部分?他又如何描寫上都?“Xanadu不僅成為‘上都’的標準譯名,而且還具備了桃花源一般的特殊意義。”其內在原因是什么?
力圖一一解答以上三組問題;珀切斯一生出版的三部書都不可翻譯為“游記”
我們先來看第一組問題。馬可·波羅是意大利人,但《馬可·波羅行紀》的原版是用法文撰寫的;因為撰寫者不是他本人,他基本上是口述,幫他記錄并撰寫成書的是來自比薩的魯斯蒂謙。因此,有些比較嚴肅的版本都會在馬可·波羅后面同時署上后者的名號——比薩的魯斯蒂謙(RustichellodaPisa)。魯斯蒂謙是精通法語的意大利人,所以有人說,他手書的原稿是用帶有意大利元素的古法文或者說是所謂的“法意混合語”寫成的。這種文字的優勢在于意大利人和法國人(當然不是全部的人)都能看懂,否則無法解釋為何這部法文書一問世就在意大利頗為流傳。最根本的問題是:魯斯蒂謙只是記錄者,把“Shangdu”音變為“Shandu”的與其說是魯斯蒂謙的筆,不如說是馬可·波羅的嘴,也就是說馬可·波羅早就習慣于把“Shangdu”念作“Shandu”。為什么呢?因為他是從蒙古人那里直接學到這個漢語詞語的發音的,而蒙古語的發音就是“Shandu”,基本上丟掉了漢語中的卷舌音和后鼻音。
我們再來看第二組問題。帕徹斯生于英國埃塞克斯郡的塞克斯特,是一個自耕農(yeoman)的兒子。也許,他曾發下宏愿,要“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但事實上,他根本做不到,他本人曾自承,他從未去過“離我出生的埃塞克斯郡薩赫特200英里的地方”。但他想給別人造成的印象是:他曾“行萬里路,讀萬卷書”,而且他思考的都是關于宇宙和人類的大問題。他營造這個人設的方法是編書,把別人的書(包括書信)編入自己的書,署上自己的名,而且還加上所有格(his),表示書中的一切都是他的(包括經歷和敘述);他企圖占為己有,但有點難為情。于是,他讓人把“his”這個詞的字體印得比前后兩個詞要小許多。在書名上他可謂煞費苦心。不過,他所編的第一部書到了第四版即最后一版印行時(他去世的年份,即1626年),或許是因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帕徹斯加上了書中文章的作者名錄。
帕徹斯樂意或者說刻意選編那些跟海外經歷有關的故事和文字,馬可·波羅關于遠東的文字自然成了他的首選。當然,他會寫一些前言后記,把一些宗教觀念生拉硬扯到那些生動熱乎的游記上去,以申明他出版這些書的大義。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們不能稱他為旅行記作家(哪有不太旅行的旅行記作家?)。有關他的英文材料中,一般稱他為“compiler”(匯編者),最多加上“editor”(編輯者)。他是一個狂熱的編書分子。如果原作是用第一人稱敘述的,那他會改為第三人稱,如“馬可·波羅說……”
除了編書,讓他這個牧師更加狂熱的是傳教;所以他給他所編的內容為游記的書都套上了宗教色彩的帽子:朝圣。他仿佛要讓人把閱讀別人寫的關于遠方或異方的記述當作語言的朝圣。或許他的真正用意是:基督教徒的傳教使命應該無遠弗屆。
帕徹斯一生編過三部書,全以“朝圣”為名。1.1613年出版的是《珀切斯的朝圣之旅,或從開天辟地到目前(1613)在所有時代和所有被發現的土地上觀察到的世界與宗教記述》(PurchasHisPilgrimage,Or,RelationsoftheWorldandofReligiousObservedinallAgesandPlacesDiscovered,fromtheCreationuntothisPresent,1613)。請注意:此書的初版年份不是羅新說的1614年,美國國會圖書館等多家機構藏有這個版本,其有關印行的完整信息是:London:PrintedbyWilliamStansbyforHenrieFetherstone,andaretobesoldathisshoppeinPaulsChurch-yardatthesigneoftheRose,1613。2.1619年出版的是《帕徹斯的朝圣者或小宇宙或人類史》(PurchashisPilgrimorMicrocosmus,ortheHistorieofMan)。3.1625年出版的是《哈克路特的遺作,或帕徹斯的朝圣》(HakluytusPosthumus,orPurchashisPilgrims)。帕徹斯所編這樣的三部書都沒有用“游記”命名,而且名稱還有區別。因此,盡管旅行作家堂·喬治(DonGeorge)說:“每次旅行都是朝圣……旅行是使世界變得神圣的朝圣行為。”(轉引自羅新:《從大都到上都》,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53頁),我們都不應該直接把它們翻譯為“游記”,否則就從書名上剝奪了他虔誠而深刻的信仰用意——每一冊書似乎都是他朝圣的階梯。
第一部《珀切斯的朝圣之旅》頗受讀者歡迎,在帕徹斯去世之前(1626)就出了第四版。每次再版都不是簡單的重復印刷,而是增加不少內容。筆者經眼的是第三版和第四版,分別印行于1617年和1626年的倫敦,第三版分為四部(books,即四個部分parts),第四版分為九部,都比第一版多出不少篇幅,都多達1100多頁;以至于有學者懷疑說,柯勒律治當年在旅途中不可能在箱子里放這么厚重的一本書,還時時拿出來翻看。還有學者說,他可能帶的是另一部書,即《哈克路特的遺作,或帕徹斯的朝圣》。殊不知,1613年第一版的《珀切斯的朝圣之旅》并沒有那么厚,比較方便攜帶。況且,他喜歡這磚頭書,再重也愿意帶著它邊走邊讀,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或不合理。最重要的是:在發表《忽必烈汗》之前專門為之寫的序中,柯勒律治自己明說他讀的是《珀切斯的朝圣之旅》(PurchasHisPilgrimage)。
按照羅新教授《從大都到上都》的前言里的語境邏輯,1613年的是1625年的簡本;殊不知,這是兩部不同的書。兩者名字就不同。1613年的叫《珀切斯的朝圣之旅》,1625年的叫《哈克路特的遺作,或帕徹斯的朝圣》。另外,珀切斯于1625年出版的《哈克路特的遺作,或帕徹斯的朝圣》不是20卷本,而是4卷本。美國國會圖書館等多家機構藏有這個版本的電子版。20卷可能是后來另一個版本的卷數。
《珀切斯的朝圣之旅》第三版(1617)的第四部分中關于“上都”的敘述比較詳細(基本上來自《馬可·波羅行紀》)。此書最后一版(1626)的第四部分中介紹了許多中國城市,也還引用了許多馬可·波羅的材料,但已經不再提及“上都”。大概在那之前不久,珀切斯終于搞明白:上都早就隨元朝的滅亡而灰飛煙滅了。1626年已經是明朝天啟六年(他在第四版中依然說那是萬歷四十年,即1612年——大概是他開始編寫此書的年份,后來沒有改過來),早在257年前,即1369年,元朝亡國之君順帝就被起義軍逼迫從荒敗的上都繼續北逃,這個輝煌一時的都城早就沒有了馬可·波羅筆下的人和物。
在珀切斯的書中,“上都”一詞不止“Xandu”這一種寫法,而是有三種:Xamdu、Xaindu和Xandu。筆者揣測,前兩種可能是排字工人看走眼或誤操作的結果,“m”被拼作“in”或相反。當然,17世紀上半葉的英語還是早期現代英語,與后來成熟的現代英語相比,還有許多不規范的發音和拼寫現象。不僅“上都”沒有英文定名,連威名遠揚甚至讓人聞名喪膽的“忽必烈汗”也沒有,他的英文稱號被珀切斯他們寫作“CublaiCan”,與后世的名稱——比如柯勒律治的寫法(KublaKhan)相差不少。
不僅在17世紀早期的這些英文文獻中,“上都”沒有定名;甚至在柯勒律治發表《忽必烈汗》這首所謂“名作”一個世紀之后,“上都”的英文名也還是沒有固定。英國漢學家亨利·玉爾(HenryYule,1820—1889)的《馬可·波羅行記》英文譯注本是比較權威的(完成于1871年),后來法國漢學家考狄(HenriCordier)對這個譯本進行詳細的修訂補注,于1920年再版。在這個譯本中,“上都”的英文名也有三個而不是一個。亨利·玉爾基本沿用其法文名,即“Chandu”(總共出現10次),更加接近漢語譯音的“ShangTu”一名則出現四次。比較有意思的是,此書目錄中有這樣的一條內容:“Chandu,properlyShangtu”。意思是:“上都”的準確英文寫法不是“Chandu”,而是“Shangtu”。緊接著,編者馬上說:“Kúblái’sAnnualMigrationtoShangtu.”(忽必烈每年移駕上都。)這個內容應該是考狄加上去的,他曾來中國實地考察,所以知道“上都”在中國人口舌上的比較準確的發音。另外,我發現,現代學者們更喜歡用這個比較準確的發音。比如,在1949年出版的伯希和譯注的《蒙古秘史》中(法文標題為意譯的Histoiresecrètedemongols,英文標題為音譯的TheYuanShi),“上都”被寫作“Shangtu”。其77章中有這樣兩句:“Everyyear,[theEmperor]resortstoShangtu。Onthe24thdayof"the8thmoon,thesacrificecalled‘libationofmare’smilk’iscelebrated.”(每年,上駕臨上都。八月二十八日,行馬奶酒祭儀。”)順便說一下,伯希和這位20世紀最杰出的漢學家、最有語言天賦的學者把此處的“八月”翻譯為“第八個月亮”,有意思。
在這個譯本中,柯勒律治所用的“Xanadu”一名只出現了一次,而且是出現在一個叫作巴貝爾(E.C.Baber)的人給譯者亨利·玉爾的獻詩中。其詩云:“Untilyouraiseddeadmonarchsfromthemould/AndbuiltagainthedomesofXanadu.”(直到您從腐殖土中救起死去的君主們/并且再度建造“上都”的穹頂。)這首詩寫于1884年7月20日。也許這位詩人偏愛柯勒律治詩歌中的“上都”之名,覺得這個變得有點怪異的帶有魔幻音色的名稱比那個更加準確的音譯更有詩意。
不過,在社會普遍的語言系統中,“Shangtu”遠遠不如“Xanadu”流行;學者嚴謹的照本念讀,哪能跟詩人不羈的生花妙筆所產生的效果相比呢?話說回來,大眾使用“Xanadu”一詞,早就跟中國的“上都”沒什么必然聯系了。
賞析《忽必烈汗》;“Xanadu”從一開始就遠離“上都”
羅新說,上都“與柯勒律治《忽必烈汗》中的Xanadu絕不相類”。誠哉斯言!柯勒律治在詩序中沒有直接引用《珀切斯的朝圣之旅》中的文字。我想,主要應該是這一段:“InXamdudidCublaiCanbuildastatelyPalace,encompassingsixteenmilesofplainegroundwithawall,whereinarefertileMeddowes,pleasantSprings,delightfulStreams,andallsortsofbeastsofchaseandgame,andinthemiddestthereofasumptuoushouseofpleasure.”(1617年第3版,第472頁)
筆者嘗試譯之:
忽必烈大汗于上都建宮苑,方圓達十六英里,以墻圍之。其地含肥美之草地、宜人之清泉、愜意之溪流,并有諸般禽獸,有鷹犬,亦有獵物。位其中者乃奢華之大安閣也。
珀切斯在引用別人的文字時往往做不小的編輯處理(改動)。與這段話對應的《馬可·波羅行紀》的內容是:
離開上述的城市后,向東北方走三天,就到達了上都。上都是忽必烈大汗所建造的都城,他還用大理石和各種美麗的石頭建造了一座宮殿。
該宮設計精巧,裝飾豪華,整個建筑令人嘆為觀止。該宮殿的所有殿堂和房間里都鍍了金,裝飾得富麗堂皇。宮殿一面朝城內,一面朝城墻,四面都有圍墻環繞,包圍了一塊整整有十六英里的廣場。除從皇宮外,別無其他路徑可以進入該廣場。這個廣場是大汗的御花園,里面有肥沃美麗的草場,并有許多小溪流經其間。鹿和山羊都在這里放牧,它們是鷹與其他用來狩獵的猛禽的食物,這些動物也棲息在這個御花園中……
編者珀切斯沒有親臨上都,所以他只能拾人牙慧;詩人柯勒律治雖然也沒有光臨過上都,但能有所讀,便有所思,有所思,便有所夢,展開想象力甚至幻想力,由點及面,甚而立體化、故事化、陌生化和烏托邦化。
我在上大學時期的英國文學課上就接觸過“Xanadu”這個詞。這個在英語文學語境中絕對具有異國情調的詞在《忽必烈汗》(KublaKhan)的一開頭便出現了:
InXanadudidKublaKhan
Astatelypleasure-domedecree:
我的恩師屠岸先生譯為:
忽必烈汗在上都曾經
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樂殿堂
飛白先生則譯為:
忽必烈汗建立“上都”,
修起富麗的逍遙宮
屠岸先生把“pleasure-dome”譯為“安樂殿堂”(這不符合中國人對宮殿類建筑的命名法),飛白先生則譯為“逍遙宮”。元上都可沒有這兩個建筑。他們可能都沒有去查閱有關元上都的文獻,不知道這座富麗堂皇的宮殿實際上指的是位于其中心的“大安閣”。“安”者,“安樂”也,故云“pleasure”。不過,沒關系,因為柯勒律治本人也不知道這個建筑物,而且他用的不是專有名詞(沒有大寫),所以可以理解為泛指,或者說他已經在詩化史實。
這首詩之所以被公認為是浪漫主義的代表作,是因為它包含大部分浪漫主義詩歌美學的原則和策略。因此,有些學者認為,這是一首詩論詩。這首詩形象豐富、情感充沛;但同時作為浪漫主義詩學主將柯勒律治的作品,它也具有相當多的理論元素或者說詩學思想,即其主題本身就是詩。尤其是這幾行:
我只消用那悠揚的仙樂
就能重建那天宮瑤池,
那陽光燦爛的宮和冰的洞窟!
凡是聆聽者都將目睹。
——飛白譯
“那天宮瑤池”(thatdome)象征的是光彩奪目的詩歌(文本)。浪漫主義詩人認為,詩歌的本源與其說是現實生活,不如說是空幻和藝術。既然詩歌本身就是空中樓閣(“thatdomeinair”),它就可以由夢、音樂和幻象建成,而不需要硬邦邦的物質材料。浪漫主義詩人還認為,詩人可以憑借間接經驗和想象寫作。訴之于耳的往往是間接的,所謂“道聽途說”也;而訴之于眼的往往是直接的,所謂“眼見為實”也。在柯勒律治看來,詩人聽了,就可以見,所謂“聽見”包含著聽覺和視覺兩個動作,而這兩個動作是相互銜接甚至同步的。當然,這個“見”的動作與其說來自肉眼,不如說來自心眼,這個“見”與其說是眼見,不如說是想見——因想象而恍如看見。浪漫主義詩人的目光往往朝上(向星空)、朝外(向遠方)、朝內(向心靈),很少朝下(向自我的現實)或環視(向社會的現實)。他們有時甚至號召或要求“閉起眼睛”(closeyoureyes,見本詩倒數第三行),這樣才能不至于有“五色令人目盲”之虞,這樣才能讓心眼更開更亮。就柯勒律治創作本詩的個案來說,間接經驗無過于書本,打開心眼無過于做夢。據他自己在序言中所述,1797年10月的某一天,他因神經痛服了鴉片酊,然后坐在椅子上閱讀珀切斯編的書,尤其是其中馬可·波羅關于上都的描寫,讀著讀著他就睡著了。鴉片的奇特功效就是既讓人閉上肉眼,又讓人打開心眼。柯勒律治入睡后開始做夢,在夢中他靈感勃發,萬象來奔,毫不費力地得了兩三百行詩。他一覺醒來,居然都能記住,于是他立即奮筆疾書,意圖把夢中所得詩行記錄下來。可惜,他中途被一個來辦事的訪客叫了出去,耽誤了一個多小時,等他打算續寫時,發現夢境與詩句都已煙消云散,無論怎么苦思也無法繼續,遂作罷。因此,這首詩有個副標題,叫《或一個夢境的片斷》。詩中所寫不是來自他的所見所聞(他壓根沒有來過中國,更遑論見過上都的遺址),而是來自他的夢境。通過比對,我們可以發現,本詩與馬可·波羅的敘述有關系的只有開頭幾行,后面基本上都是作者馳騁想象所杜撰的,或者從別處的材料里拿來的。
這是典型的浪漫主義詩歌寫作原則的生動體現,其具體寫作策略則有以下幾條:
1.神話化。上都地區本來有河,亦名“上都”。柯勒律治給河流取的是一個神話中的名字——阿爾浮(Alph)。這是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最長的河流之名(Alpheus或Alfeios)的縮寫。正如古羅馬詩人奧維德所說,阿爾甫斯是一位河神,他追逐河仙阿雷修莎,阿雷修莎逃到西西里島的奧提吉亞島,變成了一座噴泉。阿爾甫斯(河)則在伯羅奔尼撒半島進入地下,在西西里島重新鉆出地面。阿爾浮這個神的名字加劇了本詩的神話色彩,柯勒律治直接稱阿爾浮河為“神河”(thesacredriver)。神話者,人類早期詩歌之一類也,神話化即詩化。
2.遠方化。浪漫主義詩學尚“遠”——時間之久遠、空間之遙遠。阿爾浮讓19世紀的柯勒律治遙想古希臘,時間之遠也;阿爾浮讓英國的柯勒律治遙想希臘,空間之遠也。后面寫到的“阿比西尼亞姑娘”的形象也有類似的功效。
有一回我在幻象中見到
一個手拿德西馬琴的姑娘:
那是個阿比西尼亞少女,
在她的琴上她奏出樂曲,
歌唱著阿伯若山。
——屠岸譯
阿比西尼亞(Abyssinia)是非洲東部國家埃塞俄比亞歷史上一個漫長的朝代,史稱阿比西尼亞王國(或帝國),其存滅時間為1270年到1974年。阿比西尼亞比阿爾浮離英國更遠,更有異國情調。阿比西尼亞少女之所以歌唱阿伯若山(MountAbora),是因為阿伯若山是埃塞俄比亞境內的一座山脈。塞繆爾·帕切斯的《帕切斯的朝圣之旅》說,阿伯若山美得讓人無法抗拒——有人說,它是另一個世外桃源。因此,筆者揣測,柯勒律治之所以要寫阿伯若山,不是因為要強調元朝宮廷里有來自世界各地包括非洲的異人異物,而是因為要把它跟“Xanadu”并舉、作比,都是人間仙境嘛!
蒙古高原上有許多“海子”,這些“海的孩子”都是湖泊,不是海,而且離海很遠。而柯勒律治寫道:
那兒有神河阿爾浮
流經深不可測的巖洞,
注入不見太陽的海中。——飛白譯
柯勒律治用他的神筆或夢筆把遠方的海拉到草原腹地,反過來說,是把草原腹地遠方化了。詩與遠方不可分割,詩是對遠方的憧憬和沖動,遠方化也是詩化之一途。
3,陌生化。神話化和遠方化都有一定的陌生化效果。不過,柯勒律治還有專門的陌生化高招。
招數之一:營造不同于常態的意境,如:
好像施過魔術,
會有女子在下弦月下出沒,
為她的惡魔情人哀哭!
——飛白譯
一個女人在月亮底下出沒和哀哭,已經有點非同尋常,而她哀哭的對象是她的惡魔情人,何其異常!她的情人已經死了變成鬼了吧?為何要用“惡魔”(demon)這個帶有詛咒意味的詞?她對他又愛又恨?他越壞她越愛?“惡魔情人(demonlover)”這個詞組本來就是一個矛盾修飾法,其間兩人的關系以及女人對情人的感情充滿謎團甚至怪異。如果說,這個女人只是自我鬼化,那么那個阿比西尼亞少女本來就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個幻象(vision)。所以柯勒律治此處沒有用表示人的第三人稱代詞“she”來指代,而是用了指向物的“it”。這樣的非人化甚至虛幻化處理無疑能起到非常強烈的陌生化效果。
招數之二:生造新詞。“一個操琴的少女”之“少女”的原文是“damsel”,而不是平常的“maid”或“maiden”。“琴”的原文是“dulcimer”,而不是平常的“lyre”或“zither”——有人認為“德西馬琴”是“齊特琴”的一種。
羅新提出疑問:“柯勒律治把《珀切斯游記》的Xandu寫為Xanadu,不知是出于一種誤讀還是有意的創制。”我的回答是后者,即柯勒律治故意造了一個新詞,給讀者以新異的感受,以引起注意,并加強記憶。與Xandu相比,Xanadu在發音上離“上都”更遠,從而無法讓人直接聯想到上都這個曾經實際存在的都市,而可能會幻想到某個似乎跳出了現實的所在,所謂“世外桃源”也。這首詩的題目假如改為“Xanadu”,更符合全詩的內容,也更能使文本具有方外韻味和桃源魅力。也因此,筆者以為,“Xanadu”已經與那個曾經在中國元朝時期實際存在過的夏都沒有什么關系了,也就不適合返譯為“上都”。由于它曾經過蒙古語和法語兩次音變而長期廣泛被寫作“Shandu”——中國人聽起來像是“仙都”。柯勒律治在中間加了“na”,是為了通過改變這個詞的拼法滿足他求新求異的美學追求,別出心裁,另辟蹊徑。為此,筆者建議把“Xanadu”翻譯為“仙乸都”。“乸”者,“美女”也,“仙女”也,正好是這首詩中間部分所塑造和歌頌的形象。
正是通過神話化、遠方化和陌生化的處理,“Xanadu”這個空間概念樂園化了,成了西方語言中“樂園”的代名詞。筆者以為,本詩以“Paradise”(樂園)一詞結尾,具有非常強的象征意味。第一,作者下筆所要寫的“Xanadu”是一個全然陌生的概念,經過一番高明而奇妙的美學歷程,成了在基督教世界眾所周知的“樂園”。第二,用“樂園”照應“Xanadu”,首尾相銜,使得整首詩已經完滿;因此,筆者認為,本詩已經結束。柯勒律治在序言中遺憾地說,他才記錄下來夢中所得的這區區54行,還有差不多200行沒能記下來,為此還抱怨那位不速之客的打斷。其實,他哪怕把其他所有行數都記錄下來,恐怕也是狗尾續貂,有害無利。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反而應該感謝那位不速之客的到來。這是詩歌寫作最最不可思議之處。它有時是自我完成的,只是借用詩人之手筆而已。詩人之手筆由于慣性不想或不能停下來,而詩歌(或詩神)自己已經了斷,無須再續。高明如柯勒律治,恐怕對此神妙也不明就里。
作者:北塔,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已出版詩集《滾石有苔》《巨蟒緊抱街衢》,學術專著《照亮自身的深淵——北塔詩學文選》和譯有《八堂課》《米沃什詞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