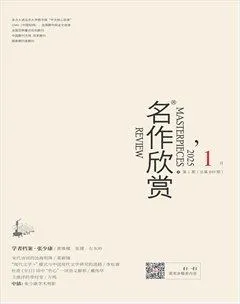作為文學知識與文學研究方法的“文學類型”
在2024年7月15—16日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挑戰與未來——第五屆青年學者創新研討會”上,中山大學林崢老師提出了一個問題,大意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方法論上一直在做“加法”,那么什么才是中國現代文學自己的“家法”呢?這個包含有同音詞的提問引發我的反思,只是限于會議時間匆匆,沒有來得及和林老師當面交流,權且借著李浴洋兄搭建的寶貴平臺,把我的一點相關思考記錄在此。
我對于這一問題的思考更早可以追溯至2020年底,當時復旦大學金理老師組織了一個主題為“外賣騎手的麻辣香鍋”的學術工作坊,其討論的核心內容是《人物》雜志的一篇非虛構報道《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在這次討論中,老師和同學們運用了很多來自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的知識和方法進入這個文本,打開了很多有意思的理解角度。但我同時也產生了一個問題,就是文學研究可以運用來自各個學科的知識和方法,充分對不同學科敞開自身是我們打開文學研究思路的有效途徑,也為整個學科發展帶來了活力,“跨學科”更是成為一種值得鼓勵和提倡的方向。但我們所做的文學研究,特別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是否能反過來為其他學科提供同樣可以借鑒的知識和方法?這樣想來不禁感到有些慚愧,似乎在眾多人文社會學科中,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更多是處于被其他兄弟學科在知識和方法上輸入的一方,而非主動輸出的一方。最簡單的一個例子,我們在做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時,會引用來自歷史學、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學者的觀點、理論和方法,借助他們所生產出來的各種知識,但我很少在這些學科學者的相關論著中,看到他們會引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觀點、理論和方法,似乎我們并沒有為他們提供同樣有價值、有品質的知識。進一步來說,我所關切的問題可以表述為,文學研究是否能生產出真正有效的知識和方法?或者說,什么才是專屬于文學研究的知識和方法?呼應林崢老師的提問方式,就是在各種研究“加法”中,如何確認我們自己的“家法”?
這里我想先從一本“舊書”談起,就是韋勒克和沃倫的《文學理論》,對于這本書,我們以往會有一個認識上的偏見,就是它似乎只關注對于封閉文本內部的研究。但實際上,這本書的內容要遠為豐富且深刻得多。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中討論“文學史”一章時,反對了兩種文學史書寫的傾向,一種“只是把文學視為圖解民族史或社會史的文獻”,另一種是把文學史寫成“一系列互不連接的討論個別作家的文章”,而在其中“缺乏任何真正的歷史進化的概念”。簡言之,前者把文學史看成是政治、社會、歷史發展的注腳,忽略了文學的審美維度和本體特征;后者又把文學史變成碎片化的、隨感式的、即興的審美分析個案的集合,缺乏歷史的眼光和發展的動力。換句話說,韋勒克希望寫出一種既是以審美為核心維度,同時又具有歷史進化觀念的文學史。但問題在于,如何讓一部文學史既是審美的,又是歷史的,這二者之間似乎具有某種內在的矛盾性。對此,韋勒克提出了文學類型的重要意義。在韋勒克看來,“文學類型的理論是一個關于秩序的原理,它把文學和文學史加以分類時,不是以時間或地域(如時代或民族語言等)為標準,而是以特殊的文學上的組織或結構類型為標準”。文學類型一方面包含了文學形式的規定性與文學內部的審美性要素,另一方面也具有歷史進化的觀念,是審美性與歷史性的統一。當然,這里的“文學類型”有著相當彈性的理解空間,既包括小說、散文、戲劇、詩歌等文學體裁(genre),也可以指偵探小說、科幻小說、武俠小說等更細致的小說類型(type)劃分。而韋勒克在書中所舉的理想的文學史寫作典范就是哥特小說,“這一類型具有人們企望一個敘述類型所應具有的所有標準,其中不但有一種限定的和連續的題材或主題,而且有一套寫作技巧”,即哥特小說在小說內容、形式、題材、意象、審美風格、寫作技巧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統一性。在全書“文學的類型”一章結尾處,韋勒克更明確地提出了“文學類型”研究的意義所在:“文學類型這一題目為研究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及它們二者之間的關系提出了重要的問題。”
有趣的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遜作為和韋勒克立場完全不同的理論家,在《政治無意識》一書中也指出:“文類概念的戰略價值顯然在于一種文類概念的中介作用,它使單個文本固有的形式分析可以與那種形式歷史和社會生活進化的孿生的共時觀協調起來。”詹姆遜在這里所說的“文類”概念具有連接文學內部與外部、形式與歷史的中介功能,并認為這種中介功能具有戰略價值。對詹姆遜的這一看法,我們大概可以從盧卡奇、伊恩·瓦特、普羅普、巴赫金、托多羅夫那里找到某些思想和方法上的源頭,但其將文學類型/文類作為形式與歷史的中介,又和韋勒克將文學類型視為審美與歷史相統一的重要命題具有相當的一致性。
回到本文最初的討論,文學類型其實就是一種屬于文學的知識與文學研究的方法,具有打通形式分析和歷史化的巨大潛力。而在當下重提文類研究的另一重意義,是在于對“文本中心論”這一研究范式的某種反撥。隨著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的興起,文本(text)漸漸發展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超級概念,小說是文本,電影是文本,身體是文本,城市街道也是文本,隨著一切研究對象的“泛文本化”,引發了兩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變得單一化,這可以簡單概括為“讀者-閱讀-本文”的行為鏈條;二是文學史研究中的一個老問題,即個別經典文本何以代表整個文學史?面對這兩個問題,文學類型研究同樣具有啟發意義。
一方面,文學類型研究關注的主要對象不再是單一文本,而是聚合的文本群落,換句話說,這里重要的不再是文本性,而是文本間性,即我們關注的不再是單一文本的特征,而是更看重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關系。正如讓-瑪麗·謝弗所說:“類型關系始終是某一特定文本與先前的某些作為模式或規范的文本的復制和(或)變異的關系,在這種程度上,類型關系才可能在超文本關系的領域中構成。”另一方面,不同于以文本為中心的研究過程中具有典范意義的“細讀”(closereading)方法,文學類型研究更宜采取弗朗哥·莫萊蒂所提出的“遠讀”(distantreading)方法,因為我們所要面對的是數量遠超過經典文學文本的非經典作品,也就是瑪格麗特·科恩所說的“大量的未讀”(greatunread)。面對這些堪稱“海量”的非經典文本與“大量的未讀”,傳統“細讀”方法的操作困境在于,既讀不完,也讀不細——很多非經典文本自身并不具備細讀的價值和潛力。但在莫萊蒂看來,對于這些非經典文本的關注又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基于這些大量作品及其宏觀發展態勢的整體性研究才是理想中的文學史研究,否則文學史不過是一個“文學的屠宰場”(TheSlaughterhouseofLiterature)。
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首先,文學類型研究并不排斥文本研究,關注“大量的未讀”并不意味著將所有文本都視為均質的對象,文學研究的民主化并不是要完全地抹平文本之間的差異,那些開創了某種類型模式的典范之作,或者打破了某種類型模式的突破之作,仍值得特別關注。當然這種關注還是要基于文本與其他文本之間的關系,或者文本與某一文學類型之間的關系而展開。其次,文學類型研究不能忽略關于人的研究。表面上看,在文學類型研究中,一位作家不同的作品完全可以被歸入不同的類型之中,比如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之于譴責小說、《新石頭記》之于科學小說、《中國偵探案》之于公案-偵探小說等。從傳統的作家論到文學類型研究,其間似乎存在著一個由作品到文本再到文類的認知上的轉型,而作家的主體性則在這一過程中被割裂或者消除。實際上,作家的生平經歷、生命經驗、創作歷程、思想資源等仍然是我們解讀文本的重要依托,是審美與歷史之間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我們要做的,反而是要在作家與作品的關系中,謹慎地加入文類這一思考的維度,呈現出更加細膩的解讀可能。最后,“遠讀”其實也并不是“細讀”的對立面,而是對“細讀”的補充,甚至可以看作是另外一種“細讀”方式。莫萊蒂即指出,研究者在“遠讀”過程中不僅僅要面對文本,還要聚焦于那些比文本小得多或大得多的單位,比如裝置、修辭、主題,或者文類。而在面對這些更大或更小的單位時,我們還是要對其展開“細讀”,只是這里“細讀”的對象與研究者“細讀”時的自我站位都與傳統的“細讀”方法有所不同。
回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科范疇之中,其實我們已經有不少文學類型研究的典范性成果。比如陳平原老師從《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通過考察晚清與“五四”小說的敘事模式,來討論中國小說發展的古今之變與中西融合;到《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以文學類型為基本單位勾勒清末民初小說的發展歷程,并總結出“承上啟下,中西合璧,注重進程,消解大家”的十六字方針,其中“消解大家”就是在“去經典化”,“注重進程”則同樣強調從整體上把握文學史發展的趨勢;再到《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陳平原老師更是親身實踐,為武俠小說這種具體的類型文學撰寫文學史。又比如王德威老師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其核心思路是認為晚清小說中存在著豐富的現代性可能,然后以四種晚清小說類型——狎邪、俠義公案、丑怪譴責與科幻奇談為代表,指出其“預告了20世紀中國‘正宗’現代文學的四個方向:對欲望、正義、價值、知識范疇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對如何敘述欲望、正義、價值、知識范疇的形式性琢磨”,這正是對類型文學研究方法的一次創造性發揮。如果說晚清小說天然具有類型文學的潛質,那么在“現代文學三十年”中,通俗文學則無疑更適合展開類型研究,對此,范伯群、湯哲聲等諸位師長已經奠定了非常扎實的研究基礎。而且對于通俗文學而言,讀者又是一個不能忽略的重要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談文學類型,就不僅僅是文本的聚合,還包括不同文學類型所關聯的不同的讀者群體想象。此外,類型文學研究還提供了一種打通現、當代文學史研究壁壘的契機,比如從晚清民國偵探小說,到50至70年代的反特小說,再到80年代的公安文學、90年代以來的懸疑推理小說,以及新世紀彌散在各種網絡文學類型與影視劇作品之中的懸疑推理元素……針對不同文學類型的研究構成了不同的理解文學史、書寫文學史,乃至“重寫”文學史的可能性。未來,我們需要的可能不是一部無所不包的、“整全”的文學史,而是多種多樣的、圍繞不同文學類型而展開的類型文學史。
最后,不妨以美國《新文學史》(NewLiteraryHistory)雜志主編拉爾夫·科恩的一句話作為我這篇思考記錄的結尾:“我的基本論點是:文學類型和具體文本是合成過程,可以提供處理文學史中變化的最有效方式……我試圖說明類型理論可以比以主題、概念、時代、潮流為基礎的文學史更有效地展示文學變化……我們需要新文學史,我相信類型理論會提供它。”
作者:戰玉冰,復旦大學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偵探小說史、類型文學與大眾文化、數字人文等。著有《現代與正義:晚清民國偵探小說研究》(2022)和《民國偵探小說史論(1912—1949)》(上下冊,2023),編有《福爾摩斯中國奇遇記》(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