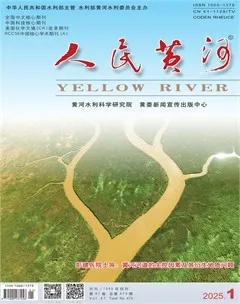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測度、區域差異及動態演進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區域差異;動態演進;黃河流域
0引言
2023年9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哈爾濱主持召開新時代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座談會,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一詞,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新質生產力通過提升生產力質量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涵蓋技術創新、要素配置優化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等多個方面,是新發展階段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
黃河流域橫跨東、中、西部地區,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也是人口活動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區域。然而目前黃河流域產業結構單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仍較為突出,因此亟須發展新質生產力,培育高質量發展新動能,進而推動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走深走實。為此,筆者測度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分析區域差異及來源,探究其動態演變情況,以期為縮小黃河流域區域差異、促進區域協調、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
1文獻綜述
1.1新質生產力內涵
一些學者對新質生產力內涵進行深入研究,形成了不盡一致的認識。有的學者認為新質生產力本質仍是生產力,應從生產力角度去理解。張林等認為新質生產力落腳于生產力,是在科技創新資源轉化、整合下,由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所催生的具有高效能、高質量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王玨認為新質生產力是新發展格局下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相對應和匹配的具有新特質的生產力,且以科技創新為關鍵核心,有助于構建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為支柱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這類觀點將新質生產力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相結合,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拓展,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中國化、時代化。
有的學者認為新質生產力應突出“新”與“質”,然而他們對“新”與“質”的理解略有差異。劉洋認為“新”表明新質生產力是代表新技術、創造新價值、適應新產業、重塑新動能的生產力,“質”則表明新質生產力體現的是生產力在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生產條件下因科技突破創新與產業轉型升級而衍生的新形式新質態。沈坤榮等認為“新”是新構成要素與新經濟表現,“質”是新質量和新質態,新質生產力擺脫了低效能、高消耗生產過程,以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是“新”和“質”的蛻變,代表生產力能級躍遷。從這個維度來看,新質生產力是區別于傳統工業經濟、符合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在新發展階段更符合新發展理念的生產力。此外,也有學者在突出“新”與“質”基礎上,進一步對新質生產力理論進行擴展與補充,如戴翔認為新質生產力內涵和特征至少可以從“新”“質”“力”三個維度進行解讀,其中:“新”表現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等新起點,“質”表現為超越傳統的物質變換范疇,“力”表現為從熱力、電力、網力到算力的升級。
1.2新質生產力測度
部分學者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科學測度新質生產力。王玨等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分別從勞動者、勞動對象和生產資料三個維度對新質生產力內涵進行界定并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利用熵值法測算2011-2021年中國省域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朱富顯等從新質勞動者、新質勞動對象、新質生產資料3個維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測度新質生產力。朱迪等從農業勞動者、農業勞動對象、農業生產資料3個維度測度中國農業新質生產力。盧江等認為新質生產力是一個至少涵蓋科技、綠色和數字三方面的集成體,并將新質生產力分解為科技生產力、綠色生產力、數字生產力,運用改進的熵權一TOPSIS法測度2012-2021年全國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李松霞等依據新質生產力及發展潛力內涵,從人力資源、創新平臺、研發能力、創新環境和創新成果5個方面建立新質生產力發展潛力評價指標體系,通過熵值法賦權、綜合指數法測度了我國30個省份新質生產力發展潛力綜合指數。孫麗偉等基于對新質生產力內涵的理解,從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發展條件3個角度構建新質生產力評價指標體系,測度2007-2021年中國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
通過梳理文獻發現:1)目前關于新質生產力的研究大多為定性研究,關于測度及影響因素等方面的定量研究還比較少:2)不同學者基于不同理論與不同視角對新質生產力內涵的界定存在差異,可能導致所構建的指標體系不能準確反映新質生產力內涵,難以實現評價指標體系與新質生產力內涵、高質量發展要求相融合的目標;3)關于新質生產力水平測度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在全國及省級行政區,對區域經濟帶研究較少。因此,本文將黃河流域作為研究區域,將新質生產力分解為高科技生產力、高效能生產力、高質量生產力3個維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對現有新質生產力測度方法在特征層面的不足進行補充,擴展新質生產力的測度體系和研究范圍。
2研究方法
2.1Dagum基尼系數
Dagum基尼系數(G)是一種測度地區差異的指標,不僅可以測度不同地區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相對差距,而且可以將差異分解,進而探究差異來源.解決傳統測度指標(如變異系數和泰爾指數)僅能測度地區差異、不能解釋差異來源的問題。G可以分解為組內系數G、組間系數Gb及超變密度系數G,分別反映地區內水平差異、地區間水平差異及各地區交叉重疊現象:
考慮到各地區存在交叉重疊現象,Dagum基尼系數具有更強的可解釋性與實用性,因此本文運用Dagum基尼系數探究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差異及來源。
2.2HP濾波法
HP(Hodrick-Prescott)濾波法是一種常用的時間序列分析方法,其數學思想是將時間序列)分解為非平穩的趨勢成分y及平穩的周期波動成分c,即
其中趨勢成分反映數據的長期發展路徑,周期成分反映圍繞趨勢的短期波動。由于趨勢成分Y和周期波動成分Ct都是不可觀測的,因此HP濾波法將待分解的時間序列數據y,視為趨勢成分y受波動影響后的觀測值。本文利用HP濾波法對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進行分解,探究其時序演變情況。
2.3核密度估計法
核密度估計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是一種能有效避免設置函數主觀性的非參數估計方法,用于估計概率密度函數,進而分析數據總體分布和演化趨勢。該方法不使用數據分布的先驗知識,也沒有在數據分布中附加任何假設。概率密度函數為f(x):的均值;K為核密度函數。
核密度函數的選擇直接影響概率密度計算結果,常用的核密度函數有高斯核函數、拉普拉斯核函數、均勻核函數。本文選擇高斯核函數進行核密度估計,分析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及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3個維度的分布態勢及變化趨勢。
3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測度
3.1指標體系構建
基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質生產力的論述,本文從高科技生產力、高效能生產力、高質量生產力3個維度構建包含6個一級指標、14個二級指標、26個三級指標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新質生產力高科技特征體現在重視科技創新及科研成果在以新質產業為代表的前沿科技產業領域中的運用。一方面,科技創新作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只有其水平提高,才能帶來技術性突破,進而推進產業革命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在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作為發展驅動力的背景下,催生了一系列新型產業與未來產業。本文從科技創新和新質產業兩方面刻畫高科技特征。具體而言,選用技術研發、成果轉化衡量科技創新水平,用新型產業、未來產業衡量新質產業發展水平,其中未來產業通過計算機器人安裝密度(機器人數量與就業人數的比值)進行測度。
新質生產力高效能特征體現在生產要素配置效率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發展新質生產力可以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方式,使包括勞動力、生產資料、勞動對象在內的生產要素加快流向核心技術領域,提高生產要素配置效率。尤其在數字經濟時代,要推動各類數字化終端平臺轉變為新型勞動資料,將一切可數字化的資源轉變為新型勞動對象。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發展會推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形成新產業、新領域、新賽道,有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具體而言,用勞動者、生產資料、勞動對象測度生產要素,用人均產值、人均收入來衡量勞動生產率。其中:創業理念借助創業活躍度進行測度,參考王玨等的做法,基于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編制的中國區域創新創業指數IRIEC,客觀、準確、多維度反映各地區的創業活躍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參考王玨等、趙濤等的做法,從互聯網發展和數字金融普惠兩個角度衡量。
新質生產力高質量特征體現在資源投入、生態環保兩個方面。一方面,新質生產力追求可持續發展,摒棄了破壞生態環境的傳統生產模式,借助可再生能源、資源循環利用等環保措施實現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相兼顧的目標: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注重生產過程中的環境友好性和社會責任感,孕育了低碳環保的產業模式、產業空間和產業體系,減輕生態系統壓力。本文采用能源消耗、廢物利用衡量資源投入,采用綠色環保、廢物治理、污染物排放衡量生態環保。
3.2研究區域及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2-2022年黃河流域九省(區)為研究區域,所構建的新質生產力評價指標體系對應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及各省(區)統計年鑒等。原始數據中存在少量缺失值,為了減少樣本損失,采用線性插值法填充缺失值。
3.3測度結果分析
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部分年份綜合得分見表2把九省(區)平均值作為流域得分,上、中、下游地區得分為相應區域內各省(區)得分均值。分析發現,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逐年提升,增長率為10.55%;上游、中游、下游地區新質生產力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0.39%、9.37%、11.43%。寧夏年均增長率最高,達12.39%,可能原因是寧夏經濟發展基礎相對較弱,而近幾年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山西年均增長率最低,僅為7.03%,原因是山西經濟發展比較依賴煤炭等資源型產業,在當前注重生態環境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其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
4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區域差異分析
基于2012-2022年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測度結果,計算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Dagum基尼系數并計算上、中、下游區域內及區域間Dagum基尼系數,結果見表3。
4.1總體差異
2012-2022年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總體G由0.258增大到0.293,年均增長率為1.28%。總體差異在2012-2019年呈現輕微下降趨勢,2019年G最小,2019-2022年G由0.239增大至0.293。轉折點出現在2019年,可能原因是2019年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重大國家戰略提出后,各省(區)政策執行力度和效果存在差異,造成各省(區)在資源配置和發展速度上不同步,導致總體差異呈擴大趨勢。
4.2區域內與區域間差異
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區域內差異變化情況見圖1(a)。上游區域內差異呈現先減小后增大的變化趨勢,分為兩階段:2012-2017年呈減小趨勢,上游區域內G由0.249逐漸減小到0.218:2018-2022年呈增大趨勢,差異逐漸擴大。下游區域內差異變化趨勢與上游相似。中游區域內差異整體呈增大趨勢,G由0.033增大至0.124,其中2012-2016年增速較快,2017年后增速略有下降。區域內差異呈現上游gt;下游gt;中游的特征。
由圖1(b)可以看出,黃河流域上、中、下游區域間差異均呈現波動上升趨勢,大致分為兩個階段:2012-2019年為波動階段,區域間差異均在一定范圍內波動變化,較為穩定:2020-2022年為上升階段,區域間差異持續增大,上下游差異明顯大于上中游差異與中下游差異,呈現由西向東逐漸增大的態勢。黃河流域發展不均衡問題突出,下游在科技創新、教育等方面處于領先地位,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較高,而上游受諸多因素的制約,新質生產力發展相對滯后,因此黃河流域上、中、下游區域間差異較為顯著,且在未來可能繼續擴大。
4.3區域差異分解
為進一步探究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差異來源,分別計算區域內差異、區域間差異及重疊項(即超變密度)的貢獻率,見圖2。由圖2可知,區域內、區域間、超變密度貢獻率均穩定在一定區間內。區域間貢獻率最大,平均貢獻率約為60%:其次是區域內貢獻率,在25%~30%范圍內變化:超變密度貢獻率最小,在9%~15%范圍內變化。綜上,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總體差異主要來源于區域間差異,因此要解決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總體差異,應當以縮小區域間差異為重點。
5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時空演變
5.1時序演變
進一步運用HP濾波法和核密度估計法分析黃河流域、各區域及各維度新質生產力時序演變情況。
5.1.1整體時序演變
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HP濾波分析結果如圖3所示。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趨勢成分變化相對穩定,發展形勢良好。基于周期波動變化進一步分為4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波動下降階段(2012-2016年),此階段處于從傳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的結構調整期,同時面臨消費疲軟等內需問題,周期波動成分呈下降趨勢,略有波動:第二階段為平穩增長階段(2016-2019年),黃河流域開始重視新發展理念,為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補”略有成效,周期波動成分整體保持平穩、緩慢增長的態勢;第三階段為下降階段(2019-2020年),此階段因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而引發黃河流域生產中斷、投資減少,就業市場以及金融市場惡化,導致新質生產力水平下降:第四階段為迅速上升階段(2020-2022年),此階段中央政府提出的“六穩”“六保”等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取得顯著成效,為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的增長提供強大動力。總體來看,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呈上升趨勢,存在一定的波動和下降,符合螺旋式上升的發展規律。
5.1.2分區域時序演變
分區域來看,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表現出上游lt;中游lt;下游的特點。其中上游與中游地區新質生產力周期波動呈W形演變,與黃河流域整體4個階段劃分相似,區別在于上游地區第二階段(2016-2019年)及中游地區第二階段(2017-2019年)為平穩上升階段,此階段以傳統農業和資源型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在經歷產業結構調整后,開始注重科技創新與可持續發展,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得到較大提升。下游地區新質生產力周期波動經歷在第一階段(2012-2017年)的平穩發展后呈V形演變趨勢,從2017年下降至2020年的最低點,隨后通過調整迅速增長。位于黃河下游的河南、山東經濟水平較高,產業結構相對合理、抵抗風險的韌性更強,在經歷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生態文明建設等過程后,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逐步恢復并保持良好勢頭。
5.1.3分維度時序演變
運用核密度估計法探究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綜合得分及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維度新質生產力時序演進趨勢,結果見圖4。首先從分布位置來看,核密度曲線均出現向右移動的趨勢,表明考察期內新質生產力及3個維度均得到提升。其次從分布延展性來看,圖4(a)(b)(c)均呈現出明顯的右拖尾現象,說明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及高科技、高效能維度發展存在顯著差異。圖4(d)的延展性較差,說明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高質量維度不存在顯著差異。最后從分布形態上看,隨時間推移,圖4(a)(b)(c)中主峰高度呈下降趨勢,說明考察期內不同地區新質生產力及高科技、高效能維度發展差異逐漸拉大。然而圖4(d)中峰值高度和位置比較集中,說明考察期內不同地區高質量維度差異趨于穩定,沒有進一步被拉大。
5.2空間演變
5.2.1省域空間演化情況
基于詹克斯(Jenks)自然斷點法將黃河流域各省(區)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劃分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高水平4級,結果見表5。相較于2012年,2022年黃河流域大多數省(區)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得到提升,其中:山東省積極發揮自身優勢,推動高新技術發展,加強對外合作,從中低水平發展成黃河流域唯一的高水平省份;四川、河南、陜西落實強省會戰略,推進高質量發展,實現新質生產力從低水平向中高水平發展的重大突破;內蒙古、山西借助政策扶持并充分發揮資源優勢,但缺乏多元化產業支撐,新質生產力從低水平緩慢發展至中低水平。
5.2.2省域空間分布特征
為更直觀地反映黃河流域省域層面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空間分布特征,借助ArcGIS軟件將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空間演變可視化,見圖5。整體來看,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呈現“自上而下,梯度提升”及兩極分化的特點。一方面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梯度提升,2012年黃河流域各省(區)新質生產力均處于低水平及中低水平,2022年大部分省(區)實現遞進發展,如四川實現“低水平一中低水平一中高水平”的跨越式動態躍遷:另一方面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兩極分化嚴重,發展不均衡。在空間分布上,下游地區始終處于領先地位,且山東省梯度提升速度明顯高于其他省(區),在黃河流域“一枝獨秀”并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寧夏、甘肅、青海受到資源、環境、科技、人才等多方面的限制,仍屬于低水平地區。
6結論與建議
6.1結論
1)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總體呈上升趨勢,發展勢頭良好。具體到各省份,年均增長率最高的省(區)為寧夏,年均增長率為12.39%;最低的省(區)為山西,僅為7.03%。
2)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總體差異呈擴大趨勢,其主要來源為區域間差異。區域間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約為60%。區域內差異則呈現上游gt;下游gt;中游的特征。
3)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周期性波動情況較為復雜。上游及中游周期波動呈W形演變,下游區域周期波動在經歷2012-2017年的平穩發展后呈V形演變。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高質量維度差異不顯著,總體新質生產力及高科技、高質量維度存在顯著差異且差異逐漸拉大。
4)大多省(區)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呈現遞進發展,山東尤為突出,從中低水平躍升至高水平;甘肅、寧夏、青海仍處于低水平;內蒙古、山西從低水平提升至中低水平;陜西、河南、四川從低水平發展至中高水平。整體來看,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發展呈現“一枝獨秀”的斷層式發展格局,兩極分化嚴重。
6.2建議
1)建立健全黃河流域協調發展機制,統籌區域聯動合作。一要加強對黃河流域各地發展的指導和協調,明確職責分工,推動各地形成合力,共同推進跨區域合作與項目協調:二要加強區域間聯系,建設黃河流域綜合交通樞紐,加強水、陸、空交通一體化發展,促進區域間資源、人才、信息等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三要根據各地資源稟賦和產業特色,優化產業布局和結構,實現產業鏈的協同發展,形成產業集群,提高整體產業競爭力。
2)從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維度進行新的戰略部署。高科技維度,要加大技術創新和研發投入,推動產業技術升級,促進產業與科技融合發展,促進科研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應用,實現新技術、新產品快速推廣和應用:高效能維度,要充分發揮數據這一優質生產要素的功能,以大數據等數字新興技術為動力不斷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方式,推動各類優質生產要素以更高效率流向重點領域,提高生產要素配置效率:高質量維度,要減少能源消耗和資源浪費,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投入與使用,減少廢氣、廢水和固體廢物排放,實現資源循環利用,進而實現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
3)以教育、科技、人才作為切入點,縮小兩極分化程度。其一推動教育均衡發展,特別是低水平地區政府應加大教育投入、重視教育資源配置,從根源提升整體競爭力;其二重點加強科技創新和技術轉移,低水平地區應通過建立科技研發平臺,培育高科技企業,吸納發達地區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高水平地區則應持續加強科技創新,通過技術輸出和合作幫助低水平地區提升技術水平:其三人才培養和流動是關鍵,低水平地區要加強人才培養和引進工作,吸引更多高層次人才和技術人才創業就業,推動產業發展和技術創新,同時高水平區域要優化人才政策,鼓勵人才到中西部創業就業,促進人才流動和交流,推動經濟的互補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