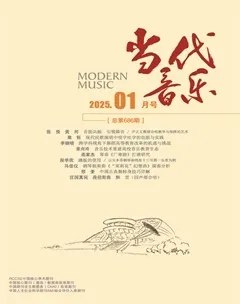數字時代流行音樂的生產與運營
[摘 要] 在數字時代背景下,流行音樂“創作—傳播—消費”的生產運營邏輯依然未變,網絡神曲《孤勇者》的破圈現象則呈現出數字音樂“非線性”產業鏈的新特征和“音樂+”產業融合的新趨勢。具身性、情感交流和亞文化資本在音樂“場景”構建中發揮重要作用,數字時代下流行音樂不僅是聽覺審美的產物,更是社會環境和大眾品味共同塑造的文化現象。
[關鍵詞] 數字流行音樂;生產運營;《孤勇者》;場景理論
[中圖分類號] J639" "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2233(2025)01-0181-03
流行音樂,亦稱為通俗音樂,是一種廣泛流傳且深受大眾喜愛的音樂形式。其特點包括旋律的易懂性、節奏的明快性,以及歌詞內容對日常生活的貼近性等。本文所指的“音樂產業”,系采用廣義概念,是一個以音樂作品為核心,涉及多領域的復雜系統。它涵蓋了音樂創作、表演、出版、制作與發行等核心環節,同時也包含與音樂生產服務相關的各類行業[1],這些行業共同編織成音樂產業的完整生態鏈。《孤勇者》是隨《英雄聯盟》衍生動畫《雙城之戰》上線的中文主題曲,由錢雷作詞、唐恬作曲,陳奕迅演唱。該曲不僅深受大眾喜愛,更在以“10后”為主體的小學生群體中病毒式傳播。本文以該爆火歌曲為案例,探尋數字流行音樂產業的運營規律及其背后的社會文化意義。
一、流行音樂的生產運營模式
音樂產業歷經傳統與數字時代的變遷,生產思維方式發生根本轉變,互聯網平臺成為音樂創作與傳播的新場所,音樂消費方式也隨之改變。然而,數字音樂并未完全摒棄傳統運營方式,其核心邏輯“創作—傳播—消費”仍保持不變,只是在內容與形式上有所創新與發展,兩者交融共進。
數字音樂通過數字化技術實現了生產與傳播的革命性變革。[2]從唱片到數字格式的轉換,展現了產品形式的與時俱進。運營方面,音樂版權組織嚴格把關,音樂服務提供商與電信運營商攜手提供多樣化服務,包括音樂軟件、短視頻平臺等。這些服務最終聚焦于終端用戶,他們購買并消費音樂產品,推動了數字音樂產業的蓬勃發展。隨著產業的不斷進步,數字音樂展現出強大的活力與潛力。音樂類App提供免費試聽與付費增值服務,用戶流量的有效利用為廣告商提供了盈利空間。在我國,數字音樂市場已經形成騰訊音樂和網易云音樂勢如水火的局面,兩大巨頭憑借碾壓式的實力購買獨家版權,成為音樂市場競爭的關鍵武器。
與傳統模式不同,當今數字音樂生產運營各環節緊密互聯。例如音樂人可繞過版權商,直接在抖音App直播或使用音樂,并傳達給個人終端,凸顯數字音樂運營模式便捷性及技術、網絡、企業的融合發展趨勢。
二、舉例典型:《孤勇者》破圈背后的音樂營銷
《孤勇者》并不像以往爆紅神曲(如《小蘋果》《江南style》等),它是脫胎于電競,實現了“電競+音樂”的創新營銷,其成功在于傳播路徑和音樂營銷策略,使其從游戲動畫主題曲轉變為經久不衰的網絡神曲。
(一)現象分析:歷經五個階段逐步出圈
針對《孤勇者》“破圈”現象,本文梳理歌曲傳播路徑將其演變分為五大階段。
1.在游戲迷與樂迷圈率先流行
2021年11月,隨著EDG戰隊贏得英雄聯盟總決賽冠軍,《孤勇者》MV迅速上線。同時,拳頭游戲推出的《雙城之戰》動畫也發布。恰逢賽事熱潮,加上陳奕迅的廣泛粉絲基礎,歌曲一經發布便在各大排行榜獨占鰲頭。此時,歌曲只是打通了玩家與樂迷圈層,尚未出圈。
2.娛樂圈翻唱“造勢”
《孤勇者》上線后不久,眾多明星翻唱不勝枚舉,如楊坤、楊丞琳等紛紛在《閃光的樂隊》《乘風破浪的姐姐》等綜藝中翻唱此曲。明星效應助力歌曲火爆,《孤勇者》在社交平臺炙手可熱,相關話題頻登微博熱搜,如那英等人改編翻唱的微博話題總閱讀量高達1.4億,展現了《孤勇者》的廣泛影響力和受歡迎程度。
3.在低齡人群“出圈”
《孤勇者》在娛樂圈“破圈”后,迅速風靡不同年齡層,尤其受低齡人群歡迎。2022年初,短視頻博主將其作為背景音樂,微博上也出現了“小學生愛唱孤勇者原因”的話題,閱讀量破億。此后,《孤勇者》在學生間傳唱度飆升,各種創意演繹層出不窮,如班級舞蹈、幼兒園體操等。更有一短視頻博主與小學生“對暗號”的視頻走紅,一度成為網絡熱梗。
4.“二創”改編熱潮
“假期版”“奧特曼版”“熊出沒版”等搞笑二創《孤勇者》版本在小學生群體風靡一時。B站UP主們則以幽默詼諧、戲謔調侃的方式進行二次創作,通過拆解、混搭和巧妙引用,解構羅翔對法律知識的講解,創作出別具一格的“不法版”,引發廣泛關注。
5.被主流媒體“點名”
《孤勇者》的出圈,大眾傳播功不可沒,而媒體報道更是錦上添花。《人民日報》官方微博、視頻號和微信公眾號紛紛下場報道,其中微博話題閱讀次數高達2.6億,微信公眾號相關推文閱讀量也突破10萬。央視、新華社等權威媒體在抖音平臺多次選用這首歌作為背景音樂,推動了其在全國范圍內的廣泛傳播,讓《孤勇者》成為人們心中的熱門金曲。
《孤勇者》的出圈之路跨越了電競圈、樂迷圈、娛樂圈、泛年齡圈層、官媒圈等多個領域。這幾個階段在時間線上相互交織,呈現出一種百花齊放、多元共融的態勢。
(二)運營策略:音樂制作、版權、跨平臺與資本共贏
對《孤勇者》傳播現象進行歸納和挖掘,可以總結出歌曲背后的運營策略。筆者將孤勇者的運營策略總結為——“天時地利人和”:音樂制作、版權、跨平臺與資本共贏。
1.歌曲定位:具象構建與平民英雄刻畫實現共情傳播
首先,作為一首音樂作品,《孤勇者》精良的創作和卓越的品質不容忽視。作曲家錢雷和女作詞人唐恬為歌曲注入了深刻內涵和獨特韻律感,使其易于學唱和傳播。歌曲定位為“中文語境下的流行電子燃曲”,既具有時尚感又充滿傳播力。此外,歌詞中的征召式表達,如“去嗎?去啊!”“戰嗎?戰啊!”等,直戳人心,激發了人們對平民英雄形象的贊美和共鳴。唐恬個人對抗癌癥的堅韌勇敢,更是為歌曲增添了深刻的情感內涵,使其不僅僅是一首電競歌曲,更是對生活中每一個“小人物”的高唱。
2.平臺規劃:資本運作、短視頻引流與官媒加持實現大眾傳播
《孤勇者》的成功,離不開各版權方與平臺方的資本運作。通過視頻平臺與音樂綜藝的聯動,結合明星影響力,歌曲得以廣泛推廣。在音樂版權領域,各大音樂類App競爭激烈,但最終獲益的主要是三個關鍵制作方:北京夢織音傳媒、索尼音樂版權代理及EAS MUSIC LTD,他們各自擁有歌詞、曲及錄音作品版權。同時,短視頻平臺上的自媒體博主通過翻唱吸引關注,MCN公司精準投資助力網紅翻唱蹭熱度,引發歌曲全網共振。主流媒體與社交平臺的正面宣傳和用戶互動,更推動歌曲裂變式傳播,擴大其影響力。
三、歸納特征:數字流行音樂產業特征
(一)核心運營流程:“創作—傳播—消費”
數字流行音樂產業在迅猛發展的數字技術下,依舊維持著“音樂創作—歌曲傳播—用戶消費”的原有模式。音樂公司仍居產業鏈頂端,音樂產品為產業鏈的基石。然而,形式上卻日益多樣化,如新舊媒體互動、音樂演出、視頻直播等融合創新。創作層面,數字平臺拓寬了音樂創作空間,實現與用戶共同創作,形成多元風格。傳播環節上,全類型平臺參與打通了歌曲傳播渠道。在消費環節,用戶參與度提升,通過購買、分享、評論等方式深度參與音樂消費。
(二)非線性產業鏈:各運營環節主體互動
就信息傳播角度而言,傳統音樂生產運營流程的單線型結構限制了生產運營主體與用戶間的溝通,導致反饋有限。然而,數字音樂運營模式則呈現出一種“非線性”的結構特征[3],使得任意環節之間都能進行充分的表達和溝通。例如,內容提供者與音樂消費者能夠即時廣泛交流,有助于用戶反哺內容,推動運營商不斷優化改進運營模式。
就整合營銷角度而言,數字音樂運營鏈條的整合主要有兩種捆綁銷售模式。一是將數字音樂服務與電信運營商捆綁,如彩鈴服務滿足了用戶展現個性和品位的需求。但隨著5G時代的到來,移動數據流量限制不再成為用戶使用數字音樂服務的阻礙,因此出現了音樂數據流量與數字音樂服務的捆綁合作,如QQ音樂的流量包月服務和“綠鉆會員+音樂流量包”的組合服務。另一種是將數字音樂服務與特定音樂內容捆綁,內容提供方更傾向于與音樂平臺簽訂獨家版權合作協議,平臺因擁有獨家內容而吸引更多用戶流量。
(三)“音樂+”產業融合:橫向縱向交叉滲透
隨著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產業融合現象日益顯著,音樂產業與其他產業間的產業滲透、交叉及重組愈發頻繁。這種重組不僅發生在聯系緊密的產業間,還廣泛存在于同一產業內部的不同行業之中。[4]流行音樂因其獨特屬性,能夠與其他多種類型的內容和服務相結合,既可以獨立成為作品,也能作為輔助因素配合其他場景、產品或服務。因此,流行音樂擁有極其廣闊的應用空間。
其一,橫向融合,拓寬內部。流行音樂與視頻的結合,不僅作為視頻營銷的輔助手段,而且視頻的播放也在無形之中推動了數字音樂的廣泛傳播。以抖音短視頻平臺為例,其背景音樂(BGM)已經成為眾多數字音樂作品的重要推廣途徑。此外,音樂公司與音樂服務商之間的緊密合作,能夠實現互利共贏的局面。比如,韓國YG公司與QQ音樂締結戰略聯盟,SM 公司與網易云音樂達成深度協作,這些合作使得韓國娛樂公司得以借助中國音樂App拓展中國市場,而中國音樂服務提供商則能吸引更多粉絲進行音樂消費。
其二,縱向融合,跨界合作。流行音樂與電影產業的結合,為電影帶來了豐富的音樂元素,作為主題曲或推廣曲有效提升了電影的傳播效果。以電影《一秒鐘》為例,其推廣曲《給電影人的情書》由中國好聲音冠軍單依純翻唱,歌曲與電影相得益彰,取得了雙贏的佳績。此外,流行音樂與游戲、電競產業的結合也呈現出蓬勃的發展態勢。數字音樂能夠為游戲產品定下基調,而游戲產品又能為數字音樂吸引大量粉絲。例如,作為“電競+音樂”的成功營銷范例,《孤勇者》充分展示了跨界合作的巨大潛力。流行音樂已經實現了與多個產業的跨界合作模式,其創新潛力巨大。
四、總結規律:作為流行文化的數字音樂
(一)流行音樂:被大眾品味所賦予的集體文化
自20世紀70年代,文化與流行音樂的關系便成為學術熱點。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研究戰后工人階級青年文化,將其置于社會經濟力量背景中,視其為象征性抵抗。此后,研究焦點轉向流行音樂本身驅動審美反應的能力,而非基于階級的統一反應。當前,“場景”“部落”“品位文化”等概念被用來強調集體文化層面對流行音樂意義的理解及音樂品味作為審美價值的重要性。流行音樂由此成為大眾品位所賦予的文化,同時大眾以流行音樂構建自己的身份。
(二)“場景”:流行音樂生產消費的概念框架
“場景”是理解流行音樂產消的重要概念框架。Straw認為“場景”超越特定地點,反映并實現不同群體間的關系狀態,將“場景”理論化為“在地”和“跨地”兩個維度的現象。[5]“在地”場景通過演出活動聚集粉絲,增強歸屬感;“跨地”場景指地理分散但審美相似的群體。還有學者提出“虛擬”場景作為第三維度,通過互聯網技術實現網絡互動。“在地—跨在地—虛擬”對應著流行音樂生產消費的發展歷程,從傳統的演唱會、到CD/mp3,再到如今的抖音,音樂場景的變化體現出消費方式的改變。
1.具身性維系音樂“場景”
具身性(embodiment)凸顯了身體在音樂場景社會文化構建中的關鍵作用。在流行音樂研究領域,伯明翰學派通過結構主義與后亞文化理論,深入探討意義生成過程,揭示行動者行為與文本創作對群體身份與抵抗意識的表達。Driver則指出,音樂場景作為社會文化空間,身體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具身性對于構建與維系音樂場景至關重要。[6]以《孤勇者》虛擬場景為例,小學生的“身體表演”引人注目,體操表演、“對暗號”言語互動或面部表情等共同維系音樂表演的活力與完整性,展現了具身性理論的實踐意義。
2.情感交流提升音樂“場景”氛圍
身體作為情感交流的媒介,在音樂場景中扮演著重要角色。[7]在《孤勇者》的爆紅視頻中,與陌生小孩對歌詞的互動、小學生拔河失利后的齊唱,都通過孩子“在場”為場景注入了獨特的情感能量,使之成為一場別具一格的表演。對于同樣沉重有力的歌曲,小孩與成年人的演唱能帶來不同的氛圍,這種氛圍取決于不同參與者在音樂場景中的動作和演唱方式。因此,這一場景代表著:個體短暫地被聯系在一起,所有參與者都存在著對類似喜悅情緒的想象。
3.“亞文化資本”:尋求身份認同
Thornton提出的“亞文化資本”概念,強調個體與同齡人文化和知識的契合度。[8]在媒體傳播的影響下,社會成員從遵循社會定位轉向自發參與和尋求認同,文化參與也從刻意設計轉變為感官自然的音樂知識。《孤勇者》最初由博主在抖音平臺助推發布,為提升“亞文化資本”,社會成員自發參與其傳播的音樂虛擬場景,尋求身份認同,視聽感官逐漸適應并習慣這種音樂場景,以達到與同齡人知識文化水平相符合的程度。MCN公司和網友造勢、網紅爭相模仿,使受眾不斷進入相同場景,身體與場景不斷互動,最終形成了一種文化迷因和自然的音樂知識。
結" "語
目前,流行音樂已經不僅是純粹的聽覺審美,而是與視覺審美共同構成了“音樂場景”。不同于阿多諾對文化產業等藝術復制行為的全面否定,本文更愿意將流行音樂視作社會環境和大眾品位的文化產物。在流行音樂“場景”中,具身性和情感交流對構建、維系“場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社會成員自發參與并尋求認同。
參考文獻:
[1] 趙志安.中國音樂產業發展報告2018[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9:3.
[2] 顏胤盛.數字音樂傳播的變革:新驅動、新樣態與新路徑[J].人民音樂,2023(10):78-82.
[3] 黃斯琪,張曉宇.音樂運營管理中的新理念與實踐探討[J].中國教育學刊,2018(07):117.
[4] 臧志彭,張軒宇.價值鏈視角下全球音樂產業并購網絡研究[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34(01):44-57.
[5] Straw W. Systems of articulation, logics of change: communities and scenes in popular music[J].Cultural studies,1991,5(03):368-388.
[6] Driver C, Bennett A. Music scenes, space and the body[J].Cultural Sociology,2015,9(01):99-115.
[7] 王娟.參與、呈現、滿足:虛擬世界的身體傳播轉向——基于數字平臺“打卡”行為的分析[J].當代傳播,2023(05):104-108.
[8] Thornton S.Club cultures:Music,media,and subcultural capital[M].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6:1-13.
(責任編輯:莊" 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