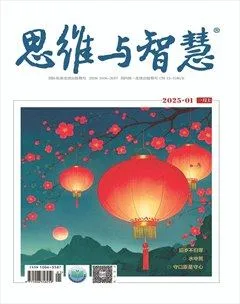漸至佳境
《世說新語·排調(diào)》講顧愷之吃甘蔗要從尾梢吃起,慢慢吃到根部,有人問他為什么這樣吃,他說這樣可以“漸至佳境”。《晉書》中也有這樣的記載。依顧愷之所言,可謂先次后好,先苦后甜,苦可細(xì)細(xì)體會(huì),甜也會(huì)逐漸醇厚,讓人回味。總之,這樣可以慢慢地、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到達(dá)美好的境界。
之前讀書,有人論及苦甜之序,總要以壞蘋果和好蘋果為例,說先吃壞蘋果后吃好蘋果,吃到好蘋果時(shí)可能它們已壞了,最后吃的都是壞蘋果,滋味必然不好受;而若先吃好的,再吃壞的,至少能品到好滋味。但我覺得,這是理想狀態(tài),就怕是好蘋果下肚,再?zèng)]有去吃壞蘋果的想法了。人生在世,享受榮華富貴后的貧苦,注定要難于貧苦之后體會(huì)榮華富貴。
不過,即便以顧愷之吃甘蔗之法,也怕尾梢吃了好久,肚腹有限,到后來根部吃不下了,也就是最美味的部分沒機(jī)會(huì)吃了;以他的次序吃,可能也不會(huì)漸入佳境,畢竟這只是一種感受,它最難以把握。有時(shí),擁有最好的東西而不自知,等到失去了,比較也就產(chǎn)生了,故有追悔莫及之感。
前幾天,我們的午餐有盆皮皮蝦,個(gè)頭不大,但趕上金秋時(shí)節(jié),蝦肉還算緊實(shí)。我對(duì)海鮮不感冒,只是機(jī)械地剝,放入嘴中,覺得比螃蟹易吃而已,要說它多么美味,始終也談不上。直到我吃的最后三兩只,甫一入口,便覺不咸不淡,鮮美異常。這種味道,可以閉上眼睛,讓感覺如絲線一樣延長(zhǎng),越回味越神往。不知道顧愷之所說佳境是不是這種感覺。
佳境難尋啊,其實(shí)佳境也難以持久擁有!看過一幅元代畫家張渥繪的《雪夜訪戴圖》,所依據(jù)的是東晉王徽之雪夜乘舟訪問摯友戴逵的故事,畫家以簡(jiǎn)練的線條,刻畫了人物的精神面貌。畫面中河岸古樹枝干遒勁,沖天向上,葉片全無,一派嚴(yán)冬氣象;徽之坐在船艙,縮頸袖手看書,神態(tài)生動(dòng),別有趣味。在故事里,徽之興起而去,興盡而歸,連友人都沒見到,但也不能說他未到佳境吧。
翻到《世說新語》的《任誕》篇原文,可知徽之在會(huì)稽郡的山陰縣,夜里下了大雪,他一覺醒來想喝酒,就邊喝邊吟誦左思的《招隱》,忽然想起戴逵。戴逵當(dāng)時(shí)身在剡縣,現(xiàn)在看不太遠(yuǎn),以古人論還是不近的,好在水路即通,“夜乘小船就之”。船行了一夜才到,到了門口卻不進(jìn)去,又返回山陰了。不知道友人若知道,又會(huì)怎么想?
一夜的旅途,消磨了王徽之見好友的意念,往日相聚的美好必定幾番涌上心頭,或許某次會(huì)面的場(chǎng)景、言語甚至表情都還記得,就像昨天發(fā)生的一樣。這不是現(xiàn)實(shí)的見面,而是精神層面的溝通,說得傷感點(diǎn),好像明人歸有光的手撫枇杷樹,抬頭望見樹冠如蓋,憶及亡妻之種種。這樣想過,徽之若此,友人亦應(yīng)欣慰。
身為凡人,即使說不出什么大道理或干不出什么大事業(yè),亦能好好生活,感受所嘗到的酸甜苦辣。漸入佳境,也像經(jīng)歷少年求學(xué)之艱辛,長(zhǎng)大品悟生活之多種層面的美好,本來就沒有什么不好吧!
(編輯兔咪/圖槿喑)
- 思維與智慧·上半月的其它文章
- 組個(gè)局
- 蹭飯
- 一輩子的柿
- 頭腦清醒的鴕鳥
- 月好風(fēng)清
- 蛇年趣擷蛇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