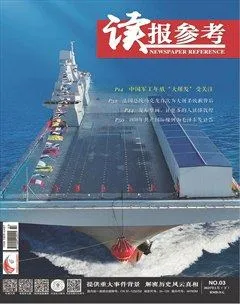金口:明清海上絲綢之路北方航道的重要節(jié)點
青島作為東方大港,先秦有瑯琊古港,隋唐有大珠山港,宋元有板橋鎮(zhèn),明代晚期至青島港開埠之前的300多年間則以即墨金口為代表。
一
"金口古港,位于山東半島南海岸黃海之濱,膠東大河五龍河入海口丁字灣西端,明代晚期開埠,至今已有400多年歷史。
"早在距今約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晚期,此地已有東夷先民在此居住,留下北阡、南阡二里等著名遺址;夏、商、周、春秋,屬東夷萊子國;戰(zhàn)國后,先后屬即墨邑、即墨縣、皋虞縣、不其縣等;隋代后屬即墨至今。明代隆慶朝以前,此地偏距海曲,“既非車轂輻輳之地,絕無商賈往來之蹤”。明中葉,有金姓夫婦二人逃難至此,結(jié)草為廬,捕魚為生,始稱“金家口”,簡稱“金口”。明萬歷六年(1578年),天津武清人許鋌任即墨知縣,為解決民生問題上書建議開放“墨邑海口”,得到明廷認同。萬歷到天啟年間,金口與當時即墨境內(nèi)的青島口、女姑口、沙子口等口岸次第開埠。
"金口,位于中國南北海上航道之側(cè),為港闊浪平的天然“避風(fēng)港”,從此沿五龍河上溯可及山東半島腹地,陸路西通膠州、高密、濰縣、青州府、濟南府,揚帆入海可達遼東、京津、蘇浙及朝鮮;丁字灣海口南北兩岸分別有軍事重鎮(zhèn)雄崖守御千戶所(在今青島即墨區(qū)田橫鎮(zhèn))和大山備御千戶所(在今煙臺海陽市辛安鎮(zhèn)),明朝時曾以千名海防官兵嚴密把守,地理交通安全優(yōu)勢突出,發(fā)展速度冠于其他口岸。
"明亡清興之際,為對抗和削弱南明抗清力量,清廷實施海禁政策,順治十二年(1655年)下令沿海“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六年后強行將江、浙、閩、粵、魯?shù)仁⊙睾>用駜?nèi)遷30-50里,30年間金口海運大受影響。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天下一統(tǒng),清廷開海禁、設(shè)海關(guān)、定關(guān)稅,金口海運逐步恢復(fù)并超過了明代的規(guī)模。
"乾隆年間,經(jīng)過一百多年曲折發(fā)展,金口終于迎來“通四海、達三江”的繁榮景象,高峰時每天進出港船只百艘以上,蟻舟盈港,商舶輻輳,南客北旅,往來不暇,貨物多為生產(chǎn)生活資料和膠東土產(chǎn),出口花生、大豆、沙參、食油、食鹽等,輸入布匹、竹、棉、麻、杉木、桐油、白糖等。金口市井日益繁華,城區(qū)占地4平方公里、人口2萬多。同治年間,東海關(guān)開始在金口設(shè)卡收稅。1926年出版的《中華新形勢一覽圖》記載金口:“市街寬敞,店肆櫛比,為沿海城市之冠。當煙臺未開埠以前,南北貿(mào)易,此為樞紐。”
"港口發(fā)展帶動了運輸業(yè)和修造船業(yè)的發(fā)展,而興盛的海運又造就了一批大商號。最有名的商號“來永春”,即為木匠出身、販鹽致富的李秉和在乾隆年間所開,輝煌時曾在全國各大城市開設(shè)“春”字號商鋪120家,號稱“一百二十春”。為尋求神祗庇護,金口士紳客商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捐資建造“天后圣母行宮”,為山東境內(nèi)規(guī)模最大的天后宮。
"經(jīng)濟的繁榮進一步促進了文教事業(yè)發(fā)展,從這里走出了清代封疆大吏初彭齡、理學(xué)名家韓揆文、武林宗師韓慶堂、海洋學(xué)家侯國本、邏輯學(xué)家金守臣等歷史名人。
二
"斗轉(zhuǎn)星移,時代更替,進入20世紀,金口貿(mào)易逐漸萎縮,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煙臺和青島相繼崛起。煙臺港、青島港吞吐量急劇增長,金口港吞吐量日漸削弱。二是交通改道。膠濟鐵路通車后,金口的交通和貿(mào)易地位進一步下降。三是港口淤積。五龍河泥沙入海導(dǎo)致丁字灣水域水深日淺,加之沿岸河流兩岸植被遭破壞,金口港道大范圍淤積,不再適合大型船舶進出。盡管如此,青島港開埠后,金口作為輔助港口的作用依然長期存在。1935年時,金口港吞吐量依舊達到年出口6300萬斤花生大豆、15000擔(dān)食鹽,進口300萬斤桐油的規(guī)模。這是金口港的余暉。
"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金口港衰落之勢加劇。1937年8月淞滬會戰(zhàn)初期,“金長生”“旺長興”“金福壽”“楊永盛”等商船從金口出發(fā)滿載豆油抵達上海港后,奉國民黨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之命無條件自沉于吳淞口以防堵日艦。1944年6月,駐青島的日軍用汽艇,將停靠在栲栳灘的“金玉壽”“金永年”“新興泰”“金永來”“金同興”等商船,全部“征用”為往來日本與青島的運輸船。
"1949年以后,丁字灣淤積愈發(fā)嚴重,進出金口港要等高潮位時才能進出。20世紀六十年代,金口港最終被青島港完全取代,完成了歷史使命,退出了歷史舞臺。
"近年來,文物考古部門聚焦青島作為“海上絲路”重要節(jié)點相關(guān)問題,對金口古港遺址及其周邊進行了大范圍勘探。在考古勘探中,古港碼頭、天后宮、望海樓、關(guān)帝廟、民居、祠堂、古路、古橋、古井、古沉船、石碑刻、油碾盤、建筑基礎(chǔ)與構(gòu)件、商號票券、商會印章、驛站名冊、族譜文牒等眾多遺跡遺物重見天日,金口港遺址核心區(qū)的建設(shè)布局一一清晰顯現(xiàn),充分印證了昔日金口港南北商貿(mào)要沖的重要性。金口古港作為明清海上絲綢之路北方航道重要節(jié)點的歷史地位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