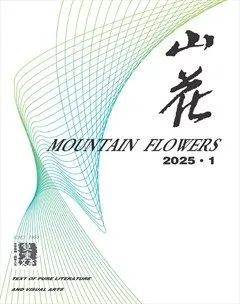你是我的女兒嗎
1
救護車的聲音在樓下的院子里嗚嗚地響,她蓬亂著頭發(fā),剛才發(fā)生的事還沒有平息。她喘著氣心慌意亂地走過去,趴在窗邊往下看。車頂紅藍閃亮的信號燈不停地轉(zhuǎn)動著,車身上白底藍字寫著:精神治療中心。她開始發(fā)抖,幾個穿白色長褂的人,從車里跳下來,正朝著單元樓道疾步跑過來。
她轉(zhuǎn)身去看正在接電話確認單元和樓層的女兒——小蔓。
剛才她們吵架了,小蔓砸了東西,還將一個杯子打在她身上,并嘶吼著說她有嚴重的精神病。這已經(jīng)不是第一次了。她認為小蔓才是真的有精神疾病,動不動就歇斯底里地摔東西,而且每次都拿東西朝著她身體的重要部位砸。有時候杯子直接瞄著她的頭飛過來,那種定要置她于死地的決心,讓她畏懼難安。小蔓自從結(jié)婚后,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女婿則是連面都見不著,但他卻無處不在地操控著家中的一切,特別是她的女兒。
“我自己生的女兒肯定不會將我關(guān)進精神病院,因為我根本沒有病,一切都是女婿指使的。”每次她們發(fā)生沖突,只要她不小心說錯一句話,女兒都要咆哮。她說:“就是一句簡單的話而已,你為什么要那么大的反應(yīng)?”女兒卻總是像被點燃了一樣,叫囂著要送她去精神病院。
開始她還正常地訓斥女兒,沒有家教,誰家姑娘這樣說話之類的,女兒就摔東西,先是摔在地上,然后就往她身上摔。
她問女兒是不是女婿讓她變成了現(xiàn)在這個樣子?這話就像捅到了馬蜂窩一般,女兒撲過去就要廝打她,如果不是外孫開門站在她們跟前,女兒早就抓住了她的頭發(fā)。
后來不管發(fā)生了什么,也無論女兒說什么,她都盡量沉默著。只要她沉默下來,小蔓身上的火焰也就慢慢熄滅了。
她沒想到這一次,女兒真的就打了精神病院的電話。
電梯門開了,腳步聲朝著她家涌過來,然后是拍門的聲音。女兒走過去開門時,她看了女兒一眼。她看見女兒眼睛里全是眼白,像是時間和生活中的一段留白。
門開了,穿白褂子的人進來了。女兒指向她,他們朝她走過來。
她喊了聲:“小蔓,我的兒啊,那個魔鬼都對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她聲嘶力竭將壓了很久的話終于說出來了。他們要強行將她帶走,她掙扎著說:“你們聽我說,我沒有病,一切都是那個魔鬼操縱的。”
他們踩過摔碎的玻璃片,其中一個人還把地上的碎片踢到一邊。幾個人架著她往外走,她越是說她沒有病,他們就越將她扯得緊。她知道有病的其實是女兒,但是她不能說出來,她不可能看著女兒被精神病院的人帶走,不可能像女兒看著她被帶走一樣,只有喪失理智的人才會無情。
這一次,女兒不僅將杯子摔在了她身上,還動手打了她,抓扯她的頭發(fā)。她知道女兒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了,她雙手護住頭,任憑女兒狂亂地一陣猛擊。在那短短的瞬間,她竟然想起了死去的丈夫臨終前的眼神和說過的話:“你千萬不要賣掉房子,姑娘受女婿操控,他是個魔鬼。”
她不知道自己跟女兒的出路在哪里。心臟上扎滿了刺,她在這樣的刺痛里絕望得近于麻木,她蜷縮著抱住頭,像一個孩子接受懲罰那樣逆來順受。女兒正常的時候,她也勸過女兒離婚,可這句話一出口,女兒的反應(yīng)就更激烈,更加確定她患有精神病無疑,并且四處搜集關(guān)于精神疾病的資料,試圖進一步讓她接受這一事實。
救護車開來前,女兒進房間去了。她正準備清掃地上的碎片,拿著掃把從廚房出來,她在廚房的玻璃門上,看見了自己蓬著頭驚慌錯亂的神情,然后就聽見了救護車開進院子里的聲音。她看見女兒拿著手機從房間走出來,已經(jīng)整理好了剛才瘋狂的情緒,兩只手將棕色的頭發(fā)捋了又捋,還對著她往嘴巴上涂了口紅,像是立馬要出門見人的樣子。
她喊著女兒的名字:“小蔓,小蔓,你知道的,我沒有病,是那個魔鬼有病,他這樣做到底是為什么啊?”
她越是掙扎著說自己沒病,他們就越是將她控制得死死的,使出了殺豬的力氣,將她拖拽到救護車邊。然后,兩個人在上面拖,兩個人在下面搡,好不容易將她按到座位上,用帶子將她綁定。她已經(jīng)是滿頭的汗水,加上滿面的淚水。
醫(yī)生們都上車后,女兒提著行李箱也上了車,看來她是早有準備。女兒坐在靠窗那排的前座,自始至終沒有轉(zhuǎn)過頭看她一眼。中途女兒還接了一次電話,她知道是女婿打來的,這一切都是他制造的,她通過車窗玻璃看到女兒說話時悄悄朝她這邊看了一眼。
阿春說得對,女兒正被女婿PUA。阿春讓她去看一個叫《煤氣燈下》的電影,她只是在網(wǎng)頁上打開這部電影的介紹看了,完全沒有勇氣看這部電影,她不想體驗像針扎一樣的感受。
車子經(jīng)過“阿春超市”的時候,她從車窗玻璃的反光里看到阿春和幾個婦女,她們站在超市門口,她不知道她們有沒有看見她。車身上明顯的標志,讓所有人都知道車子的去處。原本她們今晚還約了她一起去超市看《紅樓夢》,幾天前她還給她們講了莫言。
她們都是從黑龍江來北京投奔子女的老鄉(xiāng)。阿春是五六個老鄉(xiāng)中。唯一還有丈夫的女人,他們夫婦先是從漠河到深圳打工攢了點錢,后來因女兒在北京發(fā)展,就來北京了。其他幾個老鄉(xiāng)要么離異,要么跟她一樣丈夫已經(jīng)不在了。阿春真好,有丈夫有女兒,還沒有女婿,他們一家人看上去很幸福。
2
車子一路朝著城外開。正是草長鶯飛的季節(jié),道路兩邊的柳樹槐樹發(fā)了新芽,在太陽光下閃亮,天空湛藍高遠。過了十字路口,汽車拐進另一條道路,暗紅色的墻體順著道路延伸,斑駁的樹影在墻面上移動,來往的車輛比先前少了,她也比之前平靜了許多。
她開始想,阿春是不是看見精神病院的車了?阿春有沒有看到她坐在車上?如果看見了,阿春會不會像之前說的那樣,約上老姐兒們?nèi)ゾ人克o阿春說過不要將她跟女兒的事說給她們聽,她們不會理解的,這事反而會成為那些人的談資。
她退休前跟丈夫一樣都是大學老師,丈夫三年前去世了,她賣了家里的好幾套房子到北京來給女兒帶孩子,在阿春的超市認識了她們。她們中有兩個高中老師,另外兩個是初中老師,退休后她們都還保持著讀書的習慣,所以她們常常約著讀同一本書,然后一起在阿春的超市互相分享。每次讀書會,阿春總是最后一個拿著書走向她們的人,她會取下頭上的帽子和身上的圍腰,笑嘻嘻地坐在專門留出來的座位上。她們的聚會,她總是背對著窗玻璃坐在燈下。
這會兒她朝車窗外看,想著那個空出來的座位。她們照常坐在那兒,會不會討論救護車的事?阿春會不會去她的樓下找她?阿春看見她們家沒有開燈,就會知道她之前說的事情終于發(fā)生了。
她在北京沒有去處,女兒也不會帶她去別的什么地方,阿春那兒是她唯一可以去的地方。阿春會不會幫她報警?可是報警有什么用呢?阿春證明不了她是正常的,能去超市買東西,能分享讀書的感受等等,這些都沒有說服力。她忘了是什么時候,她告訴過阿春自己有可能得了阿爾茲海默癥,理由就是她老忘東西。而實際上她已經(jīng)確診了,她只是不能說出來。
她在冰箱的門上寫下所有該記下來的電話號碼,以及日用品和蔬菜的名稱,就是擔心有一天失憶了,還能通過記錄的文字想起什么來。很多次,她也想將自己的病癥告訴女兒,可是女兒根本就不會聽她說半句話,而且就算她說了,女兒也只會說她是無病呻吟,德道綁架。
車身在減速帶上起伏騰躍了一下,道路上的海棠花開得粉粉的。海棠花在她來北京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被她誤認成了蘋果花。現(xiàn)在偶爾出現(xiàn)在眼前的海棠花明麗地閃耀著,落在花上的陽光細細碎碎如銀如芒,讓她睜不開眼,讓她感覺到一種悠遠的茫然無措。
她側(cè)著頭,可以通過車窗玻璃的反光看到女兒,女兒一直埋著頭在發(fā)信息。她看見女兒面色暗黃,幾根白頭發(fā)從淡淡的棕色中冒了出來。打了電話還不夠,還要一路向他匯報動態(tài)。想到這兒,她的心由痛滋生出恨,那種刻骨的,對女婿的深深恨意一直在蔓延,像毒素一樣染著色,讓她深陷其中。
女兒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被那個男人控制的呢?好好的一個女兒,自從結(jié)婚以后,不,應(yīng)該是從認識這個游手好閑的人開始,他就像一條毒蛇一樣蟄伏在女兒的身體里,慢慢變成血液流遍女兒的全身。女兒的每一次情緒失控,就像他噴出來的毒液,暗黑、洶涌,令人窒息。
命運就這樣安排他們在女兒外出旅游時認識了,后來女兒還專程去了他的城市看他。很快女兒就告訴她,他們有了結(jié)婚的想法。不同意又能怎樣呢?女兒對他深信不疑。她跟丈夫兩個人的反對不僅僅是因為他沒有正當?shù)穆殬I(yè),還有一個細節(jié)就是,他第一次來家里,家里養(yǎng)的貓對他透露出了巨大的敵意,刺啦刺啦地叫,充滿著莫名奇妙的攻擊性。人說萬物有靈,貓咪肯定先于他們有了什么不好的預感,甚至可能看到了他們看不到的東西。
女兒很快跟女婿結(jié)了婚,兩個家庭沒有見過面,也沒有舉辦婚禮,更別說彩禮了。結(jié)婚是兩個人的事,她縱然有千百個理由說不能嫁給這樣的人,又能有什么辦法呢?這大概是一個人的命運,好端端一個閨女,只能眼看著一天天地滑入深淵。
她第一次發(fā)現(xiàn)女兒的變化,是女兒懷第一個孩子小產(chǎn)時,那時她跟丈夫都還沒有退休。那天她剛下課去到超市,手里拎著東西,女兒的電話來了,哭得很傷心。她問女兒怎么了,女兒說:“他說他不要我了。”她從超市走出來站在一棵樹下,將手里的東西放到地上,靜靜地聽著女兒嚶嚶的哭聲。
她在女兒哭泣的間隙里問女兒為什么,女兒說:“他說我把孩子弄丟了,我是個罪人。”她感到內(nèi)臟被利器扎入,深痛之后是血流,如果能代替,她一定會去代替女兒經(jīng)受這一切。
她輕聲細語地說:“小蔓,他這樣責備你是不對的。他去哪了?我打電話叫他回來。”
女兒哭得更厲害了:“媽,你不要去指責他,不要打電話。他不會聽你的,你又沒有生養(yǎng)他,他只會瞧不起你,更瞧不起我,瞧不起我們一家。”
她沒有聽女兒的,還是給女婿打了電話。他把電話按掉了。她又打,還是被按斷。她急得團團轉(zhuǎn),整個人火燒火燎,試圖再給女兒打電話安慰一下。女兒小產(chǎn)需要安慰,女婿那樣對女兒真讓人心痛,他住著女兒的房子,用著女兒的工資,當然他自己也有錢,據(jù)說還不少,可是在北京是靠著女兒工作掙錢養(yǎng)家啊。他也不工作,整天游手好閑,自己的錢一分不肯拿出來。她向丈夫報怨過,而丈夫卻鐵青著臉一言不發(fā)。那之后,女兒便不接她打過去的電話了,偶爾給她打電話,大概也是在他不在身邊的時候。女兒總是很自責,覺得自己什么都沒有做好,并且斷斷續(xù)續(xù)地開始自我責備,說自己有精神疾病。
那個時候的她,無法想象“魔”這個詞的重量,卻能感受到女兒身上的陽光氣息在漸漸喪失——女兒變得越來越弱,越來越膽怯,像一只驚弓之鳥,時時在不安中準備逃離,即便是隔著電話,她也能感覺到女兒的顫抖。她說她要來北京陪陪女兒,女兒立馬驚慌失措地拒絕了,然后便掛斷電話,很長的一段時間都不聯(lián)系她。
那個曾經(jīng)特立獨行的女兒,仿佛在一團陰影的后面蛻變成了一條軟體小蟲。陰濕和冰冷,仿佛讓女兒氣若游絲,給她打電話時,往往吐出來的都是充斥著綠色液體的有毒氣泡,她氣得咬牙切齒恨鐵不成鋼。
那又能有什么辦法呢?畢竟人生是女兒的。但她沒想到,這種現(xiàn)象在女兒生了兒子之后更是變本加厲。女兒打電話時顯得戰(zhàn)戰(zhàn)兢兢,說的都是自己這不是那不是。她問他們是不是還像過去那樣經(jīng)常吵架,女兒也總是支支吾吾,然后就是自責,還主觀地判定自己得的是產(chǎn)后抑郁。
“他就是這么給我說的,說我的情況和網(wǎng)上說的產(chǎn)后抑郁的狀況一模一樣,又給我看了好多資料。不過他說了,這會隨著孩子的生長而自然消減。我也去看過醫(yī)生了。”
她問:“那么醫(yī)生也說是抑郁癥嗎?”
女兒說是心理醫(yī)生說的。她告訴女兒不要聽心理醫(yī)生的話,是人就會有情緒,到了心理醫(yī)生那兒就成抑郁癥了。哪里有這么夸張?只是心情不好罷了,沒有她想象的那么嚴重。
女兒還問過她,家族里有沒有精神病一類的病史。她以為只是母女間的簡單交流,努力回憶自己父母這一支,從祖輩一直延續(xù)下來都沒有。
女兒說:“你確定沒有?”
她說:“當然啦,如果有,你姥姥會說的。”
女兒又問:“那爸爸家呢?”
她想了一下,才慢慢說:“你爺爺?shù)故窃?jīng)被人打出問題了,其實也不是精神病,反正就是打得不正常了。
女兒問:“所以爺爺?shù)降资遣皇蔷癫。俊?/p>
她說:“應(yīng)該不是。”
女兒回她:“你在有意隱瞞。”
就這樣,她們的對話就停止了。再后來這個話題就變成一個不需要討論的事實。
她說:“你爺爺只是那一陣子有點不正常而已。
女兒并不接她的話,喃喃地說:“他說了,我們家有精神病史,所以才會在我身上發(fā)生,還有我爸爸,還有你。我們?nèi)叶际恰!?/p>
她被女兒的話說懵了,以為女兒只是在開玩笑。
可是女兒卻說:“世間沒有所謂的玩笑,你說的這些一點也不好笑。”
后來當女兒有意地說到這個話題的時候,她立刻就把話題岔開,轉(zhuǎn)而問起女婿的家庭情況。在女兒那里她從來沒有真實地聽到過關(guān)于女婿家的任何情況,就連他有兄弟幾個都不知道。
除了見過面,其他都一無所知。對一個自己一無所知的人是自己的女婿這件事情,她跟丈夫都是忐忑的。出于對女兒的信任以及無奈,他們小心翼翼地聽著女兒說出的每一個細節(jié),試圖從中獲取關(guān)于女婿身份的一切蛛絲馬跡。他們發(fā)現(xiàn)女兒說話變得越來越縝密,說到女婿時總是輕描淡寫,這甚至讓他們覺得女婿的存在只是一個猜想。
她給女兒表達了,女婿跟他們沒有任何交流,甚至連面都不見,感覺生冷而又怪怪的。女兒冷冷地回:“你們想怎樣?他是跟我過,又不是和你們過。而且他說了,一個獨立的人應(yīng)該要勇敢地和家里斷親,就是要和你們獨立開來的意思,擺脫你們對我的控制。有任何問題嗎?”
她說:“有問題,我生養(yǎng)了個女兒,當然希望有個實實在在的女婿。而且我們是關(guān)心你,到他那里怎么變成了控制?”
女兒掛斷了電話,退出了家庭群聊,把他們都拉黑了,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和家里任何人聯(lián)系。
3
手機響了,費玉清唱的《千里之外》的鈴聲是她自己設(shè)置的。自從丈夫走了以后,她就很喜歡聽這首歌,甚至有點醉生夢死般地迷戀。
這會兒是阿春給她打電話,可是手機在女兒手里,她看見女兒舉起來看了一眼,然后在屏幕上一滑,關(guān)掉了手機。她意識到,世界從此以后之,于她而言,就不再會有聲音了。
她坐在病床上一言不發(fā)。窗外的樹木蔥郁有致,女兒拿著手機站在窗邊,也在朝外面那片樹林看,樹林里的桃花梨花開得燦爛。
陽光落在女兒的臉上,她叫了女兒一聲,女兒像是沒有聽見,鳥從窗前飛過的影子,從女兒臉上滑過。女兒一直在影子里面,她的心又痛起來,一根針長久地扎在心里,細碎的痛一點一點淤積,讓她陷入一種生不如死的絕望之中。真正該住院治療的是女兒。可憐的女兒,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女兒受折磨,她救不了女兒,也幫不了女兒。
辦入院手續(xù)時,女兒對醫(yī)生說母親經(jīng)常對自己施暴,把家里的東西砸碎了不少。這些實際上都是女兒的行為,女兒卻那么輕而易舉地就推到了她的身上,這樣顛倒事實,混淆黑白,有時候也讓她產(chǎn)生混亂感,仿佛那一切真的都是自己干的,而不是女兒。
就像女兒開始明明是正常的,夫妻倆吵一下架而已,天下的夫妻哪有不吵架的?吵完了女婿說是女兒精神有問題,有家族遺傳病史,把吵架的責任全部推在女兒身上,讓女兒自己去反思自己過去的生活是不是不正常。
護士進來給她量血壓測體溫,女兒從包里拿出一雙她的拖鞋,給她換上。護士將藥送到她跟前,她想假裝吞下,但護士讓她抬起舌頭,藏在舌下的藥就露了出來。
這時候的她,已經(jīng)意識到反抗和解釋都沒有用了。她從救護車上下來時還掙脫了他們的控制,然后開跑,她一跑就更進一步證明她病情的嚴重性,幾個人三下五除二逮住她,將她按住,她哭了。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哭,千言萬語涌進心頭——如果丈夫還活著,女兒會不會將他們一起送進精神病院?如果丈夫還活著,起碼兩個人還有得商量,黑龍江的房子就不會全部賣掉,再不濟他們還可以回黑龍江去。
她恨自己沒有聽丈夫的話,將最后一套房子也賣掉了。丈夫在的時候,他們就賣掉了三套房,為了全力支持女兒一家,來北京給他們帶孩子。后來丈夫病了,她又回到黑龍江,再后來丈夫去世了,女兒就叫她把老家房子賣了,回北京繼續(xù)帶孩子。
她也沒有想太多,女兒每天要上班,孩子小,需要人照顧。女婿還是那樣游手好閑,基本上不回來,不是在打牌就是跟一群狐朋狗友在外面喝酒玩樂。女婿說要避免和她同在一個屋檐下,不然兩輩人住在一起容易出矛盾,所以他就跟女兒住在另一處房子里,她也見不到他。只是偶爾他跟女兒一起過來接孩子,她通過窗子看到他穿著花紋襯衫戴著墨鏡,在樓下的院子里走來走去東看西看,像是有什么事急著要去辦。
很快女兒就給她買了套四十年產(chǎn)權(quán)的公寓,房產(chǎn)證上寫的是女兒的名字,之前賣房的錢女兒用來買了兩套房,女兒女婿住一套,她帶著外孫住一套,女兒多數(shù)時間跟她們住在一起。偶爾女婿會跟女兒一起過來接孩子,但從不上樓,她只是通過窗子看到他。這些她都沒覺得有什么問題。
隨著外孫慢慢長大,他們需要她的時間不像從前那樣多了,女兒就說要把另外那套房子租出去,或者賣掉,叫她先搬到公寓去住。搬進這套三十平米的公寓后,她給阿春抱怨說沒有地方可以坐下來看書,就一間屋子,以前的書都賣了,不然在家里放那么多書的話還擋著路。家里的洗手間也小得只能側(cè)著身體進出,廚房衛(wèi)生間擠在一塊兒,活動空間就是臥室,她努力適應(yīng),努力活著,也慢慢習慣了坐在床上看書。好在公寓離女兒住的地方不算太遠,地鐵五站就到了。
有時候她也會坐地鐵過來找阿春,在超市人少的時候坐上那么一會兒和阿春聊聊天,畢竟在北京她沒有其他可以交往和信任的朋友。她會透過超市的落地玻璃看到女兒和外孫,她們一前一后地走在路上,放學的孩子和家長也都跟他們一樣,媽媽背著書包,孩子就在前面邊玩邊跑。
外孫是她一手帶大的,每次這樣看著他們,她都會黯然流淚。阿春抬著東西站在離她不遠的地方,戴著帽子和圍腰看她,朝她笑笑說:“你一會兒吃了晚飯再回去。”阿春將上次從她那兒借來的書還給她,手在圍腰上下意識地擦了一下,并不去看她淚眼婆娑的樣子,接著說:“今天又帶新的書來了嗎?”
她急忙轉(zhuǎn)身從座位上的布袋里取出一本書遞給阿春。她看著兩鬢已經(jīng)斑白的阿春,心想這不符合阿春的年齡,阿春才五十二歲,在店里從來沒有閑著她朝柜臺那兒看去,阿春的丈夫永遠坐在那兒一言不發(fā)地看手機。無論如何她都羨慕阿春,有丈夫有女兒有家,阿春擁有整個世界,再苦也是值得的,因而阿春整天埋頭勞作,輕言細語的樣子在她眼里都是那樣充盈。
老鄉(xiāng)們聚在阿春的店里讀書,她給她們講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她說到人生是一場博弈時,聲音很小,生怕她們聽見了,就完全明白了她的處境,而不是她從《老人與海》里讀到了“博弈”這個詞。她能看見燈光下她的側(cè)影映在店面的玻璃上,她清瘦蒼老,灰白的頭發(fā)上閃爍著光影,人像是落在光與光的漩渦里上下浮游。
后來女兒又要求她回去,但晚飯后還得回她的公寓。她來來往往地兩邊跑,有時候也在女兒家住上一晚,任務(wù)是接送孩上學放學以及做飯。她將每天要買的菜,要做的事,寫成小紙條貼在冰箱上。這些紙條被女兒一次次扯下來,女兒絲毫沒有朝她也許會患上什么病這方面去想,而是告訴她:“你不要裝瘋作邪好不好?你這種行為實際上是一種精神控制,你無外乎就是想給我增加壓力而已。”
女兒將扯下來的紙片扔垃圾桶時,還會狠狠地踢一下垃圾桶:“我工作已經(jīng)很辛苦了,你不要再在我家作妖,你再這么作,我就把你趕出去。”
她聽到女兒的話,站在那里一動不動。她的心咚咚地跳不停,有時候,她為自己變得如此卑微而難過。
女兒將家里可以用來寫字的紙都收了起來,并且連一支筆都不留給她。也許女兒已經(jīng)忘了她是大學老師,做家務(wù)帶小孩從來就不是她的強項,何況她發(fā)現(xiàn)自己的記憶力以驚人的速度在下降,前幾天她竟然忘記了該坐幾路車回家,明明要坐的是847路,不知怎么上的卻是419路。
那一天會來的。她常常這樣想,感覺到日子一天天地在吞噬她。
他們又吵架了。女兒坐在陽臺上,用抽紙擦眼淚,她靜靜地聽著女兒的自責。她早已習慣了不言語,女兒找她哭訴,并不是想從她那兒得到什么指教或者平衡,女兒只是想哭哭而已,結(jié)論女兒早就給自己下了:“他說了我精神有問題,我們家有精神病史,這個是基因病,改不了的,他說了這還會遺傳給我們家小孩。”
曾經(jīng)的她試圖告訴女兒不是這樣的,他在精神控制女兒,可是卻遭到了女兒歇斯底里的制止,控訴式的責備。
她也曾想過放下女兒回黑龍江去,不管怎樣,就算是租房子,那也是自己的家。但怎么樣她也沒辦法把女兒一個人扔在這里,丈夫走了,全世界女兒就只剩下她一個親人可以依靠了,沒有了媽媽,她還有誰?她想過找女婿談一下,可是女兒不會答應(yīng),他連面都不見一個。
女兒說:“你知道為什么他不愿意見你嗎?就因為那一次我小產(chǎn),你不停地給他打電話,讓他特別沒面子,從那以后,他就沒有原諒過我們,尤其是你。”
她說:“我不是沒有打通嗎?”
“沒打通你也打了。你知不知道這是非常沒有禮貌的行為?我早就給你說過他不能接受我把兩個人的事情往外說。他說我動不動就把我和他的事告訴別人,這全是家丑啊,家丑你知不知道。”
她想不清楚親人之間的關(guān)心,怎么到了女婿那兒就變成了失禮,變成了不能接受。女兒先是認為自己有精神病,慢慢地便覺得她也有精神病,并在每一次歇斯底里的狀態(tài)中反復說她有精神病,還曾在沖突中報了警。
那一次她真的不知道女兒的病嚴重到了如此程度。女兒在她的公寓里,將她的書一本一本扔到地上,還撕了書的封面,又拿起桌上的花瓶,把水倒到書上。她給了女兒一個耳光,女兒跟她撕扯,然后報了警。
警察上門調(diào)解,做筆錄,臨走時警察站在電梯口不無同情地對她說:“老人家,你還是好好過你的晚年吧,千萬不要為兒女做牛做馬。”
她記得警察是拿著盾牌和警棍沖進家來的。她與女兒隔著一張床的距離,她聽到女兒在電話里呼救,說有人要殺死自己。警察在她僅有三十平米的屋子里烏泱泱地站著,讓她拿出身份證,她還得側(cè)著身子從他們身邊過去,他們穿著警服,像黑色的樹木那樣,讓她感到窒息和尊嚴掃地。
她無數(shù)次想過離開女兒,甚至還想過殺了那個控制女兒的魔鬼。然而她卻什么也不能做——如果她離開了,女兒會是什么樣子?看著女兒一天天被害而不自知,她心如刀割。那是病啊,比什么病都可怕的精神迫害。丈夫說得對,那個人就是附在女兒身上的魔鬼,一點點侵蝕女兒的身體,最終把女兒的生命耗盡。
4
第二年的秋天很快就來了。
她坐在窗前面對著那片樹林,成群的鳥在林子里盤旋,整個夏天耳朵里都是蟬的叫聲,讓她漸漸忘掉了樹上那窩幼鳥吃食的情形。
春天的花閃閃發(fā)亮,大鳥們飛來飛去。光著身子的幼鳥張著嘴巴,她數(shù)了數(shù)一共五只,乳紅色的皮膚透光放亮,脖子伸出窩來,五張小嘴一齊朝天打開,叫聲像飛蟲那樣細小孱弱。
鳥媽媽們忙忙碌碌地將蟲子送進幼鳥們的嘴里,整個春天和夏天,她每天都在看著它們,融入它們,甚至忘了這是座精神病院。身邊的病友蓬頭垢面,嚎叫的聲音遮住了鳥的聲音,遮住了陽光下的那些花兒。
她不知道什么時候就忘掉了說話,在這里也不需要說話。她認得每一只鳥飛行的路線,聽得懂它們的喜怒哀樂,記得它們飛走以及回歸的時間,甚至知道每一片樹葉上陽光停留的時間,花草上鳥蟲飛過的影子的方位,密密麻麻的杜鵑花開了幾朵凋落了幾朵,以及每一只螞蟻停頓和爬行的路徑。
園丁在雨天里穿著雨衣修枝,剪掉一些開得正艷的花,草坪修剪時園丁手里的割草機似乎總是出故障,使得他必須不停地走到機子邊蹲下身修整。風一陣陣送來青草的氣味,她融進那氣味里,病友過來叫她,她像沒有聽見,她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那片樹林里。
每天下午兩點是集中看電視的時間,進門時她被一個年輕的女人撞了一下,她記得幾個星期前,在過道上她就撞見過這個女人。她不知道小蔓最終也被那個魔鬼送到了精神病院,她失憶前想過他一定會這么做的。可是現(xiàn)在的她,已經(jīng)沒有那樣的判斷力了。
小蔓的臉幾乎完全被頭發(fā)遮住了,當她們相撞的那一瞬,她的身體像通了電,腦子里閃出女兒“小蔓”的名字。然而當她認真地站定后,腦子里映現(xiàn)的依然是陽光下燦爛的樹林和飛鳥。她看著小蔓從身邊走過去,然后小蔓回頭朝她看了一眼,空洞的眼眸突然閃了一下。她還看到小蔓笑了,露出雪白的小米牙。小蔓——她的腦子里閃出這個名字時瞬間清醒了那么一秒,但很快她又沉入昏暗的狀態(tài)。
每次從電視房出來,她總是走在最后面,總是找不到房間。過道里有人放了張藍色的塑料凳子,回來時凳子被人拿走了。她繞著走道往前,走到樓梯口的鐵門處,她站在那兒試圖打開繞在門上的鐵鏈。鐵門上的鎖已經(jīng)生銹了,她用手觸上去,又放在鼻子下面聞聞,然后她沮喪地靠在門上。護士過了很久才過來找她,將她領(lǐng)回四人間的開放式病房。
第二天上午十一點吃飯,去飯廳時她又跟小蔓擦肩而過,小蔓停下來轉(zhuǎn)回身,幽怨空洞的眼睛里又閃出光來。
她喊了一聲,“小蔓。”
這一次小蔓沒有笑,反而問她:“你怎么知道小蔓?小蔓是一條狗的名字,不是我的名字。小蔓早就已經(jīng)死了。死很久了。”
她看小蔓一眼說:“小蔓不是狗,是我的女兒。”
小蔓朝四處看了一眼,壓低聲音說:“別讓人聽見,他們要是知道我叫小蔓,會打死我的。”
她往前走,小蔓跟上來,兩個人一前一后進了飯廳,她坐下來,小蔓也在她身邊坐了下來。她們坐在一起開始吃飯,醫(yī)院護理分發(fā)蛋羹時,小蔓站起來想多拿一個,護士不讓拿。小蔓直愣愣地看著護士,眼淚掉了下來。她將自己的那份推到小蔓跟前,小蔓接過來吃了一口,又遞還給她,示意她也吃。她又將蛋羹推過去,小蔓似乎朝她笑了一下。她問小蔓:“你是我的女兒嗎?”
小蔓被問住了,眼睛空洞地看著朝她們走過來的護士。護士不讓她們說話,在她們周圍走了一轉(zhuǎn)。護士背對著她們時,她又將碗里的花卷放進小蔓的碗里。她們一起朝護士那兒看,兩個護士正在談?wù)撍齻兡_上的鞋子。
看著小蔓狼吞虎咽地將那些難吃的東西吃完,她又問小蔓:“你是我的女兒嗎?”
小蔓嘴里含著東西,眼神變得空洞。她遞過紙巾,摸摸小蔓的臉說:“吃慢一點兒。”小蔓點點頭,放慢了進食的速度。
吃完飯,等待看電視的空隙,醫(yī)生和護士守在門口,病人們慢慢吞吞地放下碗筷。小蔓朝她靠過來,靠在她的肩膀上,她輕輕地摸著小蔓的頭說:“你是我的女兒嗎?”小蔓轉(zhuǎn)過臉來對她說:“小蔓死了,他們說的。”
她們一起看電視,小蔓在她肩膀上睡著了,她感到小蔓的身體在抽搐,嘴里含含糊糊地喊著:“媽媽,媽媽……”她抱緊小蔓說:“媽媽在這兒呢,睡吧,不怕。”
電視的聲音,蓋住了她的聲音。
5
這天中午吃過飯,坐在電視房里的她正在給小蔓梳著頭,一個護士走過來蹲在她身邊說,有人來看你了。她說:“是我女兒來看我了?”
護士看著她給小蔓編好頭發(fā),然后將她領(lǐng)到探視室。阿春坐在那兒。阿春給她買了一束鮮花,一些水果和牛奶。看著她跟在護士身后進來,阿春一時竟沒有認出她來,直到她在對面坐下來。
她是一個身材苗條皮膚白凈的女人,之前挺直的背脊這會兒有些微彎,嘴唇毫無血色,花白的頭發(fā)剪到耳朵上面去了,露出了阿春她們從來沒見過的精致的小耳朵,耳垂下隱約能看見之前打的耳洞,鼻子上架著的眼鏡已不是阿春認識的那副了,是入院時女兒早就準備好的樹脂眼鏡。她的手還是那么纖細,只是這會兒看上去已經(jīng)枯萎了一樣。她目光淡漠地坐下來,阿春認出了她,就想上前抱住她,然而她卻抬起手拒絕了阿春的善意。
阿春對她說:“我是阿春啊,你不認識我了?”阿春哭了起來。
她問:“你是小蔓?”
阿春哭得更厲害了:“你閨女半年前也被她老公送到這里來了。”
她不說話,眼睛直直地看著阿春。然后她將手放在桌子上,阿春抓住她的手,這一次她沒有拒絕。
阿春說:“那天我們不是站在超市外面嗎?又看到了精神病院的車開到你們家樓下,我們跑過去就看到小蔓被拖上了車,幸好我記下了車身上醫(yī)院的名字。”
阿春已經(jīng)哭成了淚人兒:“你怎么成了這樣子?你見到小蔓沒有?天啦,天啦,你怎么成這樣了?”阿春哭出聲來。不遠處坐著的醫(yī)護人員提醒阿春要控制情緒,不要刺激病人。
阿春止住哭說:“她老公為什么要這么做?你們的財產(chǎn)全都被他一個人占去了,你要想辦法早點離開這兒,不然就來不及了。”阿春又加了一句,“不然真的來不及了。”
她抽回手,往身上擦了一下阿春掉在她手上的眼淚。她說,“你是我女兒嗎?”
泣不成聲的阿春停下來看著她。阿春想要站起來去給醫(yī)生講,她得的是阿爾茲海默癥,不是精神病,她是被女婿加害進來的,還有她的女兒。可是阿爾茲海默癥跟精神病,又怎么區(qū)分呢?
她擦了擦臉上的眼淚說:“姐姐,你叫小蔓給我打個電話吧,我見到她爸爸了,我要回沈陽去了,帶不了她的孩子了。你給她講一下這個情況,讓她理解一下我的處境,好不好?”
阿春握緊她的手,邊哭邊點頭。
她說:“我不忍心離開北京,就是擔心我走了,女兒就得一個人承受那個魔鬼的折磨。現(xiàn)在小蔓的爸爸叫我回去,我不得不回去,他來了每天就在樓下等我。所以我還是回去好了。”
她站起來像是又突然想起了什么,兩只手驚恐不安地上下抓著衣兜尋找著鑰匙:“哎呀壞了,我要去接孩子去了,孩子走丟了怎么了得?”
她朝門的方向走,阿春拉住她。她掙脫了阿春,紅了臉呵斥阿春走開,她又哭又鬧一定要走出去。
醫(yī)護人員開門進來,往她手腕上注射安定,然后當著阿春的面將她綁在了床上,把她連床一起推了出去。
6
又是一年冬天。
外面下雪了,漫天的大雪遮住了樹林和鳥。她使勁推開窗戶,雪花隨風飄進屋來。
有人走過去拉上窗子,外面的聲音被隔斷了。她趴在那兒看雪花簌簌地飄下來,天和地渾然一體,鳥在雪地里飛行的速度依然很快,它們的叫聲淹沒在雪花飄落的聲音里,細小透亮的雪花飄啊飄。
小蔓過來了,走到她身邊依偎著她。
她跟小蔓現(xiàn)在住在了同一個開放式病房,在醫(yī)生的精心治療下,小蔓的病情穩(wěn)定。小蔓的神志還沒有完全恢復正常,跟她住在一個病房后,變得安靜順從,醫(yī)生送來的藥都乖乖地吃,打針也不反抗,起床吃飯午休只要跟在她身邊,就很聽話。她坐在哪兒,小蔓就坐在哪兒。
她回頭問小蔓:“你是我的女兒嗎?”
小蔓笑了,將頭鉆進她的懷里。她從兜里摸出一個午飯時偷藏的花卷,小蔓接過去大口吃起來,邊吃邊看她,間或朝她笑一下。
等小蔓吃完,她又給小蔓梳頭,輕輕地用手指梳,將打結(jié)的頭發(fā)理順,挑起小蔓頭上的白頭發(fā)一根根拔掉。
“孩子啊,你那么年輕,怎么長了這么多的白頭發(fā)呢?你到底受了多少折磨啊。”她說。小蔓抬起手抓住她的手,反身要給她梳頭。她們倆調(diào)轉(zhuǎn)了坐的方向,她靠在小蔓腿上,任憑小蔓用手指給她梳著頭。
過道上傳來發(fā)零食的聲音,她們依然坐在那兒。因為沒有人給她們送東西,所以護士走過門口時,只是轉(zhuǎn)頭看了她們一眼。
梳完頭,她們又調(diào)回先前坐的樣子。小蔓趴在她的腿上,她輕輕地唱小時候小蔓在幼兒園學的兒歌:“兩個小娃娃啊,正在打電話啊——喂!喂!喂!你在哪兒呀?哎哎哎,我在幼兒園。喂!喂!喂!你在做什么?哎哎哎,我在學唱歌……”
小蔓也想起了這支歌,這是小時候媽媽每次將她從幼兒園接回家的路上,兩個人一起唱過的歌。小蔓慢慢坐直身體,她看著窗外飛揚的大雪,腦子里閃過一道一道的亮光,小蔓想起來了,這支歌自己也會唱,正要開口唱,歌聲停了。
小蔓抬起頭來,看見她的手僵直地垂下來,雙目微閉。小蔓抱住她喊:“媽媽,媽媽。”她睜開眼睛看了小蔓一眼,臉上的肌肉抽動了一下,兩行清淚順著眼角流下來。
雪花從窗外飄了進來,小蔓伏在她漸漸僵硬的身體上,緊緊地抱著她的脖子,把臉貼到她的臉上繼續(xù)喊著:“媽媽,媽媽,我們回家吧。”然后小蔓側(cè)轉(zhuǎn)身用臉貼緊媽媽的手臂——冰冷僵直的手臂,小蔓像小時候那樣往上面吹氣,反復揉搓,暖乎乎的氣流回到了她的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