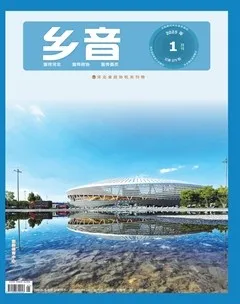古人從“頭”開始的故事


【文物名片】
雙鳳紋黃玉梳、螭紋青玉梳,河北平山縣戰國中山王厝墓出土,現在河北博物院《戰國雄風——古中山國》陳列展出。兩枚玉梳造型別致,工藝精湛,寓意吉祥,顯示出戰國中山玉雕藝術的成熟以及不同于中原諸國的文化藝術特色,講述著古人從“頭”開始的故事。
戰國時期,諸侯稱霸,列國爭雄。但是,分裂的格局并沒有阻擋各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與交流。這一時期,玉文化得到蓬勃發展,玉器的制作和使用越來越廣泛,器物造型和紋飾更加豐富多彩。在那個“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的時代,玉器的用途被系統化和理想化,玉器的禮制化也臻于完善。許多大思想家將玉器融入社會品德生活當中,儒家創始人孔子就將“比德于玉”的思想作了全面闡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由此化無形為有形,確立了玉器的人格化。有人說,戰國玉器的紋飾也許沒有唐代的生動、宋元的精巧,但那來自數千年前的渾厚和闊朗,以及它們身上回蕩著的先哲思想之音,足以讓人為之動容心醉。
20世紀70年代,河北平山縣上三汲鄉戰國中山王厝墓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僅玉器就千余件。這批玉器文化內涵豐厚,且品類繁多,造型優美,工藝精細,以出神入化的造型設計、變化多樣的構圖裝飾呈現出非同尋常的韻味和效果。中山玉器,稱得上戰國玉器中的一朵奇葩。
戰國中山國是白狄族所建的少數民族諸侯國,中山玉器反映了中山國人的崇尚和習俗,花紋及構圖方式與華夏玉器的傳統雕琢手法迥然不同,充滿了濃郁的地方色彩。關于這一點,河北平山縣戰國中山王厝墓出土的兩枚玉梳體現得尤為鮮明。這兩枚玉梳均采用透雕手法。一枚為雙鳳紋黃玉梳,質地半透明。梳柄為半橢圓形,下有10根梳齒,梳柄正中透雕兩只相對站立的鳳鳥,雙鳳長頸相連,曲體回首,身姿柔美。體表用陰線雕琢出羽毛紋,清晰而生動。玉梳上弧邊陰刻勾云紋,下橫邊雕琢細密的斜格紋;另一枚為螭紋青玉梳,質地灰綠色,玉質瑩潤。梳柄中部透雕獨首雙身的螭龍,螭龍身體蜷曲,上下雕飾有卷云紋,似蛟龍在云中翻騰,5根寬齒上雕刻有豎陰線,背部留有起草紋樣的線圖,但尚未雕琢紋飾。
我國使用梳子的歷史久遠。相傳,梳子最早出現于華夏上古時代,發明人是軒轅黃帝的一個妻室,名叫方雷氏,她是開創了華夏族鳳凰圖騰的黃帝長子“玄囂”的母親。方雷氏掌管著黃帝身邊20多位女子,她們經常是一副蓬頭亂發的模樣。每逢祭拜、締約、結盟、出征、凱旋、慶祝等部落聯盟舉行重大節慶的時候,方雷氏為了讓這些女子體面地參加盛大典禮,就把她們召集在一起,親自用手指逐個將她們的蓬發捋順,每次都弄得筋疲力盡,有時甚至都會捋破手指。有一次,黃帝手下一個叫狄貨的人打了幾條大魚,方雷氏幫他把魚做熟。鮮魚十分美味,魚肉很快被人們一搶而光。方雷氏看到剩下的一堆魚刺,忽然得到啟發。她嘗試著用大魚刺打理頭發,果然十分得心應手,大大緩解了手指的操勞。對于方雷氏的這一“發明”,黃帝深表贊許,命人用木頭做成魚骨的模樣。雖然最開始做出來的木頭魚骨,就像耕地用的耙子,但在方雷氏指點下多次改良,適合梳頭發的木頭魚骨終于問世,方雷氏將其命名為“梳子”。
對于梳發,古人非常重視。晉代傅咸的《櫛賦》有云:“我喜茲櫛,惡亂好理。一發不順,實以為恥。”《禮記》專門規定:每人每天必須梳理頭發,3天必須洗頭、沐浴一次。如此這般,梳子就顯得極其重要。可以說,梳子是人手必備,甚至隨身而帶之物,男子放于巾帽之下,女子則插于發上。甚至,古人還將用梳篦梳頭視為一種養生手段。南北朝時著名醫學家陶弘景認為:“頭當梳櫛,血流不滯,發根常豎。”明代學者謝肇浙《五雜俎》卷十二也有“梳為木齒丹,每日清晨梳千下,則固發去風,容顏悅澤”之說,由此可見古人對于梳子養生之功的重視。
其實,梳子在古代不僅是梳理發型的工具,更是婦女們插在頭發上的裝飾品,與簪、髻、釵、珠花、金鈿、步搖等并稱為中國“八大發飾”。戰國中山王厝墓出土的這兩枚玉梳,不但梳齒較長,梳齒的齒端也較為薄扁,插戴功用十分明顯。考古資料顯示,我國女性的插梳之風始于新石器時代。全國各地新石器時代墓葬中出土了形式多樣的梳子,如石梳、木梳、象牙梳、玉梳等。距今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遺址,就有象牙制作的梳子出土。玉梳的出現,是在商代,當時的貴婦階層已開始用玉梳來梳理美麗長發了。從戰國早期開始,梳子的造型發生了根本變化,最顯著的特點為:高度大于寬度,梳齒一般與梳背等高。戰國中山王厝墓出土的這兩枚玉梳,基本符合這一時代特征。但是,戰國時期中原各國出土的梳子,齒數范圍是在15至26之間。與之相較,兩枚中山玉梳,齒數明顯稀少,這種造型獨特的梳子,應與中山國人女子獨特的發式有關。戰國中山王厝墓還出土了十幾枚小玉人,這些小玉人屬于中山國絕無僅有的玉器品種。“她們”無論身體修長還是身材矮胖,都是頭梳牛角形發式,雙手置于腹部,下身穿拖地長裙,裙面圖案都是在間隔對稱的方框內飾以密集的斜格紋裝飾。另外,在平山戰國中山貴族墓地出土的狩獵紋銅豆上,也有類似頭梳牛角形發式的女性形象出現,可見這種獨特的發式在當時中山國的流行程度。
由于齒數稀少,梳背部的透雕紋飾顯得更為突出。兩枚梳子均為雙面雕刻,雙鳳紋黃玉梳的梳背部分,在拱形開光里,紋飾細密而規整,排布飽滿。以鏤空手法雕刻的兩只鳳鳥,背向對稱而立,呈左右對稱的S 形,雙肢作中軸相連。鳳鳥的喙、尾、羽翼等均作不同朝向的卷曲,線條婉轉流暢。
民間有一種說法,梳子是古代男女共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在梳子背上雕龍雕鳳,就是所謂的“龍鳳梳”。陰陽合璧的“龍鳳梳”,蘊含著“龍鳳呈祥”的美好寓意,用以祝福使用者百年好合。巧合的是,戰國中山王厝墓出土的另一枚玉梳,所雕紋飾為龍。只不過,是一種沒有角的龍——螭。戰國中山國出土的玉器中,“螭”的形象很常見。所謂“螭”,是傳說中“龍生九子”之一。螭形玉器在戰國玉器中非常少見,中山國玉器中卻有大量體態各異、造型多樣的螭紋形象的出現,它們或一首雙身,或回首卷體,或雙體纏繞,或寄生附體,這些造型多樣、體態各異的龍螭形象,堪稱戰國中山國獨創。其中,既吸收了華夏文化中龍螭的某些特征,又傾注了中山國人的審美情趣,可謂既靈氣活現又凝重莊嚴。
既有實用價值又有審美情趣的古代發梳,流傳至今的并不是很多。中山王厝墓出土的兩把玉梳,將戰國中山人獨特的審美情趣和民族風尚寄寓其中,帶給后人莫大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