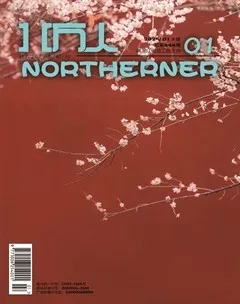寫書也不是多大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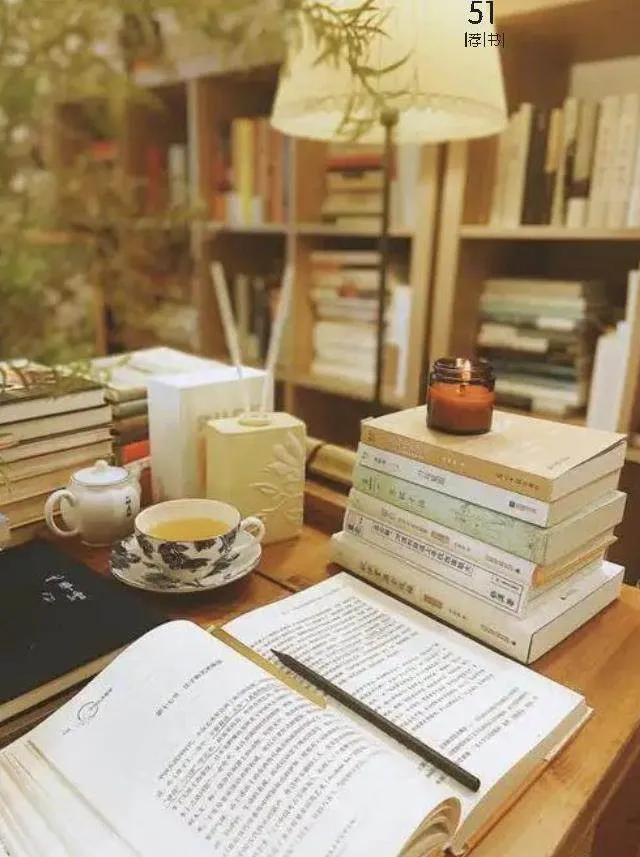
在寬大的書架前翻著一本厚厚的書,是姥姥在我們家常有的畫面。起初你想笑,一個不認字的老太太,手捧一本滿是字的書看什么?慢慢地你就有些心酸,她一定是渴望知道這書里寫啥了。再后來你就想哭,想到姥姥每次拿起書差不多都會說一句:“唉,睜眼瞎,長個眼好弄么?”不認字又喜歡字的姥姥真是痛苦啊!
“這個世界上不認字的人多了,人家不都過得挺好的?”
“他要是摸著心說實話,沒有一個人敢說他過得好。不認字,多悶得慌。”
悶得慌,姥姥的心悶得慌。
我不忍心讓姥姥悶得慌,常給姥姥念書。張潔寫的那本《母親的廚房》剛上市我就買回家念給姥姥聽,書很薄,幾天就念完了。姥姥說:“寫書也不是個多大的事,你看人家也沒寫個啥,就是過日子那點油鹽醬醋,烙個油餅炒個菜。”
“哈,老太太,就這才不好寫呢!平凡的日子人家寫得你那么愛看,這就是大家。”
又過了一陣子,姥姥拿著張潔寫的另一本書《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說:“你給我念念這本書吧,這上面寫了些啥?”
“呵,老太太,認字啊,這不是那個張潔嗎?”哦,姥姥認識書里的照片,兩本書里都是同一個女人。
這本書被姥姥催得基本上是一口氣讀下來的。今天只要停下,姥姥明天一大早起來就會問:“張潔的媽從醫院回來了嗎?醫生怎么說?”念的過程中,姥姥時不時掏出手絹擦眼睛。
我說:“你這么難受咱今天不念了吧?”
姥姥說:“念吧念吧,我不是難受,我是好受。”姥姥說的“好受”我懂,她從張潔的這本書里享受了真正意義上的親情、母女情。
張潔在書里寫道:一個人在五十四歲的時候成為孤兒,要比在四歲的時候成為孤兒苦多了。姥姥聽了這話又哭了:“你告訴張潔,媽早晚是得走的,媽走了閨女還能活,知足吧。要是閨女走了,當媽的就活不了啦。一輩兒一輩兒的都是這樣。”莫不是姥姥又想起她的小兒子了?她在五十多歲的時候失去了二十多歲的兒子,她不也活過來了嗎?姥姥說:“死了幾回啦,只有自己知道……”
家是什么?家里的人是個什么關系?不就是這么瑣瑣碎碎忙來忙去嗎?你攙我一下,我扶你一把,似乎今天過得和昨天一樣。一樣的日子有人過得有滋有味,有人過得麻木不仁。姥姥這樣評價張潔這本書:“說的都是家家都有的事兒,可是人家說的你就那么愛聽,聽了還想聽。”
我認為這是讀者對寫作者的最高表揚。
聽完了這本書,姥姥對張潔娘倆的牽掛不亞于她們的家人。那年春節,鄉下舅媽送來一筐大鐵鍋蒸的新麥子面開花饅頭,一個就有兩斤重,大個的都像盆子那么大。姥姥非讓我給張潔送兩個。我笑了,我雖然采訪過張潔老師,也認識,但北京不是水門口村啊,說上人家家提溜著兩個饅頭就去敲門,嚇著誰。
姥姥不明白,認識的人怎么還能不來往?“別看這饅頭不值啥錢,可在北京有錢也買不到。”我知道姥姥絕不是因為怕張潔沒了母親吃不上飯,而是覺得自己有個大得不能再大的熱水袋,灌滿了自己的良善,誰需要就拿去暖乎暖乎。熱水袋涼了可以隨時換上熱水,沒有熱水了還可以放在懷里加加溫。熱水袋不值錢,但卻管大用,因為有愛。姥姥覺得在這個世界上,人和人之間應該有一個基本的愛,這種愛鋪設在親情、友情之下,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溫暖,是一種自然的相互幫助、相互給予,是人性里最天然的東西。姥姥說:“這樣你上哪兒去都不用擔心,見了誰也不用害怕,就像在自己家里。”姥姥盼著社會是個大家庭。
姥姥也是在書上認識賈平凹的。我跟姥姥說,政協開會,我們倆在大會堂的座位是挨著的。姥姥覺得我真了不起,凈和一些有能耐的人坐一塊兒。在姥姥眼里,能寫會畫的人都是有能耐的,特別是那些農村出來的文人,姥姥更是高看一眼。姥姥說:“趴在炕上能把字寫周正的人,你不讓他去念書那真是白瞎了。從前農村有個啥?燈也沒有,桌子也沒有,連張寫字的紙都沒有,還能出個寫書的孩子,那不就是個神嗎?”
長大了我才明白,為什么窮的時候,姥姥家一年中吃的最好的飯是學校的教書先生派飯來家的那幾頓。一堆像破布一樣散散的油餅被姥姥用好幾層毛巾蓋著,那香味隔著院墻都能聞到。大鐵鍋旺火炒的茄子絲,蔥花爆炒的白菜心兒,那真是香啊!
姥姥還喜歡一個作家——莫言,說莫言長得和水門口村的人一個樣,人家的孩子怎么那么有出息?我說莫言長得不好看,小眼睛,黑乎乎的。姥姥說沒見哪個大雙眼皮的漢子好看,單眼皮勁道。
姥姥喜歡莫言是因為他實在,姥姥對莫言的書的評價就是這兩個字:實在。
“凈說大實話,說的你聽一遍就記住了。”
苦難、貧窮、饑餓在莫言的書里都寫到了極致,這些文字的記憶都深深地觸動了姥姥。
姥姥感動的是這個和他們村里的人長得一模一樣的作家心里沒忘記這些苦難。苦難生成了一種力量,讓他為一天能吃上三頓餃子而努力學習、出人頭地,當個寫書的人。多么真實,多么不掩飾,多么難能可貴。
理想有時候起步很小、很具體,但最終它有可能變得偉大,有可能從為自己,不自覺地變成為他人、為全人類。姥姥佩服這樣的人。
姥姥說:“人哪,不敢窮;社會啊,不敢亂。社會一亂人就窮了,人一窮社會就更亂了。莫言這孩子去念書就是想吃個好飯、吃個飽飯,這叫個啥?叫志氣!連個想吃好飯的志氣都沒有的人還能干個啥大事?”
不認字的姥姥什么書都愛聽,只要你有工夫給她念。姥姥跟著我認識了不少作家,有些作家的書我都不怎么翻了,姥姥還偶爾提起他們。比如賽珍珠,她的書現在市場上都不大能買到了,但很多年前我基本買齊了。姥姥喜歡她也是因為她寫的事姥姥熟悉。姥姥敬佩人家一個外國女人,對中國的鄉村和村民那么有感情。
姥姥的評價也很準確:“就像那個花,根啊、葉啊都是外國的,可是埋在咱這兒的地上,喝上咱澆的水,吃上咱喂的肥,長著長著就成了咱這兒的花了。你別看開的那些花還是人家原來的那個樣,可是性子啊、魂兒啊慢慢地就和咱一樣了。”后來我又給姥姥讀賽珍珠的傳記,姥姥知道她有一個傻孩子,晚年很不幸。姥姥還慨嘆:“唉,她該抱著孩子回中國找個中醫看看,孩子興許能好!人家幫了咱中國人的忙,咱也該幫幫她呀!”
蕭紅的小說姥姥也愛聽,小說的語言、小說中的故事都是姥姥熟悉的。姥姥對她的評價是:“這個閨女真會寫,寫的那些話和北極村的那姑娘一樣,干脆利索,一聽你就再也忘不掉了。”
哦,姥姥說的北極村的姑娘是指遲子建。我還不認識遲子建的時候就給姥姥讀過她的書,也是揀一些姥姥聽得懂的章節,像她寫的種菜的、走馬廄的、紀念父親給她做燈的那些事。
有一天,我拿回一張我和遲子建的合影,說:“姥姥,你給相相面,照片上的這個人有什么神的地方沒有?”
姥姥笑了:“一對兒神人,不知道的還以為是一個娘肚子里生的姐兒倆。”姥姥說我和遲子建長得像。
姥姥愛書對我是個極大的推動。一個不認字的老太太都這么明白知識的力量,我這么個認得一些字的人還不好好讀書,不應該呀。
(摘自長江文藝出版社《姥姥語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