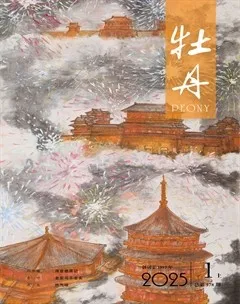收秋記憶
秋風一夜間走進村子里,聞到玉米成熟的香味,村民們開始躁動起來。把擱置在房前屋后的鐵锨、镢頭、糞叉,聚集起來,打磨錚亮。
漫長的收秋從豬圈撕開裂口。男人們穿上膠鞋跳進豬圈,甩出胳膊,雙手半合攏對著嘴,呸一口唾沫,就一叉接一叉,撂出黑臭的豬糞。我穿上父親的高筒膠鞋,拖拉著走到豬圈前,學著男人的模樣,用最帥氣的姿勢跳了進去,嚇得兩頭豬逃竄到角落,貼著墻瑟瑟發抖,任我揮動釘耙和糞叉。我必須用兩天的時間,將它們的領地掏空。
月色跌落在街道上,像水一樣滲進矩形狀的糞堆里。男人們零散著蹲在街頭,對著影子,喝著玉米糊糊,風刮了過來,一股濃烈的豬糞味,讓他們端著碗的左手更加有了力氣。草叢里傳來的蛐蛐聲,讓玉米又長瓷實了一成。
張三埋頭從地里拉回一車玉米穗,倒進院子。村民圍在他家院子里,撕開玉米包衣,大拇指甲掐著玉米粒,推算著自家玉米成熟的日期。
架子車的輪胎,已修補好,鼓鼓的,發脹到要跳起。村民們嗅著玉米香氣,男人拉著架子車,女人胳肢窩夾著編織袋,走進玉米地。整個村子的玉米稈密密麻麻,都在搖晃。大規模的收秋來了。
母親烙出十來張油餅,特意加了蔥花與花椒粉。我坐在玉米地深處的田埂上,將流油的咸雞蛋裹進蔥油餅。玉米葉隨風嘩嘩作響,蟋蟀在我腳面上蹦來蹦去。四畝多地的玉米,兩天就被我拉回家里。
收成喜人。在地里掰玉米穗時,我看見我和母親夏天澆地時留下的腳印,一滴汗,還掛在腳印旁的草尖。那時,成片的玉米地在日頭下散發著耀眼的綠,我和母親在澆地之前為它們封上了化肥。玉米葉刮拉得臉生疼,土地慪氣般蒸騰著熱浪,母親弓著腰用镢頭刨出一個坑,我緊跟著丟一把化肥,母親再刨個坑,用新土將化肥埋上,我就再丟一把化肥。一個坑連著一個坑刨著,埋著。一臉盆接著一臉盆的化肥,熏得我倆眼睛疼,心口也跟著發悶。干農活要隨著莊稼的性子。
我和弟弟妹妹圍著滿院子的玉米穗,比賽扯玉米皮。貼近玉米籽的包衣,薄如蟬翼,單獨存放起來,留給奶奶編制蒲團用。母親踩著玉米穗,跳進廚房 ,顫巍巍地端出一鍋湯面。弟弟嘴里團一根略帶毛刺的小白菜,吐不出來,咽不下去。我們剝去玉米穗粗糙的外衣,留下柔軟的櫻子,編辮子似的,把玉米編在一起,掛在屋檐下,纏在椿樹上,搭在平房頂的圍墻上。一片金燦燦。
沒有圍墻的院子,四處漏氣。
夜幕降臨,院子里樹影婆娑,沙沙響,星星落到了我的湯碗里。村子里的腳步聲,咳嗽聲,低語聲,震得掛在房梁上的煤油燈,一晃一晃。母親摸著黑,用幾塊舊磚頭茬了兩個半米高的磚墩,橫架上一根锨把一樣粗細的桐木棍。弟弟妹妹貓腰在桐木棍下鉆來鉆去,解鎖出一門新游戲。母親說這是院門,要輕拿輕放。風停了,所有的響聲止在院門外。
沒有玉米穗的玉米稈,立在風中,沒了魂,輕飄飄地舞。我踩著不太松軟的玉米地,弓腰用短鋤頭將一棵棵玉米稈連根刨出,那密密麻麻扎入土地的根須像聚攏的手指,帶出許多泥土,我挺起腰桿用鋤頭敲落泥土后,把玉米稈整齊放倒在地,讓它們頭擠頭,腳挨腳。
隔壁地里,吆喝聲不斷,趙六兄弟幾個,把砍掉的玉米稈,高高壘在架子車上,一車就拉出兩畝多地。弟弟拽一根狗尾巴草跑來,喊我回家吃飯。我卷起半畝地的玉米稈放進架子車,勒緊繩子。扭過頭,弟弟手里的狗尾草已串滿蟋蟀,黑壓壓的一群細胳膊細腿,不停扭動。發黃的玉米稈還給豬圈,兩頭豬像坐在轎子里,被緩緩抬起。
父親回來了,他環視著一院子的金黃,滿臉喜氣。他放下背包,扯出里面的一圈花電線,將梯子靠在西鄰居的山墻,接上了電線。那夜,在村里最后一聲的狗吠中,我家的院子亮了。黑夜猛地后退,土墻外的桐樹林向院子逼近,驚動了幾只落腳的飛鳥,撲棱棱地掠過雪亮的屋頂,一株瓦松跟著搖晃。自從讀過《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后,一到夜里,我總認為那一截土墻上也有一張美女蛇的臉,煞白煞白的。摸黑上茅房時,聽見樹葉的沙沙聲,我都嚇得心驚肉跳,背貼著墻大氣都不敢出。那夜,我第一次和弟弟妹妹在院子里推起鐵環,嘩啦啦,一圈又一圈,我第一次忽略掉了月光,忽略掉心里的那堵土墻,連往事都被照得透亮。
拖拉機大規模犁地的時間定下了,豬糞要在規定時間運到地里去,幾十輛架子車,浩浩蕩蕩在街道里穿梭,人人腳底帶風。空車禮讓重車。關系親近的村民碰面,匆匆報一下自家的進度,爭分奪秒走開。機井房旁坑坑洼洼的泥路,墊上了碎磚頭和瓦片,新壓出的車轍,瓷丁丁的,駕轅的人通過這截路,都是同一種走勢。李虎的嫂子專程從縣里趕來,蹲在上坡處,等他家兩輛糞車到時,就撅屁股彎腰扶著車幫,助一臂之力。趙六家把已崩裂的車轱轆纏上花圍巾,轉起來,像飛舞的花蝴蝶。系在父親車把上的助力繩,一路被我拉得緊繃繃。滿街道的腳步聲,咚咚響,震得整個村子一跳一跳的。
鐵鏈拖拉機亮著強光,嗷嗷叫進場了,留下兩條淺淺的履痕。太陽下山前豬糞已被均勻撒開。黑暗中,伴著拖拉機的嘯叫聲,村民們跟著犁地的進度,把化肥撒開,讓它在最短的時間里埋進新鮮的泥土。化肥袋縫線太難解鎖,我每次都急得用牙咬出豁口,嘴巴里殘留著一股子化肥味。空氣中散發著泥土味。
翌日清晨,旋耕機將泛著濕氣的泥土粉碎,田地歸零恢復到播種的狀態。
我光腳踩在松軟的土地上,慢慢下沉,像麥種埋在土里。
李秋燕,供職于焦作市山陽區人社局,有多篇文章發表在地方報刊和網絡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