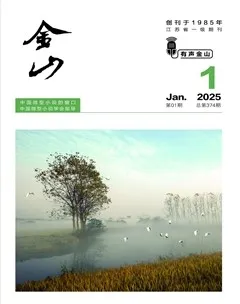海上放牧
乘船,從沙頭港出發,向東約25海里,歷經海浪顛簸,在一望無垠的大海中,七星海洋牧場似一座白色城堡躍然眼前。站在船頭遙望,城堡矗立在海天之間,顯得既壯觀又神秘。從無人機的回傳視頻看,此平臺又像一朵綻放在藍色海面上的荷花,美輪美奐。
海洋牧場不長青草,不放牧牛羊,而是養魚。城堡下方的大海就是天然的養殖場,就是魚的家。
接待我們的老葛是位40多歲的漢子,中等身材,皮膚黝黑。他是海洋牧場的技術負責人,吃住在城堡里,整天伺候網箱里放養的魚。
城堡固定在大海中,下部是巨大的長方體鋼架,上部是工作平臺。平臺上有老葛他們的生產控制室、原料倉庫、生活設施,還有直升機起降小平臺。養殖網箱就固定在長方體鋼架里,箱體長60米、寬60米、深25米。網箱說是箱,其實是用網圍起來的,網目8厘米。網箱外的海底布設了人工魚礁,營造出更加良好的魚類生活環境。
“網箱是通透的,箱內外的海水自由流動。這里養出來的魚,和大海里自然生長的魚品質差不多,具有較好的野生特性。所以,這里不叫海上養殖場,而叫海洋牧場。牧的古字是象形字,就是手拿木棍驅趕牲畜,在海洋牧場驅趕魚奔跑的不是木棍,是海流和波浪。”老葛為我們揭開了海洋牧場的第一個秘密。
老葛,微信上的名字叫漁夫。水產學院畢業后,一直在和魚打交道,奮戰在魚類養殖一線。給魚治病,培育新魚種,從土池到標準池,從露天池塘到大棚養殖,到工廠化養殖,致力于推進魚類養殖向高產、生態、優質發展。但是,20多年來,老葛一直都在和淡水魚打交道,還從來沒有下過海,沒有沾過海水的腥和咸。
找到他,請他到海洋牧場養魚,老葛猶豫過,對他來說這完全是一次全新的挑戰,存在著很大的職業風險,但他最終還是答應了。在山東一家海洋牧場實習培訓了3個月后,老葛進駐這座城堡。
在海洋牧場,老葛遇到的全是新課題。海溫、海浪、海流,風暴潮、綠潮、赤潮,大黃魚、黑鯛、海鱸魚,每一樣都很新鮮,都需要學習、研究,掌握特性和規律。特別是網箱內混養的幾種海水魚,它們是完全陌生的朋友,但是要與它們相識、相知、相伴,這不是培訓幾個月、看幾本書能夠解決的,更需要時間、更需要積累、更需要用心付出。
牧場放養5萬多尾魚,開始試運行。老葛和兄弟們一起走上了戰場,精神抖擻,全神貫注。控制臺上的滿屏數據,老葛知道每個數字的意義、作用,洞察每個數字的變化。老葛還有一個自己的日記本,每一個問題和發現,都記錄在冊。現在他的床頭上,日記本已堆起厚厚的一摞。
在生產控制室,老葛向我們介紹海洋牧場的生產情況,為我們揭開海洋牧場的又一層神秘面紗。“水下有監測系統,可實時記錄牧場水域的溫度、流速、流向、鹽度、溶解氧濃度等多項指標,360度無死角監控魚類的生長環境。”他邊說邊點開一個頁面,上面顯示當前海水溫度13.5℃、鹽度28.14PSU、pH值8.45、溶解氧濃度7.77mg/L。“如果發現哪個指標低于安全值,屏幕上就會作出警示,提醒海洋牧場出現了‘警情’。你看,葉綠素的當前狀態顯示為‘偏低’。”老葛指著屏幕說。
老葛是這片牧場的主心骨,場上兄弟們對他有一種依賴、有一份期待,遇到問題,首先想到的就是老葛。老葛也知道自己肩上的擔子和責任,邊自己摸索,邊帶教這幫兄弟,他要讓他們一起擔負起這副擔子,個個成為牧場的本土專家。
肩上的擔子重,大家一起扛。生活上的不便和艱苦,只能自己適應和克服。城堡就像一座島,雖然風力發電機提供源源不斷的電力,淡化海水設備也能供應充足的生活用水,但是孤獨和寂寞,對每個人都是一道難以跨越的坎。兄弟們還有每月輪換上岸的日子,而老葛在牧場一待至少半年,心理上的煎熬是一種摸不著、消不掉的痛。
從淡水到海水,從池塘到牧場,從戰戰兢兢到心中有底,一次轉身竟是一段“煉獄”。老葛慢慢地走過來,灑下一路苦咸的汗水,留下一路深淺的腳印。座談的時候,老葛說:“探路的事總要有人去做,蹚出了成功的路子,別人再走就要輕松一些,快上許多。”我了解老葛,這不是大話、臺面上的話,發自他的心底,也是他做出來海上放牧選擇的內核支撐。
每片海都有自己的特性和脾氣,這里到底哪種魚最適宜放養,還要控成本、有效益,老葛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探索。
又是一個風和日麗的秋日,老葛走出控制室,在牧場巡查。看看眼底下的巨大網箱,望望視野中的一片汪洋,心中翻騰著陣陣波濤,四周回蕩著澎湃的海洋牧歌,老葛攥緊拳頭給自己鼓勁:“加油,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