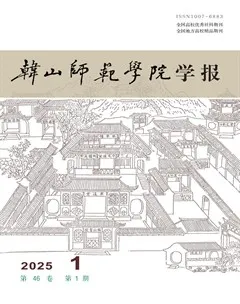論黃國欽散文集《潮州傳》的語言特色
摘 要:黃國欽對(duì)潮州文化有著高度的認(rèn)同。他的散文集《潮州傳》既有濃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又有橫貫古今的廣闊視野。他重視散文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語言運(yùn)用,以文白結(jié)合展現(xiàn)其古樸性。通過四字格、長短句、排比等的合理搭配,既清新流動(dòng)、充滿音樂性,又有效實(shí)現(xiàn)了內(nèi)容和形式的統(tǒng)一。為城市做傳,黃國欽用生動(dòng)的文學(xué)語言,調(diào)和文學(xué)與歷史,立體敘述了潮州古往今來的歲月。
關(guān)鍵詞:黃國欽散文;《潮州傳》;語言特色;地域性;文化散文
中圖分類號(hào):I 207.67"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7-6883(2025)01-0056-05
DOI:10.19986/j.cnki.1007-6883.2025.01.009
黃國欽是潮州孕育出來的作家。他深情地貼近生活于此的人民、深切地感受著土地的歷史。沈從文指出:“一個(gè)作家一支筆若能忠于土地,忠于人,忠于個(gè)人對(duì)這兩者的真實(shí)感印,這支筆如何使用,自不待理論家來指點(diǎn),也會(huì)有以自見的。”①
黃國欽散文創(chuàng)作中的地域特色不言自明。黃景忠指出,地域散文中的黃國欽是以潮州文化代言人的姿態(tài)在寫作,因而字里行間都透露出對(duì)潮州的偏愛。而人物散文因其獨(dú)特的敘述指向和結(jié)構(gòu)方式則包含濃郁的人道情懷。黃景忠以“詩性傾訴”[1]概括黃國欽散文創(chuàng)作中貫穿始終的語體特征,并指出其中蘊(yùn)含的音樂感、節(jié)奏感是其散文藝術(shù)魅力的體現(xiàn)。姚則強(qiáng)將黃國欽的散文放置在城鎮(zhèn)化的過程中來考量,無論是對(duì)鄉(xiāng)土生活的舒緩展開,還是對(duì)山水意蘊(yùn)的審美表達(dá),或是在寫人記事中流露出的真摯之情,皆深藏著人文意蘊(yùn)和歷史情懷。[2]
黃國欽在2022年出版的地域性文化散文集《潮州傳》中,通過多種方式調(diào)用語言,使得文學(xué)、歷史和情感在此書中達(dá)到了平和相容,而如黃景忠所形容的“音樂感”和“節(jié)奏感”也以一種集聚的狀態(tài)得以展現(xiàn)。這本富有藝術(shù)魅力的城市傳記深刻地展現(xiàn)著他的非凡的筆力和深厚的文學(xué)積淀。筆者嘗試以語言為切入口進(jìn)入文本,發(fā)掘黃國欽在書寫地域歷史的過程中如何展現(xiàn)歷史的細(xì)枝末節(jié)和生活的百樣姿態(tài)。
一、語言的古雅性:
傳統(tǒng)文化的深厚積淀
黃國欽具有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在地域性歷史文化散文集《潮州傳》中,他使用了文白交雜的語言。從標(biāo)題到內(nèi)容,恰如其分地融合古詩句、文言句式等,使文章整體透露出古典雅致的格調(diào)。
文章題目具有傳遞信息和吸引讀者的雙重功能。《潮州傳》中的多篇文章標(biāo)題直接引用古詩詞。如《一封朝奏九重天》,即出自韓愈的《左遷至藍(lán)關(guān)示侄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一封《諫迎佛骨表》引得憲宗大怒,韓愈被貶為潮州刺史。他踏足潮州,祭鱷驅(qū)鱷、修堤鑿渠,為潮州百姓帶來安居樂業(yè)。一封朝奏于韓愈而言,是仕途的轉(zhuǎn)折點(diǎn);于潮州而言,是新歷史的起點(diǎn)。以此為題,韓愈和潮州之間的故事順理成章地展開。《十八梭船鎖畫橋》講述了歷朝歷代修繕廣濟(jì)橋的過程。此句出自乾隆進(jìn)士、潮州人鄭蘭枝《湘橋春漲》中的“湘江春曉水迢迢,十八梭船鎖畫橋”。廣濟(jì)橋中的浮橋是由十八只木船連接而成,這正是廣濟(jì)橋最突出的特點(diǎn)之一。故以此為題,畫面感十足。《地瘦栽松柏》一文,開篇即從潮州的民性、民風(fēng)講起,似乎和標(biāo)題沒有任何關(guān)系。然而“松柏”作為中國人一個(gè)重要的文化符號(hào),本身就蘊(yùn)含著耐人尋味的深遠(yuǎn)意境。而標(biāo)題實(shí)則取自王大寶對(duì)孝宗皇帝風(fēng)俗之問的回答,記載于《永樂大典·風(fēng)俗形勝》中,全句為:“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通讀全文,才發(fā)現(xiàn)文章和標(biāo)題的重點(diǎn)都是潮州的尚學(xué)之風(fēng)。了解了標(biāo)題的出處,才明白其中蘊(yùn)含的地方的歷史底蘊(yùn)和文化風(fēng)尚。黃國欽的引用并非隨意撿拾,而是兼顧語義和審美。他的標(biāo)題往往不能一眼明了全意,但又不至于艱深晦澀。通讀全文,方能感受其用意之深。
正文內(nèi)容更加全面地展現(xiàn)了古典文學(xué)和傳統(tǒng)文化對(duì)黃國欽創(chuàng)作的浸潤滋養(yǎng)。首先是對(duì)古詩詞恰到好處的引用和化用。德祐二年,宋王朝陷入危難之際,文天祥挺身而出,黃國欽寫道:“大廈將傾,也仍有人在力撐危局。”[3]256此句化用蘇軾在《蘇文忠公全集·告文宣王文》中所言:“回狂瀾于既倒,支大廈于將傾”。描繪文天祥的臨危不懼,作者評(píng)之以“疾風(fēng)知?jiǎng)挪荩瑖鴣y顯忠臣”[3]256。此處則是化用李世民的“疾風(fēng)知?jiǎng)挪荩迨幾R(shí)誠臣”。黃國欽在用典之時(shí)并非“食古不化”,將傳統(tǒng)文言進(jìn)行現(xiàn)代性的轉(zhuǎn)化,整合到散文寫作之中,從而營造出一種雅俗共賞的散文語體。耳熟能詳?shù)脑娋浜苋菀讍酒鹱x者的歷史文化記憶,深層的含義與描繪的場景融為一體,不僅增強(qiáng)了表現(xiàn)力,更使閱讀過程充溢著對(duì)古典文學(xué)古為今用的文化視野。
除了恰到好處地放置一些古詩詞,黃國欽在文中更是直接使用了文言句式。例如:“潮州如此物阜民豐,蒸蒸然焉,朝廷聽之聞之,自然動(dòng)心,揭陽置縣,遂水到渠成。”[3]181“蒸蒸然”將民間發(fā)展繁榮之態(tài)比之水氣上升,語言形象又凝練。“焉”字無意,湊足音節(jié),讀之則韻味叢生。文言句式較之現(xiàn)代漢語,結(jié)構(gòu)更加緊縮,行文更加簡潔。在《許夫人和陳璧娘》中,陳璧娘作《平元曲》以表決心。黃國欽為其心理活動(dòng)展開了更為詳細(xì)的敘述,他寫道:“(璧娘說)心已至此,志已至此,夫復(fù)何言。”[3]289短短十二個(gè)字就將陳璧娘為國效力的決心與氣魄托舉到最高處。陳璧娘的巾幗形象在最后的反問中樹立起來。在此處,使用的文言詞語干脆有力,氛圍在韻律中層層烘托。黃國欽還有意使用一些讀者比較陌生的成語。例如,描寫北宋末年,受戰(zhàn)火影響,孔廟被毀,他寫道:“所有的樂器,淪胥無遺,奏樂的設(shè)備,也焚毀殆盡”。“淪胥”最早出自《詩經(jīng)·小雅·雨無正》:“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意為“受到牽連而遭受苦難”。后在《晉書·卷八七·涼武昭王李玄盛傳》中又有記載:“淳風(fēng)杪莽以永喪,搢紳淪胥而覆溺。”可理解為“完全喪失”之意,黃國欽便是用了這一含義。同時(shí)結(jié)合后文中的“焚毀殆盡”,對(duì)其義也可知一二。此處使用成語不僅沒有掉書袋的嫌疑,反而使文章帶有駢文之美,更加典雅。
由此可見,黃國欽有著深厚的語言功底。他可以恰如其分地選擇合適的古詩句為自己的文章添彩,又自如地切換白話和文言句式,通過詩性的語言刻畫歷史人物、書寫志向抱負(fù),讓文章意蘊(yùn)悠長。
二、語言的音樂性:
韻律化與節(jié)奏化
黃國欽曾與韓山師范學(xué)院中文系的學(xué)生分享過自己散文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yàn)。他尤為強(qiáng)調(diào)字句運(yùn)用的重要性:“在散文創(chuàng)作中,還要講究字、句的平仄,講究疊字、講究排比句、講究句子的運(yùn)用,講究長短句的搭配。”[4]228文學(xué)語言應(yīng)是藝術(shù)的語言,也應(yīng)是審美的語言。對(duì)散文語言的音樂性陳劍暉認(rèn)為:“散文語言的音樂性雖包含排比對(duì)偶,但不等于排比對(duì)偶,就現(xiàn)代散文的語言來說,音樂性更在于長短參差,可伸可縮、形神兼?zhèn)洹⑸鷼夤嘧ⅰ⒘鬓D(zhuǎn)自如。”[5]語言的音樂性可以增強(qiáng)散文的感染力和可吟詠性,使得文章更加生動(dòng)有味。黃國欽下筆平和順暢,散文的節(jié)奏性和音樂性主要通過排比、四字格,以及長短句的合用整體體現(xiàn)出來。在《潮州傳》中,隨處都能找到音樂性流轉(zhuǎn)其中的痕跡。
四字格的連用,使得文章讀起來輕快明朗。黃國欽筆下的潮州姑娘是“溫婉嫻雅、婀娜多姿、輕聲細(xì)語、笑靨如花,骨子里卻自有俠肝義膽、柔情似水、烈骨如霜、忠貞無瑕”[3]287。寫外在形象,作者分別從性格、身量、語態(tài)和面容四個(gè)角度概括。寫內(nèi)在的品質(zhì),他又連用四個(gè)四字詞,展現(xiàn)其內(nèi)外兼修、剛?cè)岵?jì)。姑娘的形象在八個(gè)四字詞語的構(gòu)筑下頓時(shí)立體鮮活。又如,描寫開元寺,他寫道:“開元寺的云板木魚、晨鐘暮鼓,早晚之間,悠悠揚(yáng)揚(yáng),也能讓人在動(dòng)亂驚悸之中,感到一些寬心舒暢……寺在潮州城中央,更深夜靜,關(guān)門閉戶,路無行人,板磬之拍、鐘鼓之聲,讓世人聽之聞之,亦沉寂下來,入靜無擾,平和隨性。”[3]527此句形式上勻稱流動(dòng),讀起來充滿韻律。內(nèi)容上既直接描繪了開元寺的鐘鼓悠揚(yáng),又以動(dòng)襯靜,板磬鐘鼓之聲更使得其幽靜平和一覽無余。作者從多個(gè)角度描繪所寫之物,但并沒有為了追求格式的整齊而犧牲內(nèi)容。在《我以我血薦軒轅》中,潮州城失守,馬發(fā)一行陷入絕望之境時(shí),他寫道:“落夜,率著殘部100多人,奮力死戰(zhàn),退守到金山子城的馬發(fā),屹立山頭,看夜色深沉,天涼風(fēng)緊,寒星閃爍,鉤月微明,山黯如漆,樹黯如影。子城外面,燒殺擄掠,悲呼慘號(hào),陣陣傳來,驚天泣地,不絕于耳。”[3]275作者再次使用了多個(gè)并列的四字詞語。一段話中既有觸覺,又有視覺;既有自然景色,又有戰(zhàn)況實(shí)錄。語言朗朗上口,語調(diào)抑揚(yáng)頓挫,和當(dāng)時(shí)的情況緊密相合。讀之便覺馬發(fā)退守金山子城的局勢(shì)緊張、情況危急。城內(nèi)外形成鮮明對(duì)比,更顯戰(zhàn)況危急、民不聊生。詞語與詞語之間層次豐富,使得行文句式整齊、節(jié)奏緊湊,無拖沓累贅之感。
黃國欽對(duì)詞語的選用和排列都有自己獨(dú)到的文學(xué)審美情趣。這是在深刻把握描寫對(duì)象特點(diǎn)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理性判斷和斟酌后得到的。唯有恰當(dāng)?shù)娜∩岷桶芽兀拍芗炔皇箤?duì)象落入自己的想象中而失真,又能充分展現(xiàn)文章的生氣。
除了四字詞語的連用,音樂性還表現(xiàn)在長短句的配合上。若樂章只有一種旋律,那聽久了未免枯燥乏味,散文也是如此。在描寫周穆王揮師江南、渡過軍用浮橋時(shí),作者寫道:“其時(shí)橋上腳步咚咚,橋下水波漣漣,旌旗鼓角,皮甲藤盔,隊(duì)列隨浮橋擺動(dòng),旗鼓合水波起伏,別有一番扣人心弦。”[3]205作家在此處用了三組對(duì)仗,分別為六字、四字、七字。句子長短錯(cuò)落,又富有對(duì)稱性,在形式和語音上共同展現(xiàn)了過橋時(shí)的恢弘氣勢(shì)。擬聲詞“咚咚”和擬態(tài)詞“漣漣”兩個(gè)疊音放在一起,將橋上人的走動(dòng)和橋下水的流動(dòng)構(gòu)成一幅動(dòng)態(tài)畫面。這一處理方式既帶來了音樂性,又強(qiáng)化了畫面感。在描繪潮州人煮糜的時(shí)候他寫道:“水少,米多,干柴,猛火,火在鼎下、鍋下,呼呼呼呼地叫著,不久,糜就滾了,頂著鼎蓋鍋蓋,沸出灶臺(tái)。”[3]272四個(gè)二字詞語的并列將潮州人煮糜的要點(diǎn)一一羅列,干脆簡練。“叫著”“滾了”“頂著”“沸出”四個(gè)動(dòng)詞連續(xù)推進(jìn),灌注在日常生活中的經(jīng)驗(yàn)呼之即出,煲糜的形態(tài)躍然眼前。黃國欽對(duì)潮州風(fēng)物、日常生活有著敏銳的感知。在此基礎(chǔ)上,他把自己的經(jīng)驗(yàn)經(jīng)歷和故鄉(xiāng)的獨(dú)特性以一種富含趣味又天衣無縫的方式結(jié)合起來,進(jìn)而使得日常瑣碎轉(zhuǎn)換為審美對(duì)象。
對(duì)于潮州大地,黃國欽向來不吝贊美之詞。生于斯長于斯,潮州的三十六街、百廿四巷于他而言,再熟悉不過。他能夠感受到自己和潮州大地之間超越時(shí)空的深度聯(lián)結(jié):“生長在潮州這塊土地,每天每夜,總有一種異樣的神韻在吸引著我,昭示著我,那是一種遙遠(yuǎn)歷史的回聲,那是一條豐沛大河在澎湃,那是冥冥中遠(yuǎn)古的先民在吟哦。”[4]7深厚的土地意識(shí)早已融在他的血液中,進(jìn)而化作文字從筆尖流淌出來。書寫人事,他的筆調(diào)充滿溫情;目及山川風(fēng)物,他又能兼顧人文和歷史。我們能很輕易地在他的筆下找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證據(jù)。更重要的是,他對(duì)潮州文化有著與生俱來的認(rèn)同感。這種認(rèn)同感推動(dòng)著他發(fā)現(xiàn)潮州民俗風(fēng)物的審美價(jià)值和文化價(jià)值,并孜孜不倦地深入歷史的深處,發(fā)掘古潮州人的生活情趣,探求著屬于這片大地的原始生命力。
節(jié)奏的快慢配合著上下文的語義,既可以平緩如溪流,又可以急促如山洪。黃國欽利用語音的優(yōu)勢(shì)將語義外化為恰當(dāng)?shù)淖中危ㄟ^“語言的韻律化和節(jié)奏化可以使并無詩意的語言產(chǎn)生詩意”[6]。倘若沒有在這片大地上真實(shí)生活過,是沒有辦法在書寫地域歷史的時(shí)候如此生動(dòng)的。如此書寫,既體現(xiàn)了凝聚中國詩性文化的審美情趣,又展現(xiàn)了作者調(diào)用詞語的得心應(yīng)手。這種得心應(yīng)手來自于對(duì)潮州大地的熟悉,也來自于年深日久的自我修養(yǎng)。作者用充滿韻味的語言完成了地域文化、傳統(tǒng)文化和現(xiàn)代經(jīng)驗(yàn)的情感連接,使得這種內(nèi)化在基因中的記憶借由文學(xué)的方式賡續(xù)下去。
三、語言的生動(dòng)性:
文學(xué)敘述和歷史敘述調(diào)和兼顧
《潮州傳》,顧名思義,是為潮州做傳。城市傳記需要兼顧歷史和人文,在人、事、城三者之間找到一種內(nèi)在連接,在與過去的深度對(duì)話中厘清城市的演進(jìn)歷程。邱華棟在《北京傳》中寫道:“一座城就像是一個(gè)人,也是慢慢生長起來的,城市是一個(gè)生命體。”[7]一座值得書寫的城市應(yīng)該是鮮活的。這種生機(jī)比一個(gè)人的成長來得更加緩慢。書寫者需要更有耐心地沿著歷史脈絡(luò)溯流而上,在卷帙浩繁中精心篩選和取材,才不至于在史料的堆疊中迷失。選擇恰當(dāng)而獨(dú)樹一幟的文明視點(diǎn),才能讓一座城以其特有的姿態(tài)被人記住。于黃國欽的潮州而言,這個(gè)視點(diǎn)是韓江、城墻、廣濟(jì)橋;是韓愈、王源、翁方綱;也是潮劇、打春、拜月娘。在不同的主軸下以最貼合的史料為證,便可以此為支點(diǎn)構(gòu)筑立體的城市風(fēng)貌。黃國欽借用文學(xué)的想象,圍繞著恰當(dāng)?shù)囊朁c(diǎn),豐富了歷史的生動(dòng)性,從而調(diào)和了文學(xué)的溫度與史學(xué)的厚度。
地域文化散文并不是史書的翻寫,它的獨(dú)特價(jià)值應(yīng)該在于:“挖掘被人們遺忘的重要記憶,再現(xiàn)歷史人物的鮮活面貌和細(xì)部真實(shí)”[8]。謝有順分析過歷史對(duì)于散文的獨(dú)特之處,他指出:“對(duì)于散文而言,歷史這個(gè)闊大命題的誘人之處,并不在于訴諸史料的歷史傳奇和歷史苦難的演義,而是在于那些長年沉潛在民間的獨(dú)特段落和瞬間。這些段落和瞬間里面所蘊(yùn)含的精神消息,往往才是巨大的,震撼人心的,它與在野的文明、異質(zhì)的文化、民間的傳統(tǒng)一脈相承。”[9]歷史的主流固然值得書寫與銘記,但是散落在歷史邊緣的人物和事項(xiàng)也值得反復(fù)品味。文學(xué)可憑借其敏銳性與溫和性,重新發(fā)現(xiàn)“在野的文明”中蘊(yùn)含的生機(jī),使其重綻光彩。
隨著戰(zhàn)火烽起、朝代更迭,潮州大地也隨之浮沉。反元?dú)w宋的馬發(fā)或是巾幗英雄許夫人自然值得彪炳史冊(cè),但并非只有撼動(dòng)社會(huì)發(fā)展的事件才允許被記住。描寫摧鋒軍晨練時(shí),作家看到了軍營的井然有序。同時(shí)又將筆鋒一轉(zhuǎn),寫了同一時(shí)間沒去看摧鋒軍晨練的潮州人。潮州人食早糜,是生活的常態(tài),也是潮州獨(dú)特的風(fēng)俗之一。士兵與普通百姓、操練和食早糜、戰(zhàn)爭與日常,都在此處平和相容。作者并沒有用宏大敘述淹沒日常話語。因?yàn)槠淠康牟⒎鞘菫榱烁韫灥拢桥?dāng)時(shí)的面貌以一種盡可能全面的方式展現(xiàn)出來。于是,生活的細(xì)枝末節(jié)也被關(guān)照到。文學(xué)尋找到了歷史未曾書寫的暗處,拂塵去灰后為其重新上色。作者還將坊間傳言、民間傳說納入視野。這些傳說雖非正史,卻不失為對(duì)歷史的補(bǔ)充:“坊間相傳,昔日樟林港口有一處盛景,曰:‘仙人翻冊(cè)’……船和帆也必須隨著轉(zhuǎn)向,遠(yuǎn)看猶如仙人無形的手,在一頁一頁地翻動(dòng)書冊(cè),妙不可言。”[3]451口耳相傳中的神秘與奇詭讓樟林港口多了一份迷人色彩。紅頭船造好之后,“在兩側(cè)紅油上又畫了黑油圓圈,如同雞目一樣。按民間的說法,船上有眼,才不致迷失航道”[3]456。民間帶有虛幻色彩的迷信往往包含著祈禱和慰藉,作者并沒有對(duì)其視而不見,而是表現(xiàn)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透露出了深植內(nèi)心的人文關(guān)懷。此外,在敘述中,作者自然地融合了當(dāng)?shù)氐拿裰V民謠民歌,活潑生動(dòng)又趣味盎然:“鳳凰山頂無日無云煙,湘子橋上無日無神仙”[3]220、“人力落,地不惰,老伯公,說好話”[3]395。極富當(dāng)?shù)靥厣恼Z言的使用給傳記增添了不少親切感,使文字也變得可吟可唱。作者沒有在歷史大潮中迷失自我,而是在史海浮沉中恰如其分地將視野聚焦于風(fēng)物、風(fēng)俗、風(fēng)土人情之中,讓如今生活于此的人們窺探到遙遠(yuǎn)的精神印記。
為城市做傳而非寫史,更需要作者雄渾的筆力和寬闊的情懷,從而使歷史話語與文學(xué)話語保持恰到好處的平衡。黃國欽在忠實(shí)歷史的基礎(chǔ)上讓人物都活泛起來。南宋危在旦夕,黃國欽寫道:“文天祥悻悻,在蓮花峰旁巨石,劍刻下‘終南’兩個(gè)斗大楷字。南宋版圖,到這里已是盡頭,南宋歲月,到這時(shí)也行將就木。文天祥有一肚子話,都傾訴在劍下的這兩個(gè)字。”[3]265黃國欽的描寫讓文天祥具有真實(shí)可感的溫度。其中不乏個(gè)人的情緒流露,“悻悻”便是作者深入歷史深處,對(duì)人物內(nèi)心的深刻把握。佇立在蓮花峰旁,看到驚濤拍岸時(shí),沉默不語,而是以劍刻二字以表心跡。作者自然地將實(shí)地考證、歷史考據(jù)和個(gè)人情感融合為一。帶有文學(xué)色彩的敘述讓人物鮮活,歷史的呈現(xiàn)才不至于單調(diào)乏味。這是作者在歷史事件、當(dāng)代經(jīng)驗(yàn)和自我感悟中尋找到了恰當(dāng)?shù)目臻g,從而為讀者再現(xiàn)了生動(dòng)的歷史瞬間。
德國歷史學(xué)家卡爾·雅斯貝斯分析了歷史和回憶之間的關(guān)系:“對(duì)于我們,歷史乃是回憶,這種回憶不僅是我們諳熟的,而且我們也是從那里生活過來的。倘若我們不想把自己消失在虛無迷惘之鄉(xiāng),而要為人性爭得一席地位,那么這種對(duì)歷史的回憶便是構(gòu)成我們自身的一種基本成分。”[10]《潮州傳》將社會(huì)生活、風(fēng)物建筑、民俗人情都納入關(guān)注視野,回溯過往,以翔實(shí)的史料為基礎(chǔ)從潮州的文化源頭開始講述,把節(jié)奏放慢,不急不緩地將幾千年悠久而豐饒的歷史畫卷徐徐展開,讓讀者看到了站在文化長河中從未消失、始終熠熠生輝的潮州。正是作者對(duì)事件的深度梳理、對(duì)歷史的反復(fù)重溫、對(duì)精神文脈的不斷探尋,才讓文明和文化從生硬的史料中復(fù)蘇。
正如南帆所言:“來自各種歷史著作的史料棱角堅(jiān)硬,邏輯固定,文學(xué)話語的接收、改造和重新裁剪常常艱澀凝重。相反,來自記憶的各種情景柔軟可塑,活靈活現(xiàn),仿佛與文學(xué)話語一拍即合。事實(shí)上,記憶與文學(xué)話語時(shí)常珠聯(lián)璧合,交相輝映。”[11]黃國欽通過自己的話語策略,將歷史化為記憶的一部分,繼而被文學(xué)話語重新敘述。不論是文白結(jié)合,還是語言的節(jié)奏性,或者是在真實(shí)的史料基礎(chǔ)上融合生動(dòng)的現(xiàn)實(shí),這些書寫方式才讓潮州不單是當(dāng)下的潮州,更是凝聚幾千年文明的古城。潮州的過往已成定局,然而正是這別具一格的敘述,才能讓生活在這里的每一個(gè)潮州人都感受到來自古老記憶的傳喚與共鳴。《潮州傳》無疑是在歷史和文學(xué)的雙重視野下,對(duì)城市外在形象和內(nèi)在溫度的綜合把握。
參考文獻(xiàn):
[1]黃景忠.仁者的散文——談黃國欽的散文創(chuàng)作[J].韓山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7(2):6-9.
[2]姚則強(qiáng).論黃國欽散文的人文情懷和意境[J].韓山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7(4):62-66.
[3]黃國欽.潮州傳[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
[4]黃國欽.花草含情[M].呼倫貝爾:內(nèi)蒙古文化出版社,2014.
[5]陳劍暉.論中國散文的抒情傳統(tǒng)[J].文藝?yán)碚撗芯浚?019(4):1-9.
[6]薛世昌.現(xiàn)代詩歌創(chuàng)作論[M].長春:吉林大學(xué)出版社,2008:69.
[7]邱華棟.北京傳[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0:23.
[8]張翼,張宇.地域文化散文書寫的藝術(shù)追求與價(jià)值——評(píng)孟豐敏的散文集《鄉(xiāng)愁里的福州》[J].福建工程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2(20):199-204.
[9]謝有順.不讀“文化大散文”的理由[J].散文百家,2003(2):48.
[10]歷史的話語:現(xiàn)代西方歷史哲學(xué)譯文集[M].張文杰,編.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2:51.
[11]南帆.交匯與互動(dòng):文學(xué)、歷史、記憶[J].東吳學(xué)術(shù),2015(4):21-30.
On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Huang Guoqin’s
Prose Collection A Chronicle of Chaozhou
HUANG Huan-hu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Huang Guoqin holds a deep sense of identity with Chaozhou culture. His prose collection A Chronicle of Chaozhou is characterized by both a rich regional cultural flavor and a broad perspective spanning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H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language use in prose writing,employing a combination of vernacular and classical Chinese to exhibit its primitive simplicity. Through the rational arrangement of four-character phrases,varied sentence lengths,and parallelism,his writing is both refreshing and musical,effectively achieving a unity of content and form. In chronicling the city,Huang Guoqin uses vivid literary language to harmonize literature and history,providing a three-dimensional narrative of Chaozhou’s past and present.
Key words:Huang Guoqin’s prose;A Chronicle of Chaozhou;linguistic features;regionality;cultural prose
責(zé)任編輯 姚則強(qiáng)
收稿日期:2023-06-08
作者簡介:黃歡歡(1998-),女,浙江金華人,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
①沈從文:《〈七色魔(魘)題記〉》,原載昆明出版的《自由論壇》周刊第3卷第3期,1944年11月1日,轉(zhuǎn)引自解志熙《沈從文佚文廢郵鉤沉》,見《考文敘事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文獻(xiàn)校讀論叢》(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