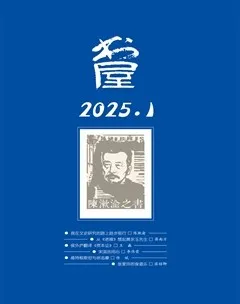老舍在重慶“跑警報”
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重慶大轟炸”。有時候,一天用一兩百架飛機來轟炸重慶;有時候,用三五架,甚至一兩架,從早至晚施行“疲勞轟炸”。“五三”、“五四”大轟炸震驚中外,“六五”大隧道慘案導致重慶兩千五百多名無辜百姓窒息死亡。抗戰時期,“跑警報”成為大后方獨有的一番景象,也是老舍在重慶的日常生活必修課之一。
日寇進攻武漢后,老舍攜“文協”總會印鑒,與何容、老向、肖伯青一道乘船駛向重慶。“盧溝橋事變”后,老舍離妻別子,逃離齊魯大學的一幕再次上演。正如老舍所言“我由青島跑到濟南,由濟南跑到武漢,而后跑到重慶”。老舍在重慶工作生活了近八年,作為“文協”總務部主任,組織并參加文藝界抗敵救國活動,表現出極大的愛國熱情和民族意識。同時,他還創作了眾多文學作品,為全民抗戰努力宣傳。
“五四”大轟炸來臨時,多日未曾出門的老舍正在趕寫劇本《殘霧》。連日的空襲未曾打斷他的工作。當天下午,周文、宋之的和羅烽找他商談“文協”工作。沒多久,防空警報就響了。對此,老舍已經習慣了,他不慌不忙到院中觀察一番后,又返回屋中繼續談話。一個小時后,防空警報再次響起。這時,大家才離開房間到地洞中躲避。在“跑警報”時,老舍還不忘把未完成的劇本《殘霧》緊緊抱在懷里。晚上七時,警報解除,他才從洞里慢慢地出來。對于當晚大轟炸的慘狀,老舍在《“五四”之夜》中這樣描述:“不錯,這晚上有月;可是天空的光亮并非月色,而是紅的火光!多少處起火,不曉得;只見滿天都是紅的。這紅光幾乎要使人發狂,它是以人骨、財產、圖書為柴,所發射的烈焰。灼干了的血,燒焦了的骨肉,火焰在喊聲哭聲的上面得意的狂舞,一直把星光月色燒紅!”
老舍看到“火光中,避難男女靜靜的走,救火車飛也似的奔馳,救護隊服務隊搖著白旗疾走;沒有搶劫,沒有怨罵,這是散漫慣了的,沒有秩序的中國嗎?像日本人所認識的中國嗎?這是紀律,這是團結,這是勇敢——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養,在火與血中表現出它的無所侮的力量與氣度”。他痛惜“那美麗的建筑,繁榮的街市,良善的同胞,都在火中”,但他也相信,“燒得盡的是物質,燒不盡的是精神;無可征服的心足以打碎最大的侵略的暴力”。這些文字有著很強的畫面感,老舍之所以能夠寫出這樣的文字,是因為親身經歷,感觸極深。大轟炸炸毀的是磚瓦土木之城,而在火光與廢墟中升騰的是眾志成城的民族抗戰意志,而重慶也在大轟炸中一遍遍浴火重生。
此外,老舍還在《八方風雨》中記錄大轟炸:“前幾天,我在公共防空洞里幾乎憋死。人多,天熱,空襲的時間長,洞中的空氣不夠用了。‘五三’、‘五四’我可是都在青年會里,所以沒受到什么委屈。‘五四’最糟,警報器因發生障礙,不十分響;沒有人準知道是否有了空襲,所以敵機到了頭上,人們還在街上游逛呢。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我在夜里跑到馮先生那里去,因為青年會附近全是火場,我怕被火圍住。徹夜,人們像流水一般,往城外搬。”
頻繁的“跑警報”,一是讓他得了盲腸炎,二是讓他創作了不少的“抗戰人名詩”。關于盲腸炎,他在《八方風雨》中這樣記載:
三一年夏天(筆者注:應為三十二年),我又來到了北碚,寫長篇小說《火葬》,從這一年春天,空襲就很少了;即使偶爾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慶那樣跑許多路。
哪知道,這樣一來可就不再動了。十月初,我得了盲腸炎,這個病與瘧疾,在抗戰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價米,里面有許多稗子與稻子。一不留神把它們咽下去,入了盲腸,便會出毛病。空襲又多,每每剛端起飯碗警報器響了;只好很快的抓著吞咽一碗飯或粥,顧不得細細的挑揀;于是盲腸炎就應運而生。
因為要“跑警報”,老舍慌忙之中將“平價米”中的稗子和稻子吃進肚子。由此可見,“跑警報”是導致老舍得盲腸炎的罪魁禍首。
10月4日,老舍疼痛難忍,不得不去重慶北碚江蘇醫學院附屬醫院割盲腸。有趣的是,老舍的胃有些下垂,盲腸也因此挪了地方。對此,老舍幽默地說:“盲腸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來似的。”最后,一名叫劉玄三的醫生花了三個鐘頭才把老舍的盲腸找到,做了切除手術。“經過還算不錯,只是外邊的縫線稍粗(戰時,器材缺乏),創口有點出水。”因老舍身患“貧血癥”和痢疾,又常常“打擺子”,再加上營養不良,他在醫院待了十七天,直到10月20日才出院。
為了躲避日機轟炸,老舍有時不得不從市區跑到鄉下。對此,他這樣記錄:“三十年夏,疲勞轟炸鬧了兩個星期。我先到歌樂山,后到陳家橋去住,還是應馮先生之邀。”其間,他還完成了劇本《歸去來兮》、論文《略論文學的語言》。
因為“跑警報”,老舍經常要在防空洞中躲避,有時一躲便是一整天。因時間太久,洞中空氣渾濁,大家在洞中百無聊賴,無所事事。為了消磨時光與排遣苦悶,他提議大家拿文藝界的人名來寫詩。于是,“人名詩”應運而生。因“人名詩”多與抗戰有關,故又被稱為“抗戰人名詩”。對此事,吳組緗曾在《老舍幽默文集·序》中回憶:“在重慶最無聊的是空襲中躲防空洞的時候。常常進了洞就出不來,久久悶坐著,無以自遣,后來我們就拿文藝界的人名拼湊詩句。”五律《憶昔》《野望》等“人名詩”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誕生的。
“也頻徐仲年,火雪明田間。大雨冼星海,長虹穆木天。佩弦盧霽野,振鐸歐陽山。王語今空了,紺弩黃藥眠。”《憶昔》一詩由十六個人名組成:胡也頻,作家、左聯烈士;徐仲年,詩人、文學翻譯家;火雪明,《時報》編輯;田間,現代詩人;孫大雨,現代詩人、文學翻譯家;冼星海,音樂家;高長虹,現代詩人;穆木天,現代詩人、翻譯家;佩弦即朱自清,著名作家;盧冀野,詩人;鄭振鐸,文學史家、作家;歐陽山,作家;王語今,著名翻譯家;薩空了,編輯、記者;聶紺弩,詩人、劇作家;黃藥眠,文學家、詩人。整首“人名詩”自然工整,無幾人工雕琢痕跡,詠史抒懷,沛然一氣,有情有景,詩意、詩境天然渾成。
“望道郭源新,盧焚蘇雪林。烽白朗霽野,山草明霞村。梅雨周而復,蒲風葉以群。素園陳瘦竹,老舍謝冰心。”《野望》一詩對仗工整,語言形象,精練含蓄,詩境優美,突顯出老舍深厚的舊體詩創作功力。據吳組緗回憶,他在躲防空洞時出了上聯“梅雨周而復”,老舍寫信以“蒲風葉以群”句相對,精確且工整,可謂一絕。老舍自幼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曾師從方還和宗子威學習古典詩詞多年。他常說“我的詩是學陸放翁與吳梅村”。陸放翁和吳梅村詩詞中的語言文字、詩情詩境、憂國憂民思想及禮儀觀念深深滲透在他的腦海里。后來,這些“人名詩”被吳組緗加上《與抗戰有關》的總題目,發表在《新蜀報》副刊《蜀道》上。
與古代“人名詩”不同,老舍的“人名詩”不是把人名鑲嵌在詩中,而是全部用人名連綴成詩,作家的名字是詩歌構成的唯一元素。其間,不用襯字連接,名字也不跟其他文字搭配成句,且少用雙關。老舍用人名作詩,抒發了對美好田園生活的向往,而人名卻隱藏在詩中,渾化無痕。胡絜青曾評價老舍,“愛把友人的名字,嵌入詩中,作為文字游戲,這些游戲詩是他的拿手好戲”。
經過老舍、吳組緗等人的倡導,“人名詩”成為一種與抗戰有關的自覺的文學活動,流行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的重慶。文藝界當年在重慶戲作“人名詩”成風。田仲濟、姚蓬子、艾青、王冶秋及西南聯大馮友蘭、容庚等文化名流紛紛響應。就連郭沫若也寫下:“胡風沙千里,凌鶴張天翼。白薇何其芳,麗尼顧而已。”對此,田仲濟認為:“重慶有的作家用人名詩拼成似通不通的五言詩,借以說明來解悶作家們講真話所造成的苦悶空氣。”為躲避日機轟炸,文人們在狹小的防空洞中大發詩興,并以人名入詩,寄情抒懷,這不僅是詩人們苦中作樂與釋放生活壓力的方式之一,還是他們交流詩藝及交游唱和的良好契機。“這種人名詩,老舍不認為只是無聊消遣,說這也體現著文藝界大團結,彼此不存畛域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