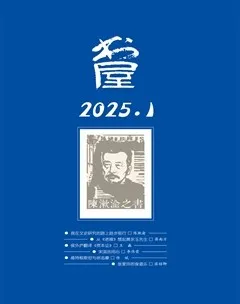重讀《祝福》
《祝福》寫于1924年2月7日,3月25日發表在《東方雜志》上,后收入小說集《彷徨》。其中,對人世毫無眷戀的祥林嫂,既逃不出魯鎮人締造的思想囚籠,也擺脫不了自身的精神禁錮,自始至終都沒有質疑夫死不能再嫁這一“從一而終”傳統禮教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這同樣也是朱安的可悲之處,處于時代轉型與夾縫中的女性,自身從未想過脫離窒息無愛的婚姻,去尋求自己的生活。
在《祝福》中,“我”在河邊遭遇來自祥林嫂的“靈魂拷問”,祥林嫂希望“我”能夠解答她內心的困惑。祥林嫂捐門檻,一則希望一如從前對于主人有價值,憑借自己的勞動重拾個體尊嚴;二則希望死后不被鋸開,與賀老六、阿毛團聚(可以理解為祥林嫂本也相信世間有魂靈)。雖然魯鎮人從不叫她老六嫂,當取笑她最后從了賀老六時,祥林嫂卻笑了,說:“阿阿,你……你倒自己試試看。”這是小說里唯一一次描寫祥林嫂談起家人時笑的情形。祥林嫂作為自然人的情感歸屬一直被掩藏被遮蔽,然而毋庸置疑,祥林嫂作為一個普通人,一生中得到的尊重與愛護、生命的光亮與溫暖只短暫存在于同賀老六結婚生子的那幾年。祥林嫂對再嫁的抗拒,新婚夜頭上撞得鮮血直流與婚后的幸福生活構成強烈的對比張力。1956年,夏衍將《祝福》改編成電影,著力渲染賀老六以真誠、善良感化誓死不嫁的祥林嫂,極力鋪陳祥林嫂與賀老六婚后的幸福生活,當然這樣的改編有夏衍的想象成分,也從另一方面強化了祥林嫂結局的悲劇性,但不可否認其改編的合理性。
祥林嫂并非恐懼可怕的死后世界,也不是怕“死后受苦”。祥林嫂第一次來到魯鎮“兩頰卻還是紅的”,但做工毫不松懈,掃塵、洗地、殺雞、宰鵝、徹夜煮福禮,繁重的工作反倒讓她覺得滿足,口角漸漸有了笑影,說明祥林的去世與這段婚姻傷痕很快被撫平。小說中祥林嫂兩次出現白胖了,第一次是在魯鎮做工時,第二次是衛老婆子講述她嫁給賀老六生兒子后,用衛老婆子的話是“母親也胖,兒子也胖”。可以想象賀老六是疼惜祥林嫂的,衛老婆子講述賀老六“所有的是力氣;會做活,房子是自家的”,驚嘆祥林嫂“現在是交了好運了”。賀老六曾將祥林嫂帶往幸福的彼岸,祥林嫂與賀老六應該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作為單親媽媽,祥林嫂“打柴摘茶養蠶都來得”,再次來到魯鎮,“兩頰消失了血色……眼角上帶些淚痕”,很明顯,祥林嫂對第二段婚姻傾注的感情與對新生活的渴望還原了其作為自然人的情感屬性,日復如斯的勞作與貧窮艱辛的生活不曾壓垮祥林嫂。生前嫁了兩次,死后不能歸于一家,不能完全歸于賀老六,構成祥林嫂真正的精神苦楚,也成為隱含在文本中的祥林嫂的深層悲哀。生命中最有價值的東西(賀老六與阿毛)被毀滅,造成祥林嫂精神與生活的雙重困頓,在小說后半部分,祥林嫂整個記憶都停留在兒子阿毛被吃的那個春天。祥林嫂聽了柳媽的話決定去捐門檻,小說沒有描寫祥林嫂的心理活動,怕死后下地獄被分成兩半只是精神表征,祥林嫂真正怕的是死后不能和賀老六、阿毛團聚。捐門檻,其實也是為了死后的“圓滿”,與生前的孤獨凄涼構成對比。
魯迅在1923—1924年思考女性的出路問題,小說中“我”對祥林嫂那種希望遠離的冷淡,但又于心不忍,作家對人物的感情頗為復雜。祥林嫂不斷向他人重復自己的悲慘遭遇,有如魯迅在《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寫到的“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祝福》不厭其煩地描寫祥林嫂反復述說個人經歷遭到眾人的唾棄與厭惡。祥林嫂博得他人同情的方式,在朱安身上也發生過。孫伏園回憶,在北京時,魯迅母親壽誕,開席前朱安穿戴整齊向親友下了一跪,說道:“我來周家已許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會離開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指魯迅母親)。”說完話,叩了頭,退回房去。魯迅說:“中國的舊式婦女也很厲害,從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爭取了去,大家都批評我不好。”張鐵錚曾將孫伏園這番話相詢周作人。周作人回答說,這是實有的事,朱夫人在家中是得到大家的同情的。
朱安始終沒有想過脫離與魯迅的婚姻,走不出自我的人生設限。魯迅曾對朱安提出結婚要求:進學堂,放足。但這兩項朱安和朱家人均未兌現。后來,俞芳在回憶錄中稱,因紹興之地風俗,若朱安被休棄,會和祥林嫂一樣的結局。但周建人的回憶錄《魯迅故家的敗落》卻提到,母親魯瑞在接到魯迅從日本的來信后放足。周建人還提到,在祖父去世后,買進來的潘庶祖母毅然與本家斷絕關系,然后與人成婚。因此俞芳的提法有待商榷。祥林嫂再嫁與被驅逐是夫權、族權所為,這一層面同朱安不一樣。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魯迅搬出八道灣,給朱安的建議是:可以繼續留在八道灣,如從前在紹興時一樣和大家庭生活;也可以回紹興去,(魯迅)每月供應生活費。魯迅與巴金一樣習慣做家長,故而朱安不會遭遇祥林嫂的命運。值得注意的是,同是紹興,秋瑾生于1875年,朱安生于1878年,但兩人境遇截然不同,紹興臺門的頑固正彰顯秋瑾的偉大,于是有了《藥》。
處于新舊交替時代的女性,有些人沖出藩籬,有些人故步自封。朱安自己畫地為牢,祥林嫂亦如此。禮教給個體戴上枷鎖,尚有可能卸去;但個體墨守成規,則與這副枷鎖融為一體。這是女性更大的悲哀之處,亦是魯迅思考女性問題的精神旨歸。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用在祥林嫂、朱安身上,多少也適宜。朱安這樣一個舊式人物,和魯迅無法進行文學、思想、社會等方面的交流,背后寓示著的正是舊社會女性的普遍遭遇。祥林嫂對阿毛、賀老六記憶的反復咀嚼,不正如同朱安對幸福家庭生活的向往嗎?《翦商》里說,商朝人用人祭祀祖先,不是讓人牲一下子死的,要讓他們持續慘叫而死,原因是祖先喜歡聽……同樣,魯迅在小說中如此寫實,如同祥林嫂的一場獻祭,祥林嫂成了魯鎮的“多余人”和一個著名的喻體,意在驚醒國人。
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里提出《祝福》后半部分用的是單媽媽的故事構架,但祥林嫂性格與外貌極可能以朱安為原型。俞芳的《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回憶朱安“臉色微黃……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綢裙……平日寡言少語,少有笑容”,這與祥林嫂的外形類似。祥林嫂第一次到魯鎮“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年紀大約二十六七,臉色青黃……只是順著眼,不開一句口,很像一個安分耐勞的人……”朱安在1906年同魯迅結婚,和祥林嫂差不多年紀;1923年,朱安四十五歲;《祝福》寫于1924年,小說中祥林嫂死時四十多歲。祥林嫂外形的變化,照應了朱安從成婚到1924年近二十年的變化。檜山久雄說,魯迅正是因為對朱安的罪障感而寫了《祝福》。姜異新在《“吶喊”之后的“重壓之感”——〈祝福〉細讀》中認為,“祥林嫂身上其實是有朱安的影子在的”。謝有順也認為,“比如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完全是虛擬人物,但讀完《祝福》,你會覺得她比魯迅的夫人朱安還真實”。
魯迅在《我之節烈觀》中提到,在境遇上不愿守節的女人做了乞丐,也竟求乞無門,終于慘苦不堪而死。作家沒有將祥林嫂圈定在一定時空中,第一次從夫家出逃的祥林嫂,猶如出走的娜拉,來到魯鎮當傭人。可以構想,一個山里人到魯鎮,恰如朱安從紹興到北京。一些研究者認為,如果朱安嫁給普通人,可能擁有幸福的生活。科舉制度取消,下聘后朱安等待魯迅七年,二人才成婚,自然與魯迅一拖再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關,但其看好魯迅日本留學的“洋功名”也是原因之一。然而婚姻的“門當戶對”不只在于器物層面的契合,更有精神層面的并立。1948年朱安去世,3月24日北平《新民報》刊出《朱夫人寂寞死去》一文,文中言:“父母愛之不啻若掌上珠,因而擇婿頗苛,年二十八始歸同郡周君豫才……”如果所述真實,從一開始便注定了朱安凄風苦雨的一生。
張鐵錚的《知堂晚年軼事一束·魯迅原配朱安女士》提到朱安何以多年不生育,周作人指出“朱夫人有侏儒癥,發育不全”;郁達夫的《回憶魯迅》也提及訪問魯迅家時,看到矮小的朱安。試想沒有生育能力,在傳統社會,嫁與何人都將處境艱難,甚至可能滑入比和魯迅結婚更不幸的境地。朱安接受許廣平和周海嬰,是出于心胸寬大、傳統女性美德,還是不為人知的無法生育的原因,難下定論。
朱安與魯迅的婚姻悲劇對當代女性依然有著警示意義。朱安等舊式女性習慣在自我付出中自我感動并失去自我,在魯迅兄弟失和后,朱安提出一同搬到磚塔胡同,理由是“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可以做……”。魯迅亦是如此,維持大家庭和不幸婚姻,直至兄弟失和,“我”對祥林嫂同情與批判兼有的矛盾復雜心態,折射出的恐怕正是魯迅與朱安的現實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