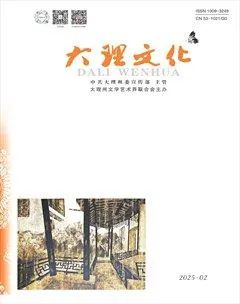大唐天空下的漾濞風云
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作為當時世界的中心,政治、經濟、文化都處于領先地位。這個中國歷史上波瀾壯闊的大時代,同樣是以洱海地區為中心的云南歷史上最曲折生動、最輝煌燦爛、最令人懷想不已的南詔時期。盡管隨著青藏高原吐蕃王朝的崛起,南詔政權一度中斷了與唐王朝的政治隸屬關系。但這并不影響云南與祖國內地日益加強的經濟文化聯系和相互交流學習的總趨勢,也不影響云南各族人民對漢文化圈的政治歸屬感和文化認同感,更不影響云南作為祖國多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員,以及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所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或缺的歷史性貢獻。
當時被中原人談之色變、視為“蠻煙瘴雨”之地的“漾水濞水”——也就是今天漾濞彝族自治縣區域,作為南詔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大唐天空下不僅同樣上演了波瀾壯闊的政治、軍事風云,而且創造了以民族文化為“內核”的絢麗多彩的地方文化。特別值得深入探討的是,作為古代滇西北的交通要道,當時的漾濞充分發揮了溝通東西方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交流的橋梁作用,為各民族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的彼此交流學習、相互吸引融合,進而為促進云南邊疆與祖國內地的各方面聯系,加強云南各族人民對漢文化圈政治歸屬感和文化認同感,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隋朝恢復經略云南之漾濞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起疆域廣闊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封建制國家,為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朝發巴蜀兵征云南,擊滅滇國(今滇池周邊)東北的勞浸、靡莫等“西南夷”部族,滇王率眾臣服。漢武帝在云南設立了益州郡,郡治設在新設立的滇池縣(今昆明晉寧)。此后數年之間,漢朝軍隊又先后兩次征服昆明部族,占有今云南中西部的廣大地區,并在今大理地區設置了云南、葉榆、比蘇、邪龍4縣,歸益州郡管轄,漾濞為邪龍縣所屬。至此,郡縣制推廣到云南。
隋開皇九年(589年),隋文帝滅南陳,結束了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中原近400年的分割局面。而在奪取北周政權建立隋王朝后不久,楊堅就下決心解決云南邊疆地區的統一問題。隋開皇四年(584年),隋王朝在味縣(今云南曲靖三岔一帶)設置南寧州總管府。次年(585年),隋朝任命韋沖為南寧州總管,統兵鎮守南寧州。以爨震為代表的云南各族部落首領紛紛到南寧州總管府拜見韋沖,表示愿意歸附朝廷,爨震被朝廷任命為昆州刺史。但一方面由于韋沖為首的朝廷官吏橫征暴斂、兇殘無道,甚至“掠人之妻”,致使“邊人失望”;另一方面爨氏并不甘心就此失去過去長期稱雄云南的局面,甚至企圖考驗一下隋王朝征服云南的決心和實力。
隋開皇十五、十六年(595- 596年),爨翫(爨震之子)為首的爨氏發動了武裝叛亂。隋朝派兵鎮壓,爨翫投降,隋朝仍委其為昆州刺史。不久爨翫再次反叛。隋文帝派大將史萬歲率兵征討。史萬歲揮師長驅直入,橫掃爨翫勢力盤踞的云南各地,其中包括洱海地區和漾濞江流域。爨翫又一次向隋軍投降。“萬歲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賂萬歲以金寶,萬歲于是舍翫而還”(《資治通鑒》隋紀二),并沒有將其押往京城。史萬歲返回內地之后,爨翫發動第三次叛亂。隋文帝大怒,在嚴懲受賄縱敵的史萬歲的同時,再次派劉噲、楊武通出師云南進行討伐,俘虜了爨翫,押入長安處死,其子爨宏達也被押入內地降為奴。爨氏統治區域縮小到建寧、晉寧地區。隨后,因隋朝忙于征討北方高句麗等國,便“棄其地”,僅僅根據云南各部族的分布勢力范圍而設置了大大小小的羈縻州,任命各部族首領為刺史等官職進行羈縻統治。
隋朝以史萬歲為代表的將領對云南的一系列軍事征討,極大地打擊了爨氏在云南的勢力。盡管由于史萬歲的貪贓受賄和隋朝形勢變化而未能實際加強對云南的治理,但爨氏雄踞云南數百年的局面已被徹底摧毀。可以說,史萬歲征云南是中原王朝在失去對云南的實際控制數百年之后,所采取的一次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行動。它雖然未能最終實現中央政權對云南的實際統治,卻從根本上削弱了稱雄云南一方的爨氏地方割據勢力,將云南重新納入中原王朝版圖。最重要的是,給云南再次帶來并進一步強化了中原地區以儒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思想為根本內核的漢族文明文化和政治思想意識。
對于洱海地區來說,隋王朝對云南的數次軍事行動,特別是史萬歲征云南時,率領浩浩蕩蕩的內地大軍,深入滇東北地區圍剿爨氏控制下的部落武裝,不僅沉重打擊了云南以部落為主的地方割據勢力,而且給這些“藏在深山,隱匿密林”、生活于幾乎與世隔絕的高山峽谷的封閉部落,帶來了祖國內地較為先進的生產技術、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觀念等新鮮的東西。倘若從歷史的縱深角度考察分析,史萬歲為代表的隋朝軍隊,對云南的一系列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可以說是繼三國時期諸葛亮南征之后,中原王朝對云南,以及對以洱海地區為中心,包括漾濞江流域在內,也包括永昌(今保山)的滇西地區,又一次廣泛深入地傳播了中原漢族文化文明和思想意識。
通過這種幾乎是暴風驟雨般的沖擊和洗禮,以中原漢族文明為核心的先進的、優勢的政治思想意識、生產技術和文化觀念,再一次廣泛深入地傳播到西南邊疆地區,并在這些地區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進而深刻地影響、改變和推動了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進步,同時極大地增強了中原地區的漢族文化和文明對邊疆地區與當地民族的吸引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正是在這種基礎上,西南邊疆地區和各族人民,對中華文明的“仰慕”“向往”,特別是對漢文化圈價值觀的認同,日益深入人心,進而不可逆轉地形成了完全認同以儒家為代表的“大一統”思想、意識和觀念,并成為包括漾濞江流域的邊疆和民族的共同意識。
作為后來漾濞縣域的范圍,也就是以“漾濞江”流域和“南方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穿越的地區為中心區域的“一江兩路”地帶,既是當年史萬歲大軍的必經之地和主要戰場之一,也是受史萬歲大軍自身攜帶的內地漢族文明和文化沖擊最大和影響最深遠的地方之一。因此自古以來,雖因地理環境比較遙遠閉塞、仿佛僻處一隅、總是“藏在深山人未識”,甚至被中原地區想當然地認為是“蠻煙瘴雨”之地的漾濞,由于占盡古代云南滇西北交通要道的“天時”“地利”“人和”優勢,往往能夠獲得“風氣之先”,及時跟上時代的腳步。所以,歷來并不顯得與滾滾向前的歷史激流脫節,還常常走在時代的前面。
唐初強化云南治理中的洱海地區
隋大業十四年(618年),李唐王朝建立,立即著手恢復隋初在云南施行的舊制。唐高祖李淵釋放了爨翫兒子爨宏達,讓他帶著裝殮爨翫尸體的棺木返回云南安葬,并任命他擔任昆州刺史,又由益州刺史派俞大施與之同至云南,重置隋煬帝廢棄的南寧州。接著,巂州都督府先后派遣吉弘偉和韋仁壽到洱海和滇池地區招撫,任命韋仁壽為檢校南寧州都督,在該地區設置了16州。這些措施無疑對中央王朝加強在云南的管理起到積極的作用。但這些措施大體仍未脫離“羈縻”之法,或者“授其豪帥為牧宰”,或者“歲一至其地以慰撫之”,或者“寄治益州”,或者“寄治越巂”,并未能在云南普遍建立直屬中央的地方政權系統。
唐太宗李世民時,朝廷在云南的郡縣設置有較大的發展。李世民標榜“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98,卷199《唐紀》15)。把南寧州都督府移到味縣(今曲靖),積極開展對云南各部的招撫,又命梁建方率兵平定松外(今永勝、華坪一帶)各部貴族的叛亂,于是前來歸附者有松外70部、109300戶,其中就有漾濞所屬的“西洱河”首領楊盛及東西洱海各部。
從武德年間到貞觀年間,唐朝先后在今天云南境內設置了許多羈縻州縣,設置南寧州都督府。到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廢棄了南寧州都督府,設置姚州都督府,(駐今楚雄姚安),后又設安南都護府(駐今越南河內)和戎州都督府(駐今四川宜賓),三個府就近統轄云南境內的羈縻州縣。這樣唐朝初步恢復了漢晉中央王朝在云南設置郡縣的規模。
然而,遠離唐王朝統治中心的云南,特別是山高皇帝遠的洱海地區,仍然處于部落“各擅山川,互不統屬”的分裂狀態。唐太宗、唐玄宗時代,朝廷銳意于經略疆土,不能接受云南長期成為“化外之地”的事實。不斷采取軍事手段與政治措施,將云南置于中央政權的直接控制之下。但因為種種原因,一直難有突破性進展。唐玄宗時代,為了與南下的吐蕃勢力爭奪洱海地區的控制權,唐廷不得不放棄原來在洱海地區推行的“以夷制夷”平衡政策,開始采取支持親唐的部落統一洱海地區以穩固西南的戰略策略。當時洱海地區的六個較大部落,也就是史書上被稱為“六詔”的區域性政權中的蒙舍詔(南詔)一直堅持奉唐朝為正朔,比較親唐,雙方各取所需,所以唐朝一直比較支持南詔。
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738年),皮邏閣在張建成的建議下厚賂劍南節度使王昱,請求合“六詔為一”。王昱向朝廷代請,得到唐玄宗允許。接著皮邏閣在唐王朝的支持和幫助下對周邊地區發動了一系列的兼并戰爭,先后消滅了其他五詔,建立起以洱海地區為中心區域的南詔政權,皮邏閣被封為云南王。在這一重大歷史演變過程中,作為漾濞原來所屬的蒙巂詔,以及蒙巂詔衰落后代替蒙巂詔的“樣備詔”(漾濞詔)的興亡,則是在這一重大歷史推進中的重要篇章。
贊普都松芒布結殞命漾濞
唐朝初期對云南經略進展比較明顯,云南也出現了相對穩定的形勢。可惜這種相對穩定的形勢,不久就被我國西部奴隸主勢力推動下崛起的吐蕃打亂和改變。
公元7世紀中葉,贊普松贊干布統一了青藏高原,建立起強盛一時的吐蕃王朝,定都邏些(今拉薩)。隨后吐蕃王朝與唐王朝開始了長達百年的爭奪戰爭。在北方與唐王朝爭奪安西四鎮(今新疆、甘肅境內),在東南方先后占領了云南洱海地區和四川的鹽源一帶。大唐調露二年(680年),吐蕃攻占了安戎(今四川汶川西南)后,控制了唐朝通往“西南諸蠻”的道路。從此吐蕃與唐朝在洱海地區展開了激烈的、反反復復的長期爭奪戰爭。直到唐貞元十八年(802年),韋皋俘獲吐蕃將軍論莽熱,至此由盛轉衰的吐蕃,才不再構成對唐朝的威脅。但此時唐王朝也國力耗盡,迅速走向了衰落。
在此之前,唐王朝為了強化對云南的治理,對云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唐高宗在設置青蛉(今楚雄大姚)、弄棟(今楚雄姚安)兩縣的基礎上,開設姚州都督府,每年由四川派兵500人戍守,統一指揮云南各部落抗御吐蕃的斗爭,先后擊敗蒙巂詔主,也就是唐王朝任命的陽瓜州(今巍山北部和漾濞)刺史蒙儉等親吐蕃勢力的進攻,爭取到浪穹詔主傍時昔率所屬25部歸附。短短時間,洱海地區“歸附者日以千數”,鹽源地區各部也相繼來降。
當吐蕃勢力南下的時候,洱海地區作為唐王朝抗擊吐蕃的西南戰線的南翼戰線,由于親吐蕃力量的不斷分化,大大削弱了吐蕃在云南的勢力。唐朝及吐蕃對洱海地區的爭奪也進一步激烈起來。
武則天垂拱元年(685年),唐王朝在對洱海地區失控多年后,再置姚州都督府,爭取洱海地區臣屬吐蕃的各部落。武則天垂拱五年(689年),原來歸附吐蕃的浪穹詔主傍時昔(又名豐時,屬烏蠻。)率所屬二十五部背棄吐蕃,歸附唐朝。唐王朝立即任命傍時昔為浪穹州(今洱源)刺史,“令統率其眾”。方國瑜教授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吐蕃侵占至浪穹時,夾在唐朝與吐蕃勢力之間的浪穹詔主傍時昔,為了生存和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巧妙周旋于唐、吐之間,兩面應付,既接受唐的封號,又接受吐蕃的支配。這是因為駐扎在浪穹的吐蕃軍隊對這片區域的控制,不是唐朝政治招徠所能削弱的。
武周長壽三年(694年),洱海地區首領董期率所屬部二萬戶歸附唐朝。姚州都督府爭取洱海地區親吐蕃勢力的工作十分順利,洱海和四川鹽源地區各部落相繼歸附唐朝,吐蕃的南翼遭到巨大的失敗。為挽救這一不利局勢,不愿甘拜下風的吐蕃,對洱海地區發動了又一輪大規模的進攻。這次是由贊普都松芒布結親自掛帥出征,決心一舉拿下滇西地區,控制南方絲綢之路,切斷唐王朝與“天竺”等國的對外聯系通道,以奪取更大的政治經濟利益。
武周長安三年(703年),吐蕃贊普都松芒布結親自統領大軍征戰洱海地區,先是攻下絳域(麗江)地區,接著揮師南下。吐蕃軍隊越接近洱海地區,受到親唐部落的抵抗越激烈。武周長安四年(704年),吐蕃軍隊再次降服三浪詔(即浪穹、邆賧、施浪)后,沿今天的洱源喬后、煉鐵一線,順黑潓江而下,并越過烏鞘箐,長驅直入樣備詔(蒙巂詔后身)的漾濞江流域。此時的樣備詔,在蒙儉反唐失敗后,已經不得不接受親唐的蒙舍詔勢力的控制和支配。吐蕃軍隊進軍洱海地區的過程中,一路受到當地部落武裝的激烈抵抗,激烈抵抗的當地部落武裝中就有原來靠攏吐蕃的蒙巂詔主蒙儉的后代。正可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吐蕃軍隊在漾濞江流域的戰斗中,屢屢遭遇到當地部落武裝的襲擊,甚至連其最高統率都松芒布結贊普也戰死在此。
都松芒布結,又名赤都松贊,《新唐書》作器弩悉弄,有時還被稱為“棄都松”,系松贊干布曾孫,吐蕃王朝第35任贊普,生年不詳,公元676年至704年在位。為吐蕃王朝最強盛時期的國王。藏史曾記載其“年雖幼沖,刀砍野豬,以腳絆拴扣野牛,抓提虎耳”等異行。藏史評價都松芒布結說,除沉深謀慮以外,加以武藝精湛,圣明遠超天下一切君王,庶民黔首齊上尊號曰“神變之王”,是吐蕃馳騁疆場、能征慣戰、勇猛強悍、所向披靡的一代雄主。都松芒布結贊普率部沿漾濞江一路浩浩蕩蕩南下,在今漾濞石門關一帶被伏擊受重傷而殞命。一代豪雄最后竟然大船翻覆于小溪,喪身于漾濞這種籍籍無名的荒山野地。究其原因,大概是都松芒布結太麻痹大意,壓根兒就不將沿途地方部落武裝放在眼里,以為這些烏合之眾是騰不起大浪的小泥鰍。
殊不知因蒙儉反唐失敗后,不得不率領殘兵敗將,從巍山壩子逃到漾濞江流域,并在今天已經融入縣城的蒙官村重新建立詔所茍延殘喘,名稱也由蒙巂詔改稱“樣備詔”的武裝,也是一支驍勇善戰、久經沙場的隊伍。如前所述,此時的樣備詔,在形勢所迫下,不得不由吐蕃的盟友變成了吐蕃的敵對勢力。因而當不顧兵家大忌,親自帶領少數親兵輕騎的都松芒布結,冒險前來深入狹隘險峻的石門關一帶觀察地形時,當即遭到熟悉當地山川地勢的樣備詔武裝的伏擊,僻靜的石門關峽谷一時亂箭齊放,殺聲震天,猝不及防的都松芒布結,當即中箭落馬,雖被親兵拼死救回,終因傷勢過重,數日后在軍中不治身亡。
之后,吐蕃軍隊雖然占領了自古兵家必爭之地漾江流域和西洱河流域,且在漾濞江、順濞河的兩條江河上修建了兩座鐵索橋,并在橋頭建碉樓等據點駐軍把守。但都松芒布結贊普的陣亡,使吐蕃軍士氣大受影響,其“東占洱海,南取永昌”的宏偉計劃也只能暫時擱淺。吐蕃軍隊護送都松芒布結靈柩歸葬于西藏芒松芒贊陵之左側,稱“拉日堅”陵。而在今天離石門關六七公里遠的地方,有一座歷史悠久的叫普光寺的寺院,寺院大雄寶殿中所供奉有一尊西藏喇嘛模樣的睡佛,相傳就是贊普都松芒布結的化身。據普光寺已故的劉紹周老居士口述,解放前每隔幾年,就會有藏區的僧侶信眾不遠千里,前來普光寺朝拜供奉此尊睡佛。
雖然都松芒布結的陣亡重挫了吐蕃軍隊的銳氣。吐蕃勢力卻并未退出洱海地區。此時的漾濞再次被吐蕃勢力控制。唐神龍元年(705年),唐朝攝監察御史李知古上書朝廷:“姚州諸蠻(即“西洱河諸蠻”)先附吐蕃,請發兵擊之。”朝廷便命令李知古征調劍南兵前來西洱河地區,也就是大理洱海地區進行討伐。李知古在洱海地區“筑城堡,列州縣”,擺出一副要與吐蕃長期對壘的架勢。遺憾的是李知古是一個頭腦簡單、行為粗暴、不懂謀略,又好大喜功的缺乏政治智慧的武夫。他不但橫征暴斂,加重洱海地區人民的稅賦,而且還誅殺他先前已經接受其投降的鄧賧詔主,把他的子女罰作奴婢。于是引起其他“豪酋”——當地部落首領的恐懼和怨恨,他們相率反叛,并引吐蕃兵攻殺李知古,斷其尸祭天。
李知古被洱海地區的“蠻酋”聯合吐蕃殺死后,洱海地區又變成了吐蕃的勢力范圍,致使“姚巂道閉不通者數年”。
“唐標鐵柱”中的漾濞往事
唐中宗景龍元年(707年)重新歸附吐蕃的部分姚州部落與吐蕃軍隊聯合進犯四川南部。
為平定“西洱河諸蠻”的叛亂,打通姚巂道,鞏固姚州都督府對洱海地區的統治,唐王朝下詔靈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征為姚巂道討擊使,率軍征討吐蕃。唐九征在姚州(今楚雄姚安)大破吐蕃軍隊和“西洱河諸叛蠻”。接著又乘勝追擊,將吐蕃軍隊一舉趕出了洱海地區。吐蕃敗軍逃出下關天生橋,沿著相傳三國時期諸葛亮第七次擒獲孟獲的“天威徑”,也就是蒼山西坡博南古道和茶馬古道之路向滇西北方向潰逃。唐九征繼續跟蹤追擊,史書載“累戰皆捷”,“俘其魁帥以還”。
這次唐王朝軍隊同吐蕃軍隊的一系列激烈戰斗中,漾濞是其中的重要戰場之一。在今天漾濞江峽谷的平坡至縣城一帶,吐蕃軍隊憑借險要的地勢和堅固的城壘,同唐軍激烈對峙,戰斗打得異常慘烈,雙方傷亡都很慘重,無數的唐軍將士和吐蕃士兵戰死在這片狹長的河谷地帶,此地一時血流成河、尸積如山。最后,唐朝軍隊終于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吐蕃“魁帥”(軍隊統帥)帶領殘余人馬棄城奔逃,唐軍繼續緊追不舍,一直追到永昌(今保山)一帶,活捉了“魁帥”及其三千部屬才凱旋班師。
唐九征擊潰吐蕃軍隊后,為了切斷吐蕃與洱海地區的道路,恢復秦漢以來中央王朝在洱海地區的統治,不僅焚毀了吐蕃在今天漾濞縣城附近建筑的城壘,還下令拆除漾濞江、順濞河上的兩座鐵索橋。當唐九征凱旋之際,為了“紀功”,更為了表明這片美麗富饒的土地已重新納入了大唐王朝的版圖,同時也為了紀念和撫慰在這場戰斗中為國捐軀、長眠于這片被當時中原人談之色變的所謂“蠻煙瘴雨”的蠻荒之地的唐軍將士,他便依仿東漢以來相沿成襲的做法——漢光武帝劉秀派伏波將軍馬援率軍平定了交趾(今越南境內)叛亂,并在其地立銅柱紀功,作為漢朝最南方的邊界——把拆卸下來的鐵索橋的鐵鏈和鐵板作為材料鑄煉成鐵柱,立于今天漾濞縣城附近的竹林寺一帶“紀功”。
根據史籍記載,當時吐蕃在“西洱河”(洱海地區)之勢力,是以浪穹(今洱源)為根據地的。方國瑜曾經深入考證說,唐九征擊敗吐蕃于漾濞江,阻斷其通西洱河之路,也就是通過今下關天生橋進入龍尾關的道路,然而未必就攻克浪穹,浪穹仍被吐蕃所占據。其依據是“至天寶十載鮮于仲通出兵攻南詔時,《南詔德化碑》說‘贊普觀釁浪穹’”,由此則可知浪穹仍“為吐蕃前哨陣地”。
從隨后洱海地區狼煙四起的“六詔爭雄”過程中,不難看到吐蕃在洱海周邊地區的重大作用和深刻影響。而唐王朝之所以鼎力支持蒙舍詔吞并洱海地區其他五詔,就是為了要利用其來制衡吐蕃的。然而迅速崛起的南詔政權,隨著軍事實力的不斷增長,政治野心也與日俱增。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南詔統治集團充分利用自己所處的特殊地緣優勢構成的政治軍事優勢,反復依違于唐王朝與吐蕃之間。他們在與唐王朝發生矛盾和沖突的時候,往往依吐蕃以自重,不斷威脅警告唐王朝,倘若將我逼急了,我就靠向吐蕃一邊。如第一次天寶戰爭時,閣羅鳳就遣使對率大軍前來興師問罪的鮮于仲通威脅說:“今吐蕃大軍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反之亦然。
由此可見,吐蕃勢力一直都存在于洱海地區周圍,并時刻虎視眈眈地窺伺著洱海地區。進一步說,唐九征擊敗吐蕃班師后,由于他并沒有將吐蕃勢力徹底趕出洱海地區的周邊范圍,漾濞的戰略地位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漾濞這個小小的彈丸之地,仍然是夾峙在先是唐王朝與吐蕃,后是南詔與吐蕃之間的一個關鍵要塞和前沿陣地,也是唐王朝勢在必得的內地通往“天竺”之道,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軍事價值和交通價值。
唐九征所立的“唐標鐵柱”,作為唐王朝實際經略云南的標志和象征,歷來受到史家的重視,以至有人這樣形容說:“‘唐標鐵柱’的實質意義就像是一把鎖,它的具體位置在哪里,即意味著當時大唐的統治疆域和勢力范圍實際上就已經延伸到達了哪里。”
事實也是這樣,唐九征立“鐵柱”的目的,除為了“紀功”和“撫慰”陣亡在當地的唐軍將士外,還具有界碑的作用。據記載,建造鐵柱時,在柱身和基座上都鐫刻有疆界地圖、地理情況、戰爭概況。“唐標鐵柱”事件發生很多年后,吐蕃與唐朝爭議“蠻中”即洱海地區的權屬問題。唐德宗便反復以“唐標鐵柱”上州圖、地記為依據,來證明洱海地區早就歸屬唐王朝。唐九征在此立鐵柱為界碑,把漾濞江以東的廣大地區重新納入唐朝統治管轄范圍,與唐初西南局勢相吻合。
“唐標鐵柱”戰事是唐王朝與吐蕃在西南邊疆爭奪戰爭中最輝煌的一次勝利,它有效遏制了吐蕃勢力的擴張,穩定了唐初西南邊疆的政治軍事局勢,推進了西南各民族的團結和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進程。而且與過去的征討相比,這次軍事行動,更進一步深入到洱海流域等滇西北地區。總而言之,諸葛亮、史萬歲、唐九征等先后遠征云南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使中央王朝的實際統治自東而西深入云南,最終影響云南全境。為隨后南詔的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
唐九征是一位對云南歷史和西南邊疆歷史都產生過深遠影響的重要歷史人物。唐九征對漾濞的影響,更是無法回避和繞過的。當年他揮師窮追猛打吐蕃虎狼之師,一舉在漾濞江畔擊潰吐蕃軍隊的赫赫戰功,并在當地豎立集“紀功”和“標界”為一體的“鐵柱”的舉措,使漾濞第一次彪炳史冊,至今仍閃爍著耀眼的光芒。
隨著“唐標鐵柱”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載入了《大唐新語》《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重要歷史典籍,也使“漾濞”二字在史籍中熠熠生輝,而且還為漾濞贏得了一個世界之最。這就是《大唐新語》卷十一所記載的“時吐蕃以鐵索跨漾水濞水為橋,以通洱河”的“鐵索橋”,被長期致力于中國科技史研究、被譽為“20世紀的偉大學者”的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1900~1995年)所著的《中國科技史》考證為全世界關于“鐵橋”見諸于文字的最早記錄。
唐王朝與吐蕃博弈中的漾濞
唐王朝和吐蕃之間曾經展開了長達百余年的激烈爭奪戰爭。這場曠日持久的爭奪戰,關系到唐朝政權的生死存亡。因為吐蕃向東擴張,不僅西北邊陲不得安寧,連中央王朝也受到重大威脅;吐蕃入犯蜀西及西洱河地區,又使唐朝西南邊疆的安全面臨嚴重危機。
為了避免前后方都被動挨打的局面,唐王朝必須在洱海地區抗擊吐蕃,并與西北方面相配合,形成對吐蕃的反包圍。因此,鞏固姚州都督府就成為保衛唐王朝全局戰略的重要舉措。要鞏固姚州都督府則必須依靠和借助洱海諸部落的力量。可以說洱海諸部落的“向背”問題,小而言之關系著姚州都督府的命運,大而言之維系著大唐王朝的安危。為此,姚州都督府的首要任務,就是隔斷吐蕃與洱海諸部落的聯系,招撫他們,使之與自己站在同一條戰線,共同抵御吐蕃勢力的進攻。
如前所述,為保衛姚州和抗擊吐蕃,唐王朝于公元707年派監察御史唐九征為姚巂道討擊使,率領大軍深入到洱海地區與吐蕃決戰并大獲全勝,立鐵柱于蒼山西坡的漾濞縣城附近的竹林寺一帶,以紀念這次戰役的輝煌勝利。但這次戰爭的勝利,也并未徹底改變洱海地區諸部落對唐王朝時叛時附的局面,因為安戎城和昆明城(鹽源)還為吐蕃所控制。于是,奪回這兩座城池成為唐朝爭奪洱海地區的當務之急。之后,又經過了4次戰爭,兩城終于又回到了唐朝手中。吐蕃曾多次派兵反攻,皆失敗而去,兩城的收復,不僅鞏固了唐王朝在西南地區的統治,也為南詔的興起創造了條件。
在唐王朝與吐蕃長達百年的博弈中,洱海地區始終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唐朝的眼里,洱海地區既是“通向天竺”的對外交通要道,更是拱衛內地的重要安全屏障和包圍吐蕃勢在必得的戰略要地。而在唐朝初期洱海地區唐王朝與吐蕃的爭奪戰中,作為洱海地區的西大門,也是吐蕃東進控制洱海地區,西退返回青藏高原重要通道的西洱河流域和漾濞江流域,軍事地位自然非常重要,一直成為雙方反復激烈爭奪的焦點。由于唐朝初期,在洱海地區的爭奪拉鋸戰中,唐王朝一方處于守勢,因此西洱河流域和漾濞江流域曾長期被處于攻勢的吐蕃一方占據,成為雙方對峙的前哨陣地。
實際上,當時夾雜在唐王朝和吐蕃中間“各擅山川、互不統屬”的處于分裂狀態的洱海地區眾多部落,為了生存和自身的利益,不得不見風使舵地周旋于唐王朝與吐蕃兩大勢力中間,誰強大就站隊誰,或者說誰對自己有利就依附誰。甚至不只在謀取自己的生存機會的關頭,就是在僅僅為了攫取某種利益的時候,他們都經常會將唐朝或吐蕃當作自己向另外一方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
吐蕃當時在漾濞江和西洱河狹谷地帶的活動,除史書明確記載的吐蕃曾經在“漾水濞水”修筑城壘和鐵索橋外,歷代的稗官野史也有不少蛛絲馬跡可尋。至今在漾濞平坡西洱河東岸,還有一個名叫白塔箐的地方,民間口碑資料說此地名的來源,就是由于在遙遠的古代,原來吐蕃的藏民曾在此建立過一座白塔。歷經千百年的風吹雨打,這座代表吐蕃信仰和文化特征的白塔,早已經在歷史變遷中滅失得了無痕跡,但白塔箐地名一直保留下來。
世道滄桑,殘陽如血。正如孫髯翁《大觀樓長聯》的不勝感慨:“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盡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不過唐九征曾經在漾濞江邊所豎立的“鐵柱”,盡管也逃不脫“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的命運,但從某種角度上講,它不僅對于云南歷史的發展有著非同尋常的影響和深遠的意義,就是對中國歷史進程和邊疆的開發而言,亦不失為一個意味深長的歷史符號……
從蒙巂詔到樣備詔的衰亡
蒙巂詔曾經是初唐時期洱海地區最大的部落,后來名稱被樣備詔取代,最后為蒙舍詔吞并。
《通典》卷一百八七“松外諸蠻”條曰:“其西洱河,從嶲州千五百里,其地有數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這就是說在隋末唐初,在洱海地區存在著眾多部落。這些“各據山川,不相役屬”的部落之間,為了爭奪土地、財物和人口,動輒刀兵相見,不斷發生沖突和戰爭。經過長期相互拼殺和兼并,逐漸演變為六個較大的部落,被稱為“六詔”。“詔”意為首領、國王,“六詔”就是六個部落的首領,同時指六個部落。
“六詔”之名號,《新唐書·南詔傳》曰:“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賧詔、施浪詔、蒙舍詔。”樊綽《云南志》卷三曰:“蒙巂一詔最大。”又卷五曰:“蒙舍北有蒙巂詔,即楊瓜州(一作“陽瓜州”)也,同在一川。”所謂“同在一川”,即這兩個詔同在一個平壩,而蒙巂在蒙舍之北,蒙舍在今巍山(蒙化)城區,則蒙巂在今巍山北部之地,有陽瓜江流貫之。方國瑜在《兩爨、六詔地理考釋》中說:“樊綽《云南志》稱蒙巂為最大,則今巍山西北之漾濞亦應為蒙巂之地。蓋五詔所領不過數十里,而蒙巂獨廣也。”方國瑜進一步指出竇滂《云南別錄》無蒙巂詔,有樣備詔,疑“樣備”即“蒙巂”,因在漾濞江邊而得名,“樣備”即“漾濞”之諧音字也。漾濞江之名已見于劉肅《大唐新語》,即今之漾濞也。
蒙巂詔在洱海地區最大詔的地位沒有維持多久,就被蒙舍詔,也就是后來的南詔所取代。而之所以發生這一重大變故,則與吐蕃勢力進入洱海地區有關。公元七世紀下半葉,從青藏高原迅速崛起的吐蕃政權,為了與唐王朝爭奪政治、軍事利益,開始南下遠征洱海地區,由此拉開了唐王朝與吐蕃地區長期兵戎相見、互相攻伐的序幕。當時洱海地區的眾多部落,根據各自的地理位置和利益關系,有的親附唐王朝,有的靠攏吐蕃。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唐王朝以李義為姚州道總管,統率軍隊征討洱海地區的眾多少數民族部落。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三月,當時姚州所轄,而且被唐廷封為陽瓜州刺史的巂部落首領蒙儉,實際上仍然依附于吐蕃。蒙儉與和舍相互勾結叛亂,他們引誘其部落首領柳諾沒弄、楊虔七部一起反對唐王朝,糾集起二十萬部眾,浩浩蕩蕩向姚州進攻。朝廷令唐朝太子右衛梁積壽帶領五千五百人征討,大獲全勝,斬殺柳諾沒弄、楊虔等。
逃脫后的蒙儉與和舍等又糾集殘余部屬,命令其強悍將領夸干率部反撲,卻再次被打敗,夸干本人亦被斬殺。唐軍乘勝追擊,斬首七千余級,獲馬五千余匹。走投無路的和舍等首領,只得將自己捆綁起當面向唐軍請求投降,此次洱海地區的部落叛亂被平定。而遠道而來、人生地不熟的梁積壽率領的區區五千多人的唐軍,面對占盡“天時”和“地利”的當地數倍的部落武裝,之所以能夠以少勝多,甚至輕而易舉就將其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除了“反叛”聯盟乃是草草拼湊起來的烏合之眾,不僅裝備差、缺乏訓練外,更說明“反叛”唐朝是不得人心的,因此士氣低落,軍無斗志。與其說這些部落武裝大多數是被唐軍消滅的,不如說他們是自行作鳥獸散的。
蒙巂詔也沒有被徹底剿滅,唐王朝可能出于“制衡”戰略考量,有意讓蒙儉及其長子儉轉叟逃脫,也就是史籍所載的他們父子兩個“脫身挺險,負命窮山”——即退守“樣備”了事。因而才使他們得以在漾濞江流域再建立“樣備詔”。不過蒙巂詔和由其演變來的樣備詔從此走上了無可挽回的衰落敗亡之道。
蒙儉反唐不論是對唐王朝、云南邊疆和洱海地區,還是對蒙巂詔而言,都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點。這個轉折點,不僅導致了洱海地區部落勢力重新洗牌,而且還左右了唐王朝對經略洱海地區的政策走向,其影響是極其深遠的。蒙儉等反唐的原因比較復雜。一方面是受到他們所親附的吐蕃的鼓動、慫恿和唆使,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唐王朝派駐云南的官吏令人不堪忍受的貪酷暴政,以及他們對一系列的政策和舉措處置失當有關,致使邊人失望。還有一個背后深層次的問題,也就是蒙儉等部落頭領自我膨脹的因素。他們或許以為云南與內地山重水復,距離遙遠,加上地理和氣候存在巨大差異。他們在此稱王稱霸、為所欲為,唐王朝根本拿他們沒辦法。但無論如何,蒙儉等部落首領無疑是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和錯誤的對象發生了一場后果異常嚴重的沖突,從而葬送了自己,使自己輸得連卷土重來的機會都沒有,最后不得不黯然退出了歷史舞臺。
從后來歷史發展的走向上看,蒙儉等反唐失敗對唐王朝初期經略云南,無疑是一個標志性的重大事件,這個事件直接的后果不僅讓蒙巂詔失去了洱海地區最大詔的地位,只得退守漾濞江流域,而且標志著唐王朝原來在洱海地區推行的“以夷制夷”平衡戰略徹底宣告失敗,轉而全力支持蒙舍詔統一洱海地區,以對抗日益強大的吐蕃勢力搶占云南的戰略意圖,為后來南詔的崛起創造了可遇不可求的重大歷史機遇。也為云南數百年的歷史走向埋下了伏筆,進而直接影響,甚至還可以說是決定了中國唐宋歷史的演變方向。
蒙儉反唐失敗所謂的“脫身挺險,負命窮山”,就是退出巍山壩子,將其勢力范圍收縮到漾濞江流域,同時將詔府遷移到今天已經融入漾濞縣城新城區的蒙光村。
蒙光村原名蒙官村,坐落于漾濞江西岸,前臨波浪滾滾的江水,背后是層層疊疊的高山密林,東邊是沙河,西邊是柏木鋪河。這兩條河水由于氣候變化,如今流量、水勢已經不甚浩大,但在那遙遠的一千多年前,前面波濤洶涌的江水和左右水流湍急的兩條河流卻構成了此地的天然屏障。因此這個東西狹長三公里的平曠河谷地帶,是那個時代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險要所在。
蒙巂詔遷移到漾濞江流域不久,蒙儉即憂憤身亡,其政權在蒙光村前后茍延殘喘了62年,而在有關史籍中的名稱,也逐漸被與漾濞音同字異的“樣備詔”所代替。此后樣備詔又經歷了5個詔主后,這個當年在巍山壩子強盛一時,顧盼自雄的洱海地區“第一大詔”,因蒙儉的一念之差產生的致命錯誤,最后被原來“同處一川”和“同一姓氏”的后起之秀蒙舍詔所滅。
按(明)諸葛元聲《滇史》、(清)倪蛻《滇云歷年傳》等史籍的記載,從蒙巂詔演變而來的樣備詔的滅亡過程大致是這樣的:其王巂輔首死,無子,弟佉陽照繼位;佉陽照死后由兒子照原繼位;照原在位的具體時間不明,大約處于唐玄宗時期。照原后來失明,當時其子原羅在南詔當人質,南詔王歸義(皮邏閣)欲吞并樣備詔,把原羅放還樣備詔,國人立原羅為王。數月后,南詔指使人殺死照原,驅逐原羅,吞并了樣備詔。至此,由蒙巂詔演變而來的樣備詔徹底退出了歷史的舞臺,成為今天漾濞這塊土地上的一樁歷史往事。
從歷史發展的規律和趨勢上看,南詔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發動兼并戰爭統一洱海地區,進而建立起包括西南邊疆大部分地區在內的強大地方性政權,不僅是唐王朝抗擊吐蕃軍事威脅的需要,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和進步,客觀上有利于洱海地區經濟文化發展和民族融合。
尤其是對由蒙巂詔演變而來的偏處一隅的“樣備詔”而言,被南詔吞并后,減少了過去部落之間那種動輒刀兵相見的無休無止的戰爭,以及所造成的對漾濞江流域經濟發展的破壞和給當地百姓帶來的痛苦。不僅如此,漾濞還成為南詔的核心疆域地區之一,也成為南詔政權的經濟政治和宗教文化涵蓋的重要中心區域。
特別是當后來南詔崛起為疆域廣大,即包括云南及與云南交界的今四川、貴州、廣西及東南亞部分地區的強盛一時的地方政權時,漾濞不僅為南詔的西大門,不僅是南詔聯系永昌(今保山)、越賧(今騰沖)、尋傳(今緬甸密支那東北一帶)等諸部疆域的橋梁,而且也肩負著溝通與緬甸中部古驃國,以及古印度等對外交通樞紐的重任,發揮著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的重要作用。大食(今阿拉伯帝國)、波斯(今伊朗)、天竺(今印度)等地的珍珠商貨,幾經輾轉,源源不斷地通過漾濞境內的古道流向四川以及內地。
唐詩中的漾濞
唐代內地著名詩人,有多人到過云南。如唐咸亨三年(672年),西南邊陲的姚州(今云南楚雄姚安一帶)發生戰亂,隨軍入滇參加平叛到過姚州,也極有可能還到過洱海地區和永昌(今保山一帶)地區,并留下唐初內地著名詩人描寫云南的第一首詩《從軍中行軍難》的作者駱賓王。倘若駱賓王到過永昌地區,那么他一定到過漾濞江流域。因為漾濞江流域,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無法繞過的必經之地。
由于漾濞江流域地處云南古代交通要道,是歷史上溝通東西方文化的南方絲綢之路的咽喉所在。所以,唐朝時由于種種不一的原因,有幸同云南結緣的內地著名詩人,大都到過漾濞江流域,如以書記員身份跟隨唐九征討伐吐蕃的初唐后期著名文士、與陳子昂和杜審言齊名的閭邱均,又如被稱為“大雅不群,遠投蠻徼,亦空谷足音也”的苦吟詩人賈島等等。
這些背井離鄉、漂泊四方的行旅之人奔走在滇西這片崖高箐險、虎嘯猿啼的逶迤驛道上,艱難輾轉行走在人煙稀少、景象迥然不同于內地的“蠻煙瘴雨”之地時,自然難免觸景生情,多感多懷。特別是在這里駐足歇宿或流連漫步、觀風賞景的詩人學者們,往往會雅興勃發,有的飲酒賦詩,遣興抒懷,有的作文記游,留下他們對這方風土人文的觀感和文化足跡。可惜時過境遷并歷經千百年的大浪淘沙后,留存下來的作品已經寥寥無幾。這里介紹其中幾位唐代內地詩人吟誦漾濞山川風物的作品。
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唐代內地著名詩人吟詠漾濞的,共有4位詩人的5首詩。其中前兩首是晚唐時期因“蜀中戰亂”被攻克成都的南詔軍隊所擄,流落云南的成都詩人雍陶所寫的。其中名氣較大、為《永昌府文征》等諸多地方文獻收錄的是《哀蜀人為南蠻俘虜五章·入蠻界不許有悲泣之聲》,其詩云:
云南路出洱河西,毒草長青瘴色低。
漸近蠻城誰敢哭?一時收淚羨猿啼。
從詩人一行所走的“路出洱河西”的路線和方向上推斷,詩中所吟詠的“蠻城”,就是今天的漾濞古城。也就是說,詩人離開大理洱海往西經過下關天生橋,沿著西洱河往滇西邊地走了一程又一程,遠遠地望見一座城池——即坐落于漾濞江邊的漾濞古城,也就是詩人謂之的“蠻城”,更加膽戰心驚起來,只得含悲忍淚,不敢啼哭號泣,只能羨慕漾濞江兩岸高巖峭崖間,可以毫無顧忌地自由自在聲聲鳴啼的猿猴。其背景是由于當年唐王朝和南詔之間連年征戰攻伐,雙邊的百姓都深受禍害,難免造成了內地與邊疆地區因血雨腥風的戰亂和長期隔絕所造成的深刻的民族隔膜和隔閡。尤其是雍陶這位被戰爭擄入南詔的飽經憂患的詩人,自然早已系驚弓之鳥,因而見到前邊出現的漾濞城池,反而擔驚受怕,憂心忡忡起來,也是不難理解的。
除著名的《哀蜀人為南蠻俘虜五章·入蠻界不許有悲泣之聲》一詩外,雍陶還在漾濞石門關留下了另一首題為《宿石門山居》的詩,同樣以準確真實、細膩生動的筆觸表達了背井離鄉的詩人,作為愁緒滿腹的天涯孤旅,思鄉思親、心神不寧,以及漫漫秋夜輾轉難眠的惆悵情懷和凄涼感受。其詩曰:
窗燈欲滅夜愁生,螢火飛來促織鳴。
宿客幾回眠又起,一溪秋水枕邊聲。
第三首是唐咸通五年(864年)七月,被唐懿宗任命為安南都護、經略招討使以抵御南詔對安南地區的侵略的高駢,在征戰南詔的過程中途經漾濞時所寫的《過天威徑》詩,其詩曰:
豺狼坑盡卻朝天,戰馬休嘶瘴嶺煙。
歸路崄巇今坦蕩,一條千里直如弦。
詩所詠的“天威徑”,前邊已經提到,就是后來的“關漾驛道”和“關永驛道”,也就是大理市下關天生橋至永平之間的“南方絲綢之路”的重要地段之“博南古道”。相傳此處的漾濞平坡西洱河和漾濞江河谷一帶,是諸葛亮設計第七次智擒孟獲,孟獲終于向諸葛亮表示臣服說:“丞相天威,南人不復返了”的地方,因此被稱為天威徑。
高駢率軍靖邊,輾轉于深林盲壑、絕崖狹蹊的天威徑,也就是下關天生橋至漾濞平坡之間的險峻山谷,不禁緬懷起漢丞相諸葛孔明前輩“豺狼坑盡卻朝天”的“以夷治夷”的高明的安邊謀略,即“豺狼坑盡”后,沒有留下一兵一卒戍邊,便班師回朝。因為孟獲大王已被其“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心戰”降服,率“豺狼之兵”歸順蜀漢政權。從此,蜀漢政權不用再派兵馬征戰于“蠻煙瘴雨”之地的高入云表的西南崇山峻嶺。這位節度使踏上當年蜀漢軍曾戰斗過的險峻歸途時,遂感嘆如今千里如弦的古驛道,已經坦蕩無阻了。
第四首就是跟隨高駢征戰南中的池州(今屬安徽)詩人顧云留下的《天威徑行》一詩。其詩曰:
蠻嶺高,蠻海闊,去舸回艘投此歇。
一夜舟人得夢間,草草相呼一時發。
颶風忽起云顛狂,波濤擺掣魚龍僵。
海神怕急上岸走,山燕股栗入石藏。
金蛇飛狀霍閃過,白日倒掛銀繩長。
轟轟砢砢雷車轉,霹靂一聲天地戰。
風定云開始望看,萬里青山分兩片。
車遙遙,馬闐闐,平如砥,直如弦。
云南八國萬部落,皆知此路來朝天。
耿恭拜出井底水,廣利刺開山上泉。
若論終古濟物意,二將之功皆小焉。
此詩所說的“蠻嶺高,蠻海闊”中的“蠻嶺”和“蠻海”,分別就是指“天威徑”東側的蒼山和“天威徑”起點背后的洱海。
第五首,也是跟隨高駢征戰南詔的崔致遠所作《七言記德詩三十首謹獻司徒相公天威徑》:
鑿斷龍門猶勞身,擘分華岳徒稱神。
如何劈開海山道,坐令八國爭來賓。
在唐朝燦若星空的詩人中,崔致遠是一個獨特的歷史存在和文化現象。他的身份和經歷都與眾不同。崔致遠,字孤云,新羅末期人,是朝鮮國歷史上第一位留下了個人文集的大學者和著名詩人,一向被朝鮮和韓國學術界尊奉為朝鮮半島漢文學的開山鼻祖,有“東國儒宗”“東國文學之祖”的稱譽。他12歲時離家來到長安求學,在中國一共待了16年時間,前面的七、八年是在長安、洛陽求學,后半期則先后在溧水(今南京市溧水區)、淮南為官,約8年多時間。崔致遠28歲回新羅,在新羅王朝繼續擔任要職。
唐僖宗廣明元年(880年),崔致遠入幕揚州高駢門下。次年5月,高駢起兵討伐黃巢,崔志遠擬就的《檄黃巢書》,天下傳誦,并憑此獲“賜緋魚袋”勛位。檄書中一句“不惟天下之人皆思顯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議陰誅”,言辭之峻切凌厲,令一代豪雄黃巢都心生怯意。崔致遠的《七言記德詩三十首謹獻司徒相公天威徑》詩,就是他跟隨高駢征戰南中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