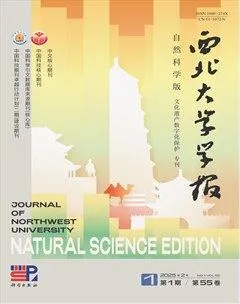基于機載激光雷達的復雜環境空間考古調查方法







摘要 機載激光雷達作為一種主動遙感技術,可在復雜環境中有效感知地表或淺地表遺跡信息。然而因成本和技術因素,目前在大規模考古調查中仍不普及。基于棱鏡式半固態機載激光雷達技術設計了一套涵蓋數據采集、處理和考古分析的一站式激光雷達空間考古調查方法,在滿足激光雷達數據精度要求的同時,降低了考古工作者學習和應用的難度,并以南陽地區古代城址調查為例,在各種復雜的遺跡賦存環境中進行了試驗。實踐表明,該方法能夠高效、高質量地完成復雜賦存環境下的考古遺跡信息獲取與感知,為考古調查和遺址保護監測等工作提供堅實的數據基礎,進而推動機載激光雷達在考古調查中的普及應用。
關鍵詞 機載激光雷達;空間考古;賦存環境;微地貌;數字考古
中圖分類號:K854.1" DOI:10.16152/j.cnki.xdxbzr.2025-01-012
Spatial archaeological surface survey method in complex occurrence environment supported by airborne LiDAR
TIAN Songlin1, QIN Gaomin1, QIAO Baotong2, WANG Wei2,XIAN Yiheng1, YU Chun1
(1.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Nanyang Institut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Nanyang 473000, China)
Abstract Airborne LiDAR, as an active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effectively perceives surface or shallow subsurface relic information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However, due to the cost and technical factors, it remains unpopular in large-scale archaeological survey. Based on prism semi-solid airborne LiDAR, we’ve designed a total spatial archaeological survey method encompassing data acquisition, processing, and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This method not only meets the precision requirements of LiDAR data, but also reduces the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difficulty for archaeologists. Taking the ancient city site survey in" Nanyang as an example, we tested this method across various cultural heritage occurrence environments, including vegetated areas, urban landscapes, and micro-topographical scen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is method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acquires and senses archaeological relic information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providing a solid data foundation for archaeological surveys, site protection monitoring, and related endeavors. Consequently, this method advances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airborne LiDAR in spatial archaeological surface survey.
Keywords Airborne LiDAR; space archaeology; occurrence environment; micro-topography; digital archaeology
三維數字化技術隨著科技發展已成為考古調查和發掘的重要方法之一[1]。機載激光雷達因其主動遙感的技術原理,可以獲取更豐富和精細的地面信息,在聚落考古調查與文物保護監測等領域發揮重要作用。考古人員通過激光雷達獲取點云,并借助一系列可視化工具得到遺址的數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和數字特征模型(digital feature model, DFM),結合考古學理論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和解釋,可深入開展聚落考古研究,拓展考古學研究的視野[2]。同時更精細的空間數據也為保護監測古代城址等不可移動文物提供了基礎和依據[3]。
近年來,棱鏡式半固態激光雷達在自動駕駛的發展下方興未艾[4]。相較于機械式線掃描激光雷達,棱鏡式半固態激光雷達結構緊湊、掃描模式多樣且高度集成,可在多種復雜工況中穩定獲取高精度數據。然而此方案在考古領域的應用相對較少,業界對其在復雜環境考古調查中獲取遺跡數據的有效性、質量和效率方面尚不明確。研究基于機載棱鏡式半固態激光雷達系統,在河南南陽對9個有著不同賦存環境的古代城址進行激光雷達掃描和可視化分析,旨在設計一套包含數據采集、處理、空間信息可視化與考古分析的一站式空間考古調查方法。該方法能在復雜的考古調查場景中更好地感知和識別古代城址結構,而且在低成本和便捷作業的前提下,可有效滿足大規模、精細化的空間考古調查與數字化文物保護與監測需求。
1 南陽古代城址及賦存環境特征
南陽盆地地處河南省西南部,北抵伏牛山,西靠秦嶺與大巴山,東為桐柏山。盆地內水系發達,自然條件優越,人文資源豐富,自古以來便是溝通南北交通的樞紐,也因此孕育了眾多的古代城址,其賦存環境[5]也存在差異。受多因素影響,南陽古代城址景觀變遷巨大:有些被植被覆蓋,有些因土地平整導致殘存遺跡被破壞,僅剩下微小的痕跡;更有一些城址與現代城市重合或者被包圍。復雜的賦存環境,直接影響研究者對古代城址空間信息的獲取與感知。傳統的考古調查方法,如航空攝影[6]、全站儀測量[7]等工作在面對復雜的遺址賦存環境時,存在無法獲取有效信息、工作效率低等問題。因此,激光雷達方案的出現,為解決類似問題帶來了新的可能。
為配合南陽古代城址考古調查工作,對9個具有代表性的古代城址進行了激光雷達掃描作業。9個城址分布在南陽各地(見圖1),賦存環境各不相同,主要包括植被覆蓋場景、城市場景和微地貌場景3種類型,基本涵蓋了城址考古調查中面臨的場景,可有效驗證棱鏡式半固態激光雷達在不同環境下是否具備有效、高效獲取考古空間信息的能力。
1.1 植被覆蓋場景
古代城址受環境、社會等因素的影響,并非永續使用。一些古城被廢棄后,容易引起植被覆蓋,一些關鍵的遺跡,如城墻、城門等地面設施因此受到植被遮擋。南陽市以平原為主,降水豐富,植被相對茂密,相當一部分古代城址被植被覆蓋,導致考古調查時難以通過常規手段獲取有效信息。9個城址地點中,金湯寨遺址、博望故城和圣井寺古城3處屬于該場景類型。
金湯寨遺址位于南陽市方城縣金湯寨村(見圖1,地點7),遺址核心區三面環水,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既往的田野工作和研究表明,該遺址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商時期修筑城墻,城址存續至宋代。該遺址目前地表殘存城墻年代最早可追溯到西漢,為夯土結構。古代墻體的上方有大量的植被覆蓋,航空和衛星影像僅能通過城外的河流觀察城址的大致邊界,無法觀察墻體結構和城址的詳細空間信息。博望故城位于南陽市方城縣博望鎮(見圖1,地點5)。西漢時期張騫被冊封“博望侯”于此,行政區劃歸屬南陽郡管轄,之后則長期作為縣級地方單位使用。遺址當前環境和金湯寨相似,城墻和城址核心區均存在茂密的植被覆蓋現象。圣井寺遺址位于南陽市方城縣小史店鎮(見圖1,地點9)。城址整體年代為隋唐至元代,城址中央還有一座廟宇。相較于金湯寨和博望遺址,圣井寺遺址城墻整體保存較為完好,四面城墻均高于地表,但北部的墻體被大量植被覆蓋,同樣需要通過激光雷達獲取植被下方的城墻結構數據,以便監測墻體當前保存狀態,為文物保護提供依據。
1.2 城市場景
古代城市的選址往往是自然和人文條件優越的區域[8],因此很多沿用至今。一些古城的遺跡結構雖然得到保留,卻難免被“淹沒”在高樓大廈之間。在考古調查中,傳統的攝影測量可能因為建筑物過于密集,難以有效測量古城遺跡結構的立體結構,同時因城市環境復雜難以開展貼近攝影測量作業。因此可以借助棱鏡式半固態激光雷達在非重復掃描模式下能獲取被測對象更多立體結構信息的特點,在建筑物密集的城市場景開展古城的高精度測量工作。激光雷達掃描的9個目標城址中,有3處位于城市中心。
方城遺址(見圖1,地點6)位于南陽市方城縣城市核心區。方城作為古代城址從漢代沿用至今,目前地表僅存西墻,墻體為夯土結構,帶馬面。這段墻體所處的位置東西兩側均為密集的現代建筑。阿婆城遺址(見圖1,地點1)和靳崗遺址(見圖1,地點4)的賦存環境與方城類似,均因城市建設導致古代城墻被現代建筑包圍,其中阿婆城遺址僅存的墻體東西兩側距離建筑物不足5 m,且墻體周圍還有植被覆蓋,環境更加復雜。
1.3 微地貌場景
微地貌是地理學的概念,一般是指起伏微小的地表形態[9]。微地貌雖然特征不明顯,但它往往揭示了潛在的地理趨勢在地質災害監測等領域廣泛應用[10]。古代城址在長時間保存中難免會因各種原因被破壞。一些城址的墻體或建筑可能較為堅固,不一定完全被損毀,留下了細微痕跡。這些痕跡通常表現為微小的地形起伏,即“微地貌特征”。古代城址的微地形特征一方面起伏較小,特征不明顯;另一方面由于農作物等低矮植被的遮擋,肉眼或者攝影測量更是難以察覺。在此研究中,同樣有3處城址的主要結構表現為微地貌特征,分別是梁城遺址(見圖1,地點8)、棘陽城遺址(見圖1,地點3)和光武遺址(見圖1,地點9)。其中梁城遺址(南陽市方城縣)和棘陽城遺址(南陽市新野縣)情況類似,兩處遺址的核心范圍為農田景觀,墻體也位于農田中,地表觀察基本無法判斷是否具有墻體殘留特征;而光武遺址通過航空攝影可大致觀察殘存的古城墻,但因墻體保存情況較差,仍然需要經過微地貌可視化處理才能更清晰顯示目前墻體的保存狀況和城址的空間特征。
2 機載激光雷達空間考古方法
2.1 機載棱鏡式激光雷達技術
考古調查中常用的激光雷達包含地面式和機載式兩大類[11]。地面式激光雷達主要通過車載、固定站等形式實現對目標物體的掃描,獲取地面及周邊一定高度內遺跡的高精度三維結構數據,可用于考古現場遺跡和遺物建模。但掃描面積小且視角較窄、架站難度大、數據高精度定位復雜等都是掣肘其進一步應用的因素。機載式激光雷達則是搭載于各類航空器平臺執行掃描任務。早期機載激光雷達體積龐大,需要有人機作為飛行平臺完成工作,操作復雜且成本高昂。近年來隨著小型無人機和棱鏡式半固態激光雷達技術的成熟,無人機載激光雷達為考古調查中應用此項技術提供了可行性方案[12]。相較于地面激光雷達,機載激光雷達掃描視角更大,可快速獲取大范圍遺址及其周鄰賦存環境的高精度地貌模型,配合微地貌可視化、點云語義分割[13]和分類等分析方法,可有效感知遺址整體空間特征及其與賦存環境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可有效獲取植被下方的遺跡信息,為復雜環境下的考古調查提供更翔實、高精度的基礎數據。
棱鏡式激光雷達是一種通過內置旋轉棱鏡實現多角度激光掃描的半固態激光雷達解決方案[14]。緊湊的結構使其在無人機平臺上得到了廣泛地應用。與傳統的機械式LiDAR相比,操作簡單,維護成本低。同時在掃描精度上可以達到64線激光雷達的效果。此外,棱鏡式半固態激光雷達支持非重復掃描模式,可獲取更多的立面信息,方便獲取遺跡的側面視圖。研究采用大疆M300RTK無人機掛載大疆Zenmuse L2機載激光雷達進行掃描。L2裝備了LIVOX棱鏡式半固態激光雷達模塊,每秒可發射24萬個激光點,接收5個回波。在機載RTK固定解模式下,L2獲取的點云數據平面精度達5 cm,高程精度約3 cm,可在旁向重疊率僅25%時獲取高精度地形數據。不僅如此,L2具有三軸云臺,可以有效抵消無人機飛行產生的振動且支持墻面等垂直面場景的掃描,更加穩定地獲取高精度、多視角數據。此外,L2支持后差分定位(post processing kinematic, PPK)功能,在無4G網絡覆蓋的區域,可通過后處理匹配云基站獲取高精度差分定位[15],進一步拓寬了高精度激光雷達的作業場景。
2.2 點云數據采集和處理方法
為確保數據精度,外業工作均采用航線模式。首先在地面站上設置飛行區域,此區域以遺址區為核心,向東西南北4個方向外擴100~150 m規劃一個矩形,確保激光雷達有效掃描面積大于遺址核心區,一方面是保證遺址邊緣的掃描精度;另一方面也同步采集遺址周邊景觀的地形數據,反映遺址賦存環境特征。為保證數據分辨率一致性,9個城址的激光雷達數據采集參數設置為5回波模式,航高125~130 m,航速9~10 m/s,激光掃描旁向重疊率25%。在此參數下,點云密度控制在約247~250 pts/m2區間內,經地面點分類后得到的地面點云密度約為190~205 pts/m2,可滿足制作分辨率為0.07 m的數字高程模型和數字特征模型[16]。
數據處理方面,L2采集的點云原始文件包含點云機內直出文件(LDR格式)、慣導數據、RTK數據和用于著色的照片,需經大疆智圖軟件的激光雷達點云模塊完成數據的預處理,獲得LAS格式的完整點云數據。預處理的核心為點云平滑和點云精度優化。其中點云平滑基于點云去噪算法[17],去除因環境干擾等因素采集的離散噪聲點,降低點云厚度,進而清晰呈現局部特征,提升點云質量;點云精度優化主要利用航帶平差[18]等方法,對多個架次和不同時段作業得到的點云數據進行優化,提升點云數據的一致性。這兩種預處理方法進一步提高了L2原始點云數據精度,可滿足后續點云分類、遺跡微觀地貌單元可視化等空間考古分析。
大疆智圖的點云預處理邏輯包含點云密度、點云處理和高級設置3個流程:點云密度主要是設置處理時的點云密度模式,可選擇百分比模式或距離模式。在考古調查中,一般選用百分比模式并設為100%,后處理時所有的點云均參與計算,數據精度最高;點云處理模塊則包括精度優化、點云平滑、地面點分類以及DEM和DFM制作。這里推薦開啟精度優化和點云平滑,軟件會對L2點云數據進行航帶平差和去噪,讓點云厚度更薄且拼接誤差更小。
地面點分類方面,大疆智圖預設了平地、緩坡和陡坡3種場景的地形場景,根據實際作業環境選擇合適的地面點分類場景以達到良好的地面點分類效果[19]。調查中掃描的所有的城址均采用“緩坡”場景執行地面點計算,僅需將“最大建筑物對角線長度”按實際情況修改即可。DEM與DFM生成也較為簡單,可直接設置分辨率或比例尺,本次研究中9個城址的DEM和DFM分辨率設置均為0.07 m,方便快捷處理的同時也具備較高的分辨率,可進行有效的遺跡細節特征判讀。最后一步則是高級設置,這一塊主要選擇合適的大地坐標與投影坐標,以及選擇是否需要合并多架次采集的點云。參考系設置按統一設置進行即可(WGS84/UTM49N),默認勾選點云合并選項以便生成完整的DEM。完成上述設置后,點擊“開始重建”,大疆智圖即可自動完成上述工作流,并輸出可供第三方地理信息系統讀取和分析的LAS點云和TIFF格式的DEM。需要注意的是,部分遺跡在點云分類時有可能被歸入“未分類點”而不參與生成DEM,導致最終圖像信息不完整,因此需要人工將其歸入“地面點”后才能生成反映遺跡地貌信息的DEM,進而制作專門表現城址遺跡的DFM。
2.3 點云數據可視化與考古分析
在提取點云的有效考古信息中,空間可視化方法[20]至關重要。山體陰影和暈渲地貌是點云數據可視化的兩種常見的技術方案。將采集的點云進行地面點分類和提取,再使用地面點數據集構建數字高程模型,插值方法為不規則三角網格[21],由此得到過濾了植被、地表人工建筑、車輛等信息的數字高程模型,經過山體陰影的方式,將古代城址遺跡結構清晰地還原出來并進行注記和解釋,制成一張反映微地貌遺跡特征的DFM[22]。面對微地貌場景,可增強山體陰影參數設置中的Z因子倍數(通常是5倍)實現更加清晰的可視化結果。另外,DEM/DFM可在三維地理信息場景中基于三維地形生成2.5維模型,即一種固定三維模型某個觀察方位輸出的圖像[23]。相較于真三維模型(如Mesh等),2.5維模型能反映遺址及其賦存環境地貌三維特征的同時支持探索性3D分析中的高程剖面分析,獲取古代城址重要遺跡結構的剖面信息,并與平面結構相結合,更全面地完成古代城址的空間感知與分析研究[24],并且便于演示和出版。不僅如此,2.5維圖的計算和生產所需的算力遠小于真三維模型,可進一步降低數據可視化的算力門檻。
考古分析方面,可根據數字特征模型所顯示的基礎上,運用地理信息標注工具,對疑似遺跡的位置進行標記。一般城址可使用點要素標記城址中心點以及城內重要設施的位置、線要素標記墻體、面要素標記建筑區域和城內功能分區,甚至在進階的三維地形分析中調用多面體要素進一步標記甚至重建古城內部的地面要素,如建筑、墻壁等[25]。完成標注后,即可結合地形分析工具和要素分析工具,對城址內部結構、城址與周邊賦存環境進行量測、空間關系分析等研究。在此基礎上可對目標城址的遺跡賦存環境情況、遺跡保存現狀進行評估,同時確定引起地貌異常的區域,為后續的考古勘探、發掘等精細化研究工作提供準確、完善的前置信息,同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導發掘方案,提升古代城址考古勘探和發掘的精細化程度[26]。
總之,基于機載激光雷達的空間考古方法可劃分為前置工作、數據采集和處理、空間信息可視化、考古分析解譯及實地驗證5個環節:①前置工作的主要是適應無人機新規中關于空域申報的要求,結合遺址具體情況制定專業合法的工作計劃[27];②數據采集和數據處理著眼于古代城址激光雷達數據的制作,目的在于得到可供主流地理信息系統所識別、感知和分析的通用數據;③空間可視化則是將離散點云數據轉化為以柵格數據為代表的通用地理圖資,如數字特征模型、數字高程模型,以便開展計算量更小,更便捷的柵格分析與計算;④考古分析和解譯則注重激光雷達調查的考古導向,將考古學的理論和遺跡判斷的方法應用于數據解譯和分析,進而得出符合考古學和文物保護監測需要的相關信息;⑤驗證與復查則是依據解譯的空間信息,積極開展實地復查、驗證,根據結果進一步優化可視化方案。通過要素標記、多源遙感數據對比、柵格和矢量疊加顯示等方法,著重表現已確定的遺跡區域,進而更高效地掌握大遺址的各類信息,有條不紊地開展考古研究和文物保護工作。
3 數據成果與分析
通過上述方法完成了9個古代城址的激光雷達掃描工作,得到了對應的數字特征模型。從數據質量看,9座城址的點云數據質量基本一致。點密度為125~133 pts/m2,生成數字特征模型的分辨率為0.07 m,滿足考古調查數據基本要求的同時保留更多遺跡細節。下面對棱鏡式半固態激光雷達在3種常見的遺跡賦存環境下獲取和解析遺跡形態的有效性進行討論。
3.1 植被覆蓋場景
根據實際情況,L2在植被覆蓋的場景下能有效獲取地面信息,采集古城墻體的結構數據(見圖2)。經過植被濾波后的數字特征模型顯示了博望故城西北側的墻體結構相對完好,但東部和南部基本不見城墻的結構特征〔見圖2(a1)、(a2)〕,僅能通過故城四周的河道大致判斷當時城址的最大范圍;金湯寨的城墻雖然大部分被村莊周邊的樹木覆蓋,但四周保存相對完好,可以準確識別出城址的范圍〔見圖2(b1)、(b2))〕,一些被茂密植被覆蓋的墻體在激光雷達的支持下也能被完整記錄,并經現場復查確認夯土城墻的存在;而在其東北角因河流侵蝕與現代建設,有部分墻體損毀。一些保存完好的古城,如本次調查的圣井寺古城,墻體上方有部分植被覆蓋影響了整體城墻的結構記錄,借助激光雷達的穿透性特征即可實現完整記錄〔見圖2(c1)、(c2)〕,無需人工地面全站儀打點測量林下遺跡高程,極大提升了城址考古調查的效率。
由于L2具有多回波特性,可接收最高5次回波。有效信息集中在哪幾次回波,是判斷棱鏡式半固態激光雷達在林下場景獲取考古信息能力的重要參考。以金湯寨城址整體點云〔見圖3(a)〕為例:首次回波〔見圖3(b)〕點云總數最多,但大部分點為植被最頂部的冠層表面和一些無植被覆蓋遺跡結構,林下墻體信息較少;第2〔見圖3(c)〕和第3次回波〔見圖3(d)〕主要采集樹木中間的冠層和部分地面信息,有部分墻體因上方植被相對稀疏,在2、3回波的點云中也包含它們的信息;第4次回波〔見圖3(e)〕基本上為地面點,記錄了大部分植被下方墻體信息。第5次回波〔見圖3(f)〕點云總數最少,單純依靠第5回波的信息無法建立有效的數字特征模型。綜合博望故城和圣井寺遺址的情況,L2在植被茂密的考古遺跡賦存環境下,遺址主體空間信息集中在1~2回波。而林下遺跡信息大部分包含在3~4回波中(見圖4),第5回波雖然點數較少,但在高密度植被場景中可以進一步感知林下信息,提升林下地面點數量,進而生成更高分辨率的DFM。表明5回波模式下可滿足大部分植被覆蓋場景下的考古遺址信息獲取和處理。
3.2 城市場景
城市場景在古代城址考古調查中較為常見。一般情況下城市場景中古代城址有兩種賦存情況。一種是古代城址的大部分結構位于現代都會區地下;另一種則是古城的一些重要的結構, 如城墻、 馬面、敵樓,因城市建設發展被現代建筑包圍。 棱鏡式半固態雷達無法獲取第1種情況下的遺跡信息, 而對于第2種, 則可以發揮非重復掃描的特征優勢,配合點云分類實現遺跡的準確提取和標記。 對阿婆城、 靳崗遺址和方城遺址3處古代城址進行掃描, 3處城址雖然均位于市區, 但具體情況有所差異。 阿婆城遺址殘存墻體和馬面位于城址核心區的西北角, 其殘存墻體四周不到2 m的范圍內有著密集的建筑物〔見圖5(a)〕,對墻體的側面形成遮擋。使用L2的非重復掃描模式,獲取了阿婆城西北角城墻和馬面的點云,并通過大疆智圖濾波后,點云數據清晰地展現了阿婆城西北側城墻和馬面結構〔見圖5(b)〕。
靳崗遺址的情況與阿婆城類似,殘存墻體分布在城址核心區西側,墻體東西兩側均為密集的居民區。數字表面模型因為同時顯示了古城墻、現代街道和建筑物等多種地物信息〔見圖6(a)〕而難以突出重點;而基于激光雷達掃描和點云分類提取后生成的DFM〔見圖6(b)〕則清晰地展示了靳崗遺址目前地表保存的古代城墻及其拐角的空間特征。最后,方城遺址的情況(見圖7)在過濾現代建筑物后也能清晰顯示殘存的西墻及其馬面。
3.3 微地貌場景
微地貌對考古調查而言是發現潛在遺跡的線索之一,但它在觀測和識別上具有相當的難度。由遺跡引起的微地貌特征,其形成原因有兩點:一是遺跡結構埋藏深度較淺,僅頂部部分出露地表;另一點則是遺跡結構大部分遭到破壞,僅剩下細微的痕跡。在研究案例中,光武遺址屬于第1種情況;而梁城遺址和棘陽城遺址結合現場踏查看,屬于第2種情況。
光武遺址城墻保存情況較好,地表可依稀觀察古城墻的夯土結構〔見圖8(a)〕,但墻基埋在地下,地表露頭不明顯。激光雷達掃描的DFM〔見圖8(b)〕可以觀察到北、東、南3個方向有類似城墻的結構,可視化效果也不理想。采用山體陰影配合高程增強顯示后,得到了圖8(c)的結果。該圖清晰顯示了光武古城的北墻、東墻和南墻保存完好且墻體基本閉合,僅西墻和東墻南段有缺失。根據DFM可視化結果,可以復原光武古城的城墻構造,并大致推算其城內面積。
相較于光武遺址,棘陽城遺址和梁城遺址的情況更為特殊。受機械化農耕影響,城址結構破壞較為嚴重。傳統踏查難以發現墻體的位置、結構等空間信息,因此采用山體陰影增強可視化方法對城墻可能分布的區域進行了解析制圖可有效感知殘存的遺跡特征。首先是棘陽城,文獻記載中表明西漢時期棘陽城設立于此,考古踏查也能發現大量的漢代磚瓦、陶片等遺物,但地表不見任何城墻結構〔見圖9(a)〕。使用L2對這一區域掃描后,經計算機后處理過濾了地表低矮植被(農作物)并使用山體陰影配合Z因子倍增對原始高程數據進行增強〔見圖9(b)〕,顯示了一處疑似墻體的微地貌特征〔見圖9(c)〕。從走向看,該結構有可能是此前第二次文物普查時所記載的棘陽城殘存城墻。梁城的情況與之類似,從衛星影像上可觀察梁城遺址僅西北角有一處殘存的古城墻結構〔見圖10(a)〕,而經過HSD增強5倍高程顯示時〔見圖10(b)〕,可觀察到疑似為西墻的微地貌結構順著梁城城墻西北角向南延伸,然后向東拐,而在山體陰影模式中 Z因子增強10倍后,此現象更為明顯〔見圖10(c)〕。根據微地貌數據結果考古專家可對疑似墻體進行標注〔見圖10(d)〕,引導后續實地勘探和踏查。
需注意,并非所有的微地貌特征都是因遺跡埋藏產生。因此對激光雷達數據反映的微地貌特征還需要結合實地踏查、考古研究和遺跡形態理論框架,經人工解譯才能得到相對可信的解釋。
3.4 小結
以L2為代表的棱鏡式半固態激光雷達性能良好,操作簡便,面對植被場景,它可接收5次回波信號,有效克服植被遮擋獲取遺跡信息。在城市場景中,可使用非重復掃描模式向更多方向發射激光束,進而在高樓間隙中更有效獲取遺跡的立面結構,配合點云分類可更直觀地制作考古遺跡專題圖。而面對因遭受破壞或淺埋藏引起的遺跡微地貌特征,棱鏡式半固態激光雷達也可以有效捕捉微小的地形結構,經增強可視化計算后即可重建考古遺跡空間特征。上述場景基本涵蓋了大部分考古調查中面臨的遺跡賦存環境,而本研究的實踐證明這種低成本的機載激光雷達方法應用于大規模、日常化的考古調查工作以及周期性的不可移動文物點保護監測具有現實意義。
需注意,激光雷達在聚落考古調查中的優勢建立在遺址地表存在相關遺跡現象或微觀地貌特征之上,對于深埋地下的遺跡現象仍然無法有效感知,也無法作為判斷遺跡的年代屬性的依據。因此,需要結合地面踏查和遺物采集,空地信息協同才能高效且準確地把握遺址內涵,準確、深入地認識文化遺產。
4 結語
早在30年前激光雷達就已引入考古學領域,成為繼航空可見光遙感后又一場革命[28]。在探索前沿的同時,更應關注如何將激光雷達方案廣泛應用于空間考古調查和文化遺產監測保護工作[29]。南陽古代城址調查的實踐證明了棱鏡式半固態激光雷達空間考古調查方法的潛力。面對植被遮擋、城市以及微地貌等多種賦存環境,棱鏡式半固態激光雷達都能有效獲取考古遺跡信息,基于點云數據生成的DFM清晰顯示了目標城址遺跡的細致結構,讓那些沉寂在荒煙蔓草中的古代城址重出天日,喚醒大眾對文化遺產的共同記憶。不僅如此,該方法將進一步降低激光雷達考古調查的技術準入門檻,讓更多非測繪專業出身的考古人員能夠快速應用,同時也能進一步提升考古調查數據獲取和解析能力,為正在開展的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提供更為堅實的技術保障。
除了制作反映裸土地表信息的高精度DEM/DFM外,激光雷達點云還可與機器學習、圖像識別等人工智能結合,構建考古遺跡識別模型,進而實現對同一類遺跡的自動識別,并由此探討遺跡空間結構特征的量化表達方法[30],從而探討其中的文化因素、思考文明的產生和發展,讓激光雷達數據不僅作為考古成果展示載體,更成為空間考古研究和深度數字化分析的重要材料。事實證明,棱鏡式半固態激光雷達技術在現代考古調查、研究與城址類文化遺產保護中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對其研究和實踐應該持續不斷深入推進,并探索激光雷達技術與考古學的融合,以推動多源遙感空間考古不斷發展。
參考文獻
[1] 黃曉娟,嚴靜,范娟娟,等.陜西周原賀家遺址出土車馬器工藝調查及數字化復原[J].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1,51(5):797-806.
HUANG X J, YAN J, FAN J J, et al.Technical investigation and digital restoration of chariot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unearthed at the Hejia site in Zhouyuan, Shaanxi[J].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2021,51(5):797-806.
[2] RENFREW C, BAHN P.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M].London: Thames amp; Hudson, 2020:86-88.
[3]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場域3D雷射掃描記錄[M].臺北:臺北科技大學防災工程科技中心, 2020:10-14.
[4] 曾昊旻,李松,張智宇,等.車載激光雷達Risley棱鏡光束掃描系統[J].光學精密工程,2019,27(7):1444-1450.
ZENG H M,LI S,ZHANG Z Y,et al. Risley-prism-based beam scanning system for mobile lidar[J].Optics and precision Engineering,2019,27(7):1444-1450.
[5] 王心源,郭華東.空間考古學:對象、性質、方法及任務[J].中國科學院院刊,2015,30(3):360-367.
Wang X Y,GUO H D.Space archaeology: Disciplinary attribute, research object, method and tasks[J].Bulleti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2015,30(3):360-367.
[6] 李松陽,王藏博,徐怡濤.以小型低成本無人機進行大型考古遺址航測的新探索:以赤峰遼中京遺址為例[J].遺產與保護研究,2018,3(11):124-132.
LI S Y, WANG C B, XU Y T.A new exploration of aerial photogrammetry in large archaeological sites with small and low-cost unmanned aircraft: Taking the Liaozhongjing Site in Chifeng as an example[J].Research on Heritages and Preservation,2018,3(11):124-132.
[7] 秦嶺,張海.電子全站儀在田野考古中的應用[J].考古,2006(6):73-78.
QIN L, ZHANG H.The Application of Electronic Total Stations in Field Archaeology[J].Archaeology,2006(6):73-78.
[8] 任冠,魏堅.城市考古研究中空間分析的理論與實踐:基于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61(1): 77-82.
REN G, WEI J.Theory and practice of spatial analysis in urban archaeology research: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system[J].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21, 61(1): 77-82.
[9] 黃德華:福建山區機載LiDAR微地貌識別最優點密度研究[J].測繪與空間地理信息,2023,46(10):132-136.
HUANG D H. Study on the optimal density of airborne LiDAR micro landform recognition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Fujian Province[J].Geomatics amp; Spatial Inofrmation Technology,2023,46(10):132-136.
[10]趙曉東,楊華,王曦閱.三維點云數據微地形特征量的提取及應用研究[J].測繪科學,2024,49(5):133-142.
ZHAO X D, YANG H, WANG X Y.Study on extraction of micro-terrain features from 3D point clouds and its application[J].Scienc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2024,49(5):133-142.
[11]王成,習曉環,楊學博,等.激光雷達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3-5.
[12]PRUFER K M,THOMPSON A E, KENNETT D J.Evaluating airborne LiDAR for detecting settlements and modified landscapes in disturbed tropical environments at Uxbenká, Belize[J].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15(57):1-13.
[13]袁立成,魏振華.三維點云語義分割方法[J].現代電子技術,2024,47(22):51-56.
YUAN L C, WEI Z H.Method of three-dimensional point cloud semantic segmentation[J].Modern Electronics Technique,2024,47(22):51-56.
[14]LI A H, LIU X S, SUN J F, et al.Risley-prism-based multi-beam scanning LiDAR for high-resolution three-dimensional imaging[J].Optics and Lasers in Engineering,2022,150: 106836.
[15]王晶,王朝陽,張峰,等:北斗PPK技術輔助無人機航空攝影測量精度分析[J].測繪通報,2022,(12):64-69.
WANG J, WANG C Y, ZHANG F, et al. Precision analysis of aerial photogrammetry assisted by Beidou PPK technology[J].Bulleti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2022,(12):64-69.
[16]FRACHETTI M D, BERNER J, LIU X Y, et al. Large-scale medieval urbanism traced by" UAV-iDAR in highland Central Asia[J].Nature,2024, 634(8036):1118-1124.
[17]劉一萍,周明全,寇姣姣,等.基于無監督網絡框架的文物點云模型去噪[J].激光與光電子學進展,2022,59(12):362-371.
LIU Y P, ZHOU M Q, KOU J J, et al. Denoising of cultural relics point cloud model based on unsupervised network framework[J].Laser amp; Optoelectronics Progress,2022,59(12):362-371.
[18]王麗英,宋偉東,孫貴博.機載LiDAR數據航帶平差研究進展[J].遙感信息,2012(2):120-128.
WANG L Y, SONG W D, SUN G B.A survey of researches on strip adjustment of Airborne LiDAR data[J].Remote Sensing Information,2012(2):120-128.
[19]黃江雄,曹騫,胡向,等.輕小型機載激光雷達點云處理關鍵技術[J].測繪通報,2024(5):115-120.
HUANG J X, CAO Q, HU X, et al.Key technologies of Point cloud processing for light and small airborne LiDAR[J].Bulleti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2024(5):115-120.
[20]朱軍,朱慶,艾廷華,等. 空間信息可視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23:15-17.
[21]徐巍,孫志鵬,徐朋,等.基于LiDAR點云數據插值方法研究[J].工程地球物理學報,2012,9(3):365-370.
XU W, SUN Z P, XU P, et al.Interpol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Point Cloud Data LiDAR[J].Chinese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physics,2012,9(3):365-370.
[22]TULAR B, EICHERT S, LOZIC E.Airborne LiDAR point cloud processing for archaeology: Pipeline and QGIS toolbox[J].Remote Sensing, 2021, 13(16):3225.
[23]文伯聰,張彤.一種用于導航的2.5維地圖的構建[J].計算機工程與科學,2011,33(4):110-114.
WEN B C, ZHANG T. A 2.5dimension map building for navigation[J].Computer Engineering amp; Science,2011,33(4):110-114.
[24]張海.GIS與考古學空間分析[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272-275.
[25]DELL’UNTO N, LANDESCHI G.Archaeological 3D GIS[M].London: Routledge, 2022:72-74.
[26]任冠,魏堅.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在城市考古中的實踐[J].江漢考古,2020(4):102-111.
REN G, WEI J.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to urban archaeology[J].Jianghan Archaeology,2020(4):102-111.
[27]李宇奇,王紫玉.無人機考古調查方法初論[J].華夏考古,2023(3):128-138.
LI Y Q, WANG Z Y.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archaeological survey methods using UAV[J].Huaxia Archaeology,2023(3):128-138.
[28]LUO L, WANG X Y, GUO H D, et al. Airborne and spaceborne remote sensing for archaeolog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pplications: A review of the century (1907—2017)[J].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2019(232):111280.
[29]孫滿利,張景科.文物保護學的理論探討[J].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2,52(2):192-198.
SUN M L, ZHANG J K.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s[J].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2022,52(2):192-198.
[30]WANG S L, HU Q W, WANG S H, et al. Archaeological site segmentation of ancient city walls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nd LiDAR remote sensing[J].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2024(66):117-131.
(編 輯 邵 煜)
基金項目:國家科技基礎資源調查專項(2022FY101503)
第一作者:田松林,男,從事激光雷達遙感考古和數字化考古研究,MU2323XIAN@163.com。
通信作者:于春,女,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田野考古研究,yuchun@nw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