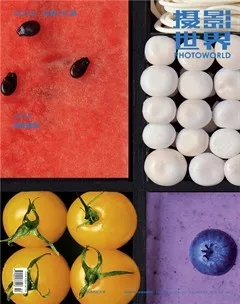技術服務、審美載體和生活影像:攝影師為什么拍美食

談論美食,就像談論天氣一樣,是陌生人拉近距離的好辦法。而且,幾乎每一個人,都能就這個話題聊上幾句。不過,攝影師對美食的關注,卻不像對天氣的關注。雖然在攝影史上,我們能看到很多美食照片,一些被當作報道手段,大部分屬于商業服務,也有的被認為是藝術創作。但美食攝影成為大眾話題,還是近些年隨著智能手機和社交網絡的普及開始的。換句話說,在專業攝影領域,美食攝影并不是個大類型。
技術服務
我們都知道,1839年1月7日,物理學家弗郎索瓦·阿拉貢在法蘭西科學院宣告了攝影術的發明。幾個月后,法國政府購買了“銀版攝影法”的知識產權,并在1839年8月19日正式宣布攝影術誕生,并把這項技術無償提供給世界上所有人使用,讓它變成了公共財產。使用“銀版攝影法”拍攝的照片影調細膩,不易褪色,方法一經公布便得到了歐洲上流社會的一致點贊,還促成了一個新興行業的誕生,即以拍攝肖像照片為主的照相館。
肖像攝影是典型的技術服務型商業攝影。在19世紀,職業攝影師大多以提供技術服務為主,收入也算不錯。但遺憾的是,拍攝美食的職業攝影師非常少見。這要從供給和需求的角度分析。一方面,受限于技術發展和掌握門檻,攝影供給并不多,在沒有明確需求的情況下,不會有多少攝影師關注無法獲得穩定收入的領域;另一方面,受限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食品工業和餐飲服務還沒有用多種手段進行廣告宣傳進而促進銷售的需求,不會有多少攝影師有機會進入美食攝影領域。

這種情況在20世紀初迎來了變化。隨著攝影器材和技術的進步,特別是135小型相機的問世,再加上現代新聞業的迅速發展,報道攝影迎來了黃金時代,商品廣告帶著對20世紀美好生活的向往加速走入普通人的生活,廣告中使用照片也多了起來。得益于此,美食攝影的生意逐漸穩定。在內奧米·羅森布拉姆(NaomiRosenblum)編著的《世界攝影史》(AWorldHistoryofPhotography)中,作者選入了兩張美食廣告照片,分別是瑪格麗特·沃特金斯(MargaretWatkins))拍攝的《鳳凰牌芝士》(1925)和尼古拉斯·穆雷拍攝的《靜物》(1943,照片中包括蛋糕、冰激凌、咖啡、牛奶、麥片)。這兩張照片都有很高的清晰度,也都以充分勾起觀者的食欲為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它們都傳遞著這樣一種消費感受:唯美食與愛不可辜負!而攝影師是誰,不重要。
這種以影像來吸引消費者注意的需求促成了攝影師拍攝美食的生意。除了廣告照片外,餐館是美食攝影師們最重要的客戶。雖然目前還無法確切了解最早使用照片做菜品宣傳的餐廳是哪家,但19世紀后期的法國,已經有餐館使用照片,20世紀20年代中國也有餐館拍攝菜品圖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食照片和帶照片的菜譜伴隨著經濟復蘇被廣泛應用。而當下,我們身邊的現代人已經無法想象沒有照片的菜譜了。而對于餐飲企業來說,拍好一張張美食照片也成了影響經營的大事。
但話說回來,美食攝影服務雖然重要,但畢竟可替代性高,在觀者心中的留存率也低,想在這個領域留名難度很大。尤其是計算攝影越來越強、AI生圖也愈發普及的現在,技術服務型美食攝影市場景氣度難免下降。
審美載體
除了生意,人們生活中不可缺的美食,也承載著我們對于美甚至是善的想象。有種開玩笑的說法,會做飯的男人值得嫁。類似的,拍美食的攝影師審美品味也不會差。只是將美食照片作為審美載體也不是原本便如此的。
1860年,以拍攝克里米亞戰場成名的英國攝影家羅杰·芬頓(RogerFenton)使用蛋白印相工藝拍攝過一幅《果實靜物》照片。這種題材是西方繪畫的傳統題材,一些致力于讓攝影成為藝術的攝影師也繼承了下來,來彰顯自己的美術趣味。不過,將食物單獨作為拍攝對象在那個時代還不常見。


改變局面要等到19世紀最后十年。不依靠攝影為生、卻喜歡拍照片的“業余攝影家”們開啟了“畫意攝影”的時代,他們不同意僅把攝影作為記錄的手段,也不贊成用各種技術讓攝影越來越像版畫、水彩畫或油畫,他們看重拍攝本身,關注照片自身屬性。攝影不是謀生手段,拍照也不是一時興起的玩兒票行為,畫意攝影家們認為攝影是藝術,是美的載體。為此,他們要找到合適的拍攝對象,要突出形式美。雖然畫意攝影家們還是更喜歡拍攝人體,但自然景物、水榭樓臺之外,瓜果蔬菜也逐漸被接納了。特別是20世紀初“直接攝影”美學理念占據主導后,攝影家們表現食物的形式美也多了起來。比如1912年,美國攝影家勞拉·吉平用奧托克羅姆彩色工藝拍攝了裝在籃子里的桃子;1930年,荷蘭攝影家皮特·茲瓦特用明膠銀鹽工藝拍攝了黑白照片《白菜》。

當然,拍攝“食材”最著名的還要屬愛德華·韋斯頓(EdwardWeston)。他在1930年拍攝的《青椒》、1931年拍攝的《卷心菜葉》和1932年拍攝的《傘菌》都是經典代表作。顯然,韋斯頓拍這些肯定不是因為垂涎食物或敬畏食物,他更關心的是在其中找到純粹的“美”,食材只不過是載體罷了。所以,他在1932年1月28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事實上我已經通過攝影證明,大自然擁有藝術家們能夠想象的所有‘抽象’形式。”
生活影像
以上我們所說的,都是將美食或食材作為拍攝對象,它們都缺少“人”的元素。畢竟,古人說“食色,性也。”如果始終沒有人的存在,美食照片的價值總會打折扣。
晚年的愛德華·斯泰肯(EdwardSteichen)一定同意以上關于食色的說法。1955年1月24日至5月8日,時任紐約現代藝術館(MoMA)攝影部主任的斯泰肯策劃了至今在世界范圍內仍頗有影響的大型攝影展“人類一家”。該展覽花了3年籌備,集結了來自68個國家攝影師的503幅作品,力圖用充滿“人文關懷”的方式呈現世界范圍內普遍的價值觀。斯泰肯是不會在這次展覽中放入商業攝影和畫意攝影照片的,但他并沒有放棄反映美食或飲食的照片。展覽中,一共有26幅照片含有美食元素,有的是各種場合下的聚餐,也有的是不同地區人們采買或烹飪食物。這些照片都是生活影像,也都是功能性照片(即不能被當作藝術),表現著斯泰肯心中渴望和想象的某種“大同”,就像他在展覽中引用了一句俄羅斯諺語:“接受了別人的款待,就要講真話”(EatBreadandSaltandSpeaktheTruth)。
20世紀后半葉,作為商業攝影分支的美食攝影發展迅猛,將食材作為純粹藝術表現對象的攝影作品雖然有一些但不成氣候,而以美食切入生活的攝影卻漸漸豐富起來。比如,美國攝影家史蒂芬·肖爾(StephenShore)在《美國表象》包含了很多之前一定會被當作“廢片”的飯菜和餐飲照片,中國攝影家翁乃強用改革開放后菜市場和廟會的照片來表現時代巨變,而最喜歡拍美食的要算瑪格南“怪大叔”馬丁·帕爾(MartinParr)。
馬丁·帕爾曾說“我自認為是一個吃貨”,但他拍攝食物照片絕不是為了打卡紀念或做美食日記。如果你翻一下《珍藏馬丁·帕爾》這本書,就會驚訝于他鏡頭下竟有那么多食物照和餐飲照。從1980年代到21世紀,他拍過快餐,也拍過大餐;他拍過派對聚餐,也拍過孤獨干飯;他拍過清冷的英國食物,也拍過火熱的墨西哥美食;他拍過銷售食物也拍過消費食物。
不過,我們肯定不會孤立地看待馬丁·帕爾拍美食這件事,看看他的那些包括食物照片的系列作品名稱就明白了,《銷售的意義》《生活的成本》《最后的度假勝地》《國內國外》《常識》《無聊的夫婦》《審視英格蘭》,等等,都可為其注解。“吃”這件事,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吃”放在生活中。換句話說,在這些影像中,食物的符號價值是大于其實用價值的。
德國攝影家沃爾夫岡·提爾曼斯(WolfgangTillmans)也是這么認為的。在他的作品中。我們也經常能見到聚餐、吃喝或者食物本身,但相比馬丁·帕爾,沃爾夫岡鏡頭下的日常食物更生活化,符號的指向不再是中產階級空虛無聊,變為了叛逆不羈的青年文化和亞文化。
最后,還有一位攝影家的照片我想要提及,那就是德國攝影家約阿希姆·施密德(JoachimSchmid),他在2008年到2011年完成了一組“借用照片”系列作品《來自他人的照片》。英國攝影評論家馬克·德登(MarkDurden)在《今日攝影》一書中引用了其中一組四聯照片《咖啡》,內容是攝影家收集的普通人拍攝的杯裝咖啡照片,其中有兩杯還有拉花,雖然拍得不算好,但一看便知攝影師是在模仿咖啡館菜單中的樣子來記錄自己的咖啡時光。由此引發了很多攝影人思考的兩個問題:這算藝術作品嗎?它們可以被歸類為美食照片嗎?
對于第一個問題,藝術界和藝術市場已經給出了答案:算!因為在當代藝術中,我們感受的不是寫實的美,不是形式的美,而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生命美、生活美,是人與社會的關系,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與人的關系。
對于第二個問題,答案要模糊一些,從本文給出的攝影師為什么拍美食的三個角度,似乎不算。但是,正如本文開頭所述,美食攝影成為大眾話題,是近些年隨著智能手機和社交網絡的普及開始的,我們現在談論美食照片,職業攝影或專業攝影的語境實在是越來越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