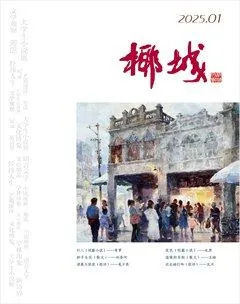旅程(短篇小說)
經(jīng)過三個(gè)多小時(shí)的快速行駛,上午十點(diǎn)鐘他們到達(dá)了露營地。項(xiàng)婧看著車窗外的黃沙、荒草和蒼茫的遠(yuǎn)處,對趙小語要求的草原露營之旅表達(dá)了最后的憤怒。
項(xiàng)婧雙腳站在沙地上,忍不住發(fā)牢騷。趙博又像沒聽到一樣,沉默如常。他打開車的后備箱拿東西,開始在一棵大柳樹下搭帳篷。他一定會先搭那頂橘色的小帳篷,然后才能輪到大一點(diǎn)的灰色帳篷。
趙小語跟在趙博后邊,拿著固定帳篷用的地釘,歡快地在一旁準(zhǔn)備著。項(xiàng)婧又嘆了一口氣,她為什么要跟著他們父女到這個(gè)地方來呢?但緊接著,她又后悔在路上對他們說了那么多話。她本該管住自己的,她對自己都感到厭煩。
她轉(zhuǎn)頭看向遠(yuǎn)方的沙山,金黃的沙山圍著一塊平地連綿接續(xù)。一條河流呈U形流動(dòng),帶出一片綠洲。她向靠近河流的沙嶺走去,可在沙地上走路很吃力,才走一小段,她就微微喘粗氣了。
別想得那么美好,生活就是一條向老的路。她記得以前一位老領(lǐng)導(dǎo)是這么說的。當(dāng)然,那老領(lǐng)導(dǎo)已經(jīng)故去了。
她在沙嶺邊沿上坐下來,面對著河流。
“不能把帳篷搭在河邊,那樣會被蚊子咬。河邊蚊子多,它們也喜歡水草豐茂的地方。”趙博對趙小語說,用一貫溫柔敦厚的口氣。
項(xiàng)婧回頭看他們,趙小語乖巧地跟在趙博身邊,專注地看著趙博抖弄帳篷支架,再一根一根地?fù)纹饋怼K洲D(zhuǎn)回頭來看河流,河流邊上有幾戶人家撐起遮陽棚,放了野外的小餐桌,圍坐著看孩子在河里玩。
猛然間,她聽到趙小語驚叫起來,她趕緊站起身,就要往回走。
“就是一條毛毛蟲嘛,怕什么呀!你要想,它會變成蝴蝶的,美麗的蝴蝶。”趙博說話時(shí)雙手扇動(dòng)著,學(xué)蝴蝶飛舞的樣子。
趙小語安靜了下來。
趙博這句話說得倒是不錯(cuò),項(xiàng)婧想。她又坐回沙地上,沙子被太陽曬得暖暖的,熱意再一次從臀部一直向上延伸。她仰起頭,閉上眼睛,陽光就照在她的臉上。
過了很長時(shí)間,趙博和趙小語從遠(yuǎn)處邊說話邊走過來。
“帳篷都搭好了,我們要到下邊走走,你去不?”趙博指著沙山下的河流說。
項(xiàng)婧搖了搖頭,“你們?nèi)グ伞!彼f。她看著他們沿著沙坡路一腳深一腳淺地走了下去,仿佛要離開她一樣。
遠(yuǎn)處,她看見趙小語一手拎著鞋在河里走著,光腳蹚著水——她在想什么呢?她是個(gè)14歲的少女了,已經(jīng)跟她這個(gè)母親剝離得差不多了。趙小語一直低著頭看水面,現(xiàn)在她彎下腰,在水里找尋,一定是河里有蝌蚪或蟲子什么的。項(xiàng)婧幾乎下意識地想喊出來,提醒趙小語把手機(jī)拿好,別掉水里了。不過,她沒開口,畢竟距離這么遠(yuǎn),況且她也意識到根本無需提醒。
在趙小語5歲時(shí),項(xiàng)婧懷上了一個(gè)孩子。不過,那時(shí)她很戲劇性地一直跟趙博爭吵不斷。她完全對他喪失了欲望,不愿意忍受趙博的親密。她計(jì)劃著離婚,很決絕地把孩子打掉了。這件事隨著時(shí)間的流走變得日漸重要起來,她默默地為了她毀滅的這個(gè)小生命懺悔,有時(shí)還忍不住幻想那是一個(gè)男孩,生下來,他會成長,心向著她。
太陽曬得厲害,她往后移動(dòng),退到一棵大柳樹下坐著。她抬頭看天空,看遠(yuǎn)處的沙山和草地上的羊群,但更多時(shí)候她看著趙小語和趙博。
她伸開雙腿讓自己舒服點(diǎn)。她看見右腳上有一條灰綠色的毛毛蟲,于是皺緊了眉頭,準(zhǔn)備站起把它甩掉。毛毛蟲晃動(dòng)著腦袋,一半身體貼附在她白色的鞋幫上,一半身體懸空,頭引領(lǐng)著軟糯的身體四處晃動(dòng)。它在找一個(gè)附著物,多么脆弱,只要她一落腳就可以讓它去死。
她看著毛毛蟲蠕動(dòng),想到了菜市場案板上魚的抖動(dòng),尾巴擊打在案板上發(fā)出啪啪的聲音,而頭翹起,又摔在案板上。泥鰍從水桶里躍出來,在地板上蜿蜒摔打,它們可真夠慘烈的,她想。接著她的注意力又回到毛毛蟲身上,眉頭已然舒展了些,臉上現(xiàn)出嚴(yán)肅而平靜的神色。她把腳往一根苦豆菜前移動(dòng),毛毛蟲蠕動(dòng)著,把頭伸向了苦豆菜。
趙小語和趙博的情緒都很高,在中午一點(diǎn)前,他們終于準(zhǔn)備好了午飯。
“媽媽今天心情也很好吧!”趙小語笑嘻嘻地看著她說。
“當(dāng)然好,你看她今天都沒嫌棄我們倆呀!”趙博說著,在她臉上掃了一眼,臉上露出戲謔的笑容。
項(xiàng)婧張了張嘴,沒出聲。她用筷子夾了一塊火腿片放進(jìn)嘴里嚼著,眼睛看向別的地方。
他們旁邊不遠(yuǎn)處一棵柳樹旁,一個(gè)女人正坐在帳篷外抽煙。她灑脫的神態(tài)讓項(xiàng)婧忍不住偷偷打量。她在帳篷門口擺放了一張小桌子,上面鋪著白綠相間的格子桌布。她上半身靠在折疊椅子上,兩腿伸開,瘦長的身體健美地舒展著,一邊吸煙一邊看著遠(yuǎn)處的天邊。
他們與那個(gè)女人之間大概有20米的距離。
“你說她怎么會一個(gè)人來野營呢?”項(xiàng)婧低聲問。
“管她呢。”趙博說。
“耍酷唄。”趙小語說。
項(xiàng)婧又不說話了。
他們吃完了午飯,項(xiàng)婧認(rèn)真地洗了碗筷。到了這個(gè)地方,她用起水來也謹(jǐn)慎了很多,倒不是沒有水,而是這滿眼的沙地和細(xì)淺的河流讓她不忍心多用水了。
“又不是沒水,為什么不把水開大點(diǎn)呢?”趙博問。
“這不是節(jié)約用水嗎。”她說。
“都會流到沙地里,也不算浪費(fèi)。”他說。
這讓項(xiàng)婧不知該怎么反駁。“管得可真多。”她抱怨說。
趙博和趙小語又去玩了,他們說要四處走走。趙小語說要去玩滑沙,從高高的沙嶺上滑下去,都是些孩子的把戲。
項(xiàng)婧戴著遮陽帽,懶懶地靠坐在折疊椅上,雙腳搭在樹干上。整個(gè)下午,她都可以這樣獨(dú)自享受了。她看了很長時(shí)間的朋友圈。直到4點(diǎn)多,旁邊帳篷里的女人走了出來。她大概已經(jīng)睡了一個(gè)美美的午覺,神色清爽,還換了一身藏青色的運(yùn)動(dòng)衣。
她打開車門,很利落地上去,關(guān)上車門,發(fā)動(dòng)了越野車,沿著沙土路向遠(yuǎn)方駛?cè)ィ@一系列的動(dòng)作都讓項(xiàng)婧羨慕。
項(xiàng)婧站起來,向沙土路眺望。車影消失了。片刻后,她拿出手機(jī),發(fā)了微信給趙博。
她轉(zhuǎn)身回帳篷里拿了自己的包,找到車鑰匙。她有些慌亂,臉紅紅的,車鑰匙掉在地上兩次。她也很有力地打開車門,發(fā)動(dòng)車子,向沙土路的方向開去。
她并沒有開出很遠(yuǎn)的距離,在一處沙地上,她的車陷住了。雖然感到尷尬,但她并不為這件事后悔。
她幾次發(fā)動(dòng)車子都沒有成功。她從車上下來,查看車輪陷入的情況。但她只是繞著車轉(zhuǎn),沒有任何有效率的行動(dòng)。
遠(yuǎn)處一輛皮卡車正在行駛,猶豫了一下,向她這邊開過來了。她緊張地站在原地,等著那輛皮卡車開近。
一個(gè)粗壯的男人從車上下來,毫無顧忌地看了她一眼。
“我?guī)湍阃铣鰜怼!彼f。他有草原人特有的口音,給她一種牛羊吃青草的感覺。
他拿出繩索。“在沙地上經(jīng)常需要這個(gè)。”他看了她一眼,飽經(jīng)風(fēng)霜的臉上帶著干凈的笑容。
“真是太感謝了,我正不知怎么辦呢!”她說。她在想要怎么答謝他,首先想到的是給一筆勞務(wù)費(fèi),幸好來之前她特意準(zhǔn)備了現(xiàn)金,畢竟這里不是城市,在這種情況下轉(zhuǎn)賬也有點(diǎn)煞風(fēng)景。
她站在邊上看著他掛繩。
“發(fā)動(dòng)車子,等我開始拉的時(shí)候,你就慢慢往前開。”他對她說,等著她上車。
她按他的指示行動(dòng)起來,車啟動(dòng)后差一點(diǎn)就撞到他的車上,她緊張得出了一身汗,又感到羞愧,臉紅紅的,她能想到自己在他眼里的狼狽樣。
他并沒有嘲笑她,還安慰她說沒事。
她緊張地掏出現(xiàn)金。“就這么多了。”她說。
他哈哈哈笑起來。“這不用付錢,完全免費(fèi)。”他說。
他說他就住在離這不遠(yuǎn)的地方,經(jīng)常遇到這種情況,只要碰見了他都會幫忙的。
“那就加個(gè)微信吧。”她說,好像生怕欠了他的。
男人笑了笑,把手機(jī)拿出來,讓她掃微信二維碼。
她聞到他身上帶著的沙土和野草的氣息,還夾雜著煙味。她把這樣的氣味記到了心底,這是跟城市完全不同的味道。
他的昵稱是草原人,樸實(shí)親切。
目送皮卡車消失在前方,西天的紅日就要落下去了。她上了車,并沒有再往遠(yuǎn)處開,而是選擇了原路返回。她能感覺到有些東西在從她身上脫落,她變得輕松安逸。夕陽往下滑,云霞漫天,曠野寂靜,這給她造成了一點(diǎn)情緒波動(dòng),心里最柔軟的部分在覺醒。激情、美好、放手……多種情感混雜,在她胸口激蕩,幾乎讓自己熱淚滾滾。她加快了車速,心里想著一部外國電影里女人在公路上開車的場景,金黃色的長發(fā)在風(fēng)中飄揚(yáng),緊接著,腦海中又是旁邊帳篷里女人開車沿沙土路駛向遠(yuǎn)處的畫面。
車燈亮著,前面就是露營地,她把車速調(diào)慢,讓時(shí)間拉長。
帳篷就在前面不遠(yuǎn)處的柳樹林里,在這片大樹林里有幾處帳篷,除了他們自己家的兩處和旁邊女人的帳篷,在稍遠(yuǎn)一點(diǎn)的樹旁還有幾處帳篷。
她沒有把開車出去發(fā)生的事情告訴趙博,更不會對趙小語透露任何消息。她終于有了一個(gè)特別的秘密,感覺內(nèi)心都豐盈起來。
趙博已經(jīng)把晚飯準(zhǔn)備好。
“來這個(gè)地方不也還是一樣要吃飯,跟在家里吃有什么不同呢?都一樣過日子。”她說,臉上是玩笑的表情。
“那您干嘛還要開車出去呢?您不是最煩開車嗎?跟在城市里開有什么不同呢?”趙小語說。
趙博笑起來了。
“你們兩個(gè)就是小團(tuán)伙,二人幫。”她笑著說,很快樂地拿起一片面包片,開始往面包上涂果醬。
“您不是說果醬太甜,不吃嗎?”趙小語說。
項(xiàng)婧呵呵地笑了起來。“我剛剛開車消耗太多。”她說。
“得開燈了,蚊子太多了。”趙博說。
“我怎么沒感覺有蚊子呢,這樣朦朧的感覺也挺好,還挺有情調(diào)的。”她說。然而她突然意識到自己過于快活了,于是專心地吃起東西來,一邊回憶著“草原人”幫她拖車的情景。
傍晚晦暗的天色下,兩束車燈的光直沖而來,隔壁帳篷女人的越野車出現(xiàn)在路口。他們?nèi)硕伎粗禽v車開近,從他們面前經(jīng)過,停在原來的那棵樹旁。
他們看著女人進(jìn)了帳篷,片刻后音樂就從她帳篷的縫隙里飄出來,響在空蕩的夜里。
睡前,他們一家三口坐在沙地上看了星星。趙博和趙小語有說不完的話,而她更多的時(shí)候是沉默的,間或插話也只是“嗯”“啊”的回應(yīng)詞。她在獨(dú)自回想一些過去的事情,有些片段清晰,有些片段模糊,有些片段她自己都感到驚詫。
睡覺前,項(xiàng)婧帶著趙小語一起去方便。母女倆走出好遠(yuǎn),直到看不見帳篷群里透出的光,才輪流值班,把事情解決了。趙小語已經(jīng)比她高了一點(diǎn),在這樣黑暗的夜里也沒挽住她的胳膊。
露營的缺點(diǎn)之一就是沒有廁所,要想解決問題,必須得走到很遠(yuǎn)的沒有人的地方露天排泄。在白天尤其不便。每次要方便的時(shí)候,項(xiàng)婧都會帶上一個(gè)塑料袋,把自己用過的手紙裝進(jìn)塑料袋里,再帶回來,用石頭壓在不遠(yuǎn)處的一棵樹下,留待統(tǒng)一處理。
旁邊的帳篷里也亮著燈,不遠(yuǎn)處一個(gè)搭帳篷里有人正在唱歌,還有男人間爭吵勸酒的聲音。他們已經(jīng)鬧騰很久了,酒后疏解的叫嚷聲在風(fēng)中飄散。
項(xiàng)婧總?cè)滩蛔∪リP(guān)注旁邊帳篷的動(dòng)靜。在這荒野中,她缺乏安全感。旁邊帳篷里的燈光和遠(yuǎn)處時(shí)高時(shí)低的酒話也讓她感到親切。
項(xiàng)婧在風(fēng)聲還有類似雨點(diǎn)的聲音中醒了,她抬起手看了看時(shí)間,熒光的表盤上顯示凌晨兩點(diǎn)多。她爬出帳篷,帳篷外的月色很好,一片清暉。趙小語沒關(guān)帳篷燈,從里面透出光來。她小心地拉開帳篷,趙小語裹在睡袋里睡得正熟。
她在帳篷邊上站了一會,向遠(yuǎn)方看看,又抬頭看月亮,接著她向河邊的沙嶺處走了幾步,又停下來,站在原地四處張望。她又回頭看了看那三個(gè)帳篷,一大一小挨得很近,另一個(gè)在旁邊很安靜。她轉(zhuǎn)回身迎著月亮走去,除了從河流中傳來的清脆的蛙聲,就是她自己的喘息聲,她一深一淺地向前走,臨近河流的時(shí)候,她加快了腳步。
她站在沙嶺上,看月色,看河流,看月光下的空曠,蛙聲起伏應(yīng)和。過了一會兒,她猶豫著坐在了沙地上。
猛然間背后有響聲,有踩著沙子走路的聲音,她忍不住回頭,看見不遠(yuǎn)處有一閃一閃的光點(diǎn),一個(gè)抽煙的人正在走近。她沒有站起身,只是不動(dòng)聲色地移動(dòng)雙腿,并攏在身前,做好隨時(shí)起身離開的準(zhǔn)備。
那個(gè)人并沒有直接靠近她。月光下,項(xiàng)婧看清了走來的是旁邊帳篷里的女人,一瞬間她就放松了。
“月色不錯(cuò)。”女人說。
“是,很安靜。”項(xiàng)婧說著,站了起來。
“我叫薩仁。”女人說。
“我叫項(xiàng)婧。”她的語氣緊張又欣喜。
薩仁遞過來一支煙。
“我不抽煙。”項(xiàng)婧說。趙博不抽煙,她也不抽煙。抽煙有害是他們一直以來的信條。
“不抽也沒關(guān)系,點(diǎn)著了,熏蚊子。”薩仁說,她把打火機(jī)按著,項(xiàng)婧把煙伸過去,點(diǎn)著了。在夜風(fēng)下,煙很容易就點(diǎn)著,在風(fēng)中燃燒。項(xiàng)婧把煙拿在手里,學(xué)著薩仁的樣子,把煙放在食指和中指之間夾著。
薩仁很隨意地坐在了沙地上,一口一口地吸著煙。項(xiàng)婧也在她旁邊坐下了。這是一種奇妙的感覺,兩個(gè)女人深夜出現(xiàn)在星空下,坐在曠遼的沙地上抽煙。
項(xiàng)婧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煙送到嘴邊的,一口下去她就被嗆到了,咳嗽起來。
薩仁什么都沒說,依然看著月亮。她這樣淡然的態(tài)度讓項(xiàng)婧很感激。
“我第一次抽煙。”項(xiàng)婧說。
“嗯,不抽也好,我抽很多年了。”薩仁說。
“沒想過戒煙嗎?”項(xiàng)婧問。
“沒有,人生的愛好越來越少,最后就剩下這么點(diǎn)自我放縱了,我可不想再難為自己了。”薩仁說。
項(xiàng)婧睜大了眼睛,看著手中的煙,煙頭的火花和她眼中的光碰撞在一起。她沒想到薩仁抽煙會是這樣的理由,而她從來沒有一點(diǎn)放縱自己的癖好。
“你女兒很漂亮。”薩仁突然說。
“14歲了,真是不知怎么就長這么大了。”項(xiàng)婧說,“你怎么一個(gè)人來露營呢?我是不敢的。”
“我習(xí)慣了。”薩仁說完,又點(diǎn)燃了一支煙。
月亮掛在半空,幾縷云在月亮周邊纏繞。她們都抬著頭看月亮。
“好像一切都是夢,這樣的夜晚很不真實(shí)呢,我一直生活在城市。”項(xiàng)婧說。
“嗯,荒野讓人自在。”薩仁說,她的煙頭亮了又暗。
再次回到帳篷里,已是凌晨三點(diǎn)。趙博把手伸過來時(shí),她沒有甩開。
一群馬在奔騰,綠草地上野花在搖晃,茂盛的草在起伏波動(dòng),上面是漫天的蝴蝶,它們跟著馬群在飄飛。一切就在她眼前,她驚呆在原地,看著馬群奔跑。
三小時(shí)后她醒來,夢境里的馬群依然在她腦海里奔跑,一切都像真實(shí)發(fā)生過的。
趙博不在了,他在微信里留言說他們要繞著沙嶺走一圈。
她從帳篷里出來。晨暉中帳篷上爬滿了毛毛蟲,綠色的、灰色的、灰綠相間的……大多數(shù)毛毛蟲在蠕動(dòng),它們在夜晚被一陣大風(fēng)刮落在帳篷上,到早上都沒能離開。
她向四處望了一圈,只見樹影。她迎著太陽光的方向走去,竟然想尋找馬群奔跑過的痕跡。
當(dāng)她返回時(shí),薩仁正用便攜燃?xì)鉅t煮東西。
“早上好。”她歡快地對薩仁說。
“睡得好嗎?”薩仁嘴里還叼著煙。
“很好。”她說,眼睛看著薩仁嘴上的煙頭一閃一閃的火光。她不著急煮飯,于是就走到薩仁的帳篷前。
薩仁把麥片倒入碗中,把滾開的水倒進(jìn)去,加了牛奶。“我平時(shí)喜歡喝奶茶,今天早上懶得煮了,中午煮,你們一起來喝。你們不走吧?”薩仁的聲音比夜晚爽朗很多,還帶有濃濃的草原韻味,比“草原人”的口音要淡一些,聽起來很舒服。
“下午走。那就一起吃午飯吧,我們也帶了一些吃的。”項(xiàng)婧爽快地附和著。
吃早飯的時(shí)候,他們一家就跟薩仁熟識起來。趙博變得健談了很多,他說的話還能把薩仁逗笑。趙小語纏著薩仁教她表示問候的蒙語。
他們坐在柳樹下,像親切的朋友一樣說了一會的閑話。薩仁說很多以前的事情,而項(xiàng)婧也愿意聽。后來,趙小語被一陣鳥叫聲吸引,趙博跟著她去尋找鳥的蹤跡。
薩仁提議去走走。出了柳樹林,更遠(yuǎn)一點(diǎn)的地方是一片田地,田埂齊整。在田地和樹林之間是一處傾斜的草坡,雜草地里散落著啤酒瓶等各種垃圾。
“這些人,來這就是制造垃圾。”薩仁抱怨說。
“我們那有大的塑料袋,可以撿一些。”項(xiàng)婧說。
薩仁看著她哈哈笑起來。“好吧,我們就做點(diǎn)好事。”她說。
她們又返回去,拿了兩個(gè)大塑料袋,把小塑料袋套在手上,像模像樣地?fù)炱鹄鴣怼?/p>
酒瓶、礦泉水瓶、煙盒、煙頭,還有女人用過的衛(wèi)生巾。撿衛(wèi)生巾的時(shí)候,項(xiàng)婧忍不住在心里咒罵起來。在撿垃圾的過程中,項(xiàng)婧的心是沉重的。這并不是美好的體驗(yàn),垃圾在這個(gè)地方大批出現(xiàn)本身就是人類自私的證明。
很快,兩個(gè)袋子就裝得滿滿的了。
“垃圾袋就放我車上吧,我知道往哪兒扔。”薩仁說。
上午十一點(diǎn),薩仁開始燒奶茶。
一條綠色的毛毛蟲掉在薩仁的肩膀上,蠕動(dòng),茫然。
“沒落到鍋里,算它好運(yùn)。”薩仁說。她用手指輕輕捏著毛毛蟲,把它放到了旁邊的草葉上,它慢慢地蠕動(dòng)著往前爬。
“你說它知道要去哪里嗎?”項(xiàng)婧困惑地說。
“知道吧。”薩仁回答,她轉(zhuǎn)頭看了一眼在草葉上的毛毛蟲。
“蟲子的世界,我不懂。”她玩笑似的說。
“想不到這樣軟塌塌的蟲子會變成蝴蝶。”項(xiàng)婧含糊地說,更像是自言自語。
“也許是變成蛾子,不是所有的毛毛蟲都會變蝴蝶。”薩仁說。她把煙放在嘴里叼住,騰出手?jǐn)Q開煤氣罐的開關(guān),用打火機(jī)點(diǎn)燃,“我做記者的時(shí)候在南方見過一種特別漂亮的毛毛蟲,渾身長滿彩色的毛。這種毛毛蟲不大,瘦瘦的,大概三厘米,顏色卻十分艷麗。當(dāng)時(shí)它正在休閑地爬著,我對我身邊的朋友說,它一定能變成色彩艷麗的蝴蝶。你猜怎么樣,我朋友說它注定會變成蛾子。我只能信他,因?yàn)樗芯坷ハx。”薩仁講這些事情時(shí)自帶神秘感。她的煙灰落到了奶茶鍋里,她把煙頭在水里按滅,丟進(jìn)垃圾袋中。
“這么想來還真有點(diǎn)奇妙,很多習(xí)以為常的事情一細(xì)想就有點(diǎn)難以理解了。”項(xiàng)婧說。
“我倒覺得可以理解,蛻變前色彩那么濃烈,羽化后變成喜歡撲火的飛蛾,本性難改。”薩仁說。
“夠慘的,還是普通的毛蟲蟲好,之前毫不起眼,羽化后就變成了飄飛的蝴蝶。”項(xiàng)婧說。
“無非是前好和后好的分別,其實(shí)都是一樣的。”薩仁說。她正在用盒裝的牛奶兌奶茶。
“我還帶了黃油。”項(xiàng)婧說。她從一個(gè)帆布袋里掏出一個(gè)小瓶子,里面是金黃的凝固物。
薩仁說她練過近身格斗,并且堅(jiān)持長期鍛煉,她去過很多地方,做過很多有趣的事。
“真羨慕你。”項(xiàng)婧說。
“其實(shí)呢,每個(gè)人都有每個(gè)人的路,就像同樣是毛毛蟲,有的會變成蝴蝶,有的變成蛾子。可有什么關(guān)系呢,努力扇動(dòng)翅膀就行了。”薩仁說著,調(diào)皮地笑著瞇了一下眼睛。
項(xiàng)婧沿著沙土路向遠(yuǎn)處望去,高高的沙丘擋住了她的視線。他們一定玩得很開心,她想。過了一會兒,趙博和趙小語出現(xiàn)在沙路上。
趙小語跟薩仁玩得很好。她喜歡聽薩仁講戶外旅行中發(fā)生的事情。
“你得學(xué)會跟自己玩。”薩仁對趙小語說。薩仁自己沒生孩子,這時(shí)倒像個(gè)開明的媽媽,對趙小語表現(xiàn)出極大的耐心。
午后,項(xiàng)婧幫薩仁拆卸帳篷,打包。薩仁說她要到附近城區(qū)補(bǔ)充物資,接著去下一站。趙博和趙小語都羨慕地看著將要離開的薩仁。
她們彼此告別。項(xiàng)婧主動(dòng)擁抱了薩仁,承諾要常聯(lián)系。
他們看著薩仁的車消失在沙路盡頭。
“我以后也要買輛車,自己一個(gè)人到處跑。”趙小語說。
食物和水還夠,項(xiàng)婧決定再留一晚,第二天上午再走。這個(gè)決定得到了趙小語的強(qiáng)烈支持,她蹦跳著擁抱了項(xiàng)婧。項(xiàng)婧已經(jīng)很久沒得到這樣的擁抱了,一瞬間她幾乎要流淚,又溫暖又委屈。
薩仁的離開讓項(xiàng)婧心里失落了片刻,可她得成為自己,這對一個(gè)40多歲的女人來說確實(shí)是一個(gè)必須面對的問題了。
下午,她一個(gè)人到周邊去轉(zhuǎn)。
河流對岸的遠(yuǎn)處有幾匹馬正在吃草、走動(dòng)。
薩仁說能看到馬就不錯(cuò)了,如今草原上的人都開車、騎摩托,馬失去了優(yōu)勢。項(xiàng)婧不禁為那幾匹馬憂傷了起來。
一些家庭帶著孩子,吃東西、喝酒、說話,而孩子在玩水。無論世界變成什么樣,總會有歡笑聲響起。
項(xiàng)婧在沙脊上的一棵柳樹下坐下來,看著平原處河流的迂回蜿蜒,等著時(shí)間靜靜流逝。褲腿上有一條毛毛蟲在爬,她把它放在手心里,看它蠕動(dòng),尋找出路。她開始和毛毛蟲對話,原本讓她起雞皮疙瘩的蟲子,突然變得親切起來。她專注地看著毛毛蟲,好像進(jìn)入了另一個(gè)世界。
天氣預(yù)報(bào)說一天后有沙塵暴,傍晚的云霞瑰麗得出奇,然而風(fēng)不大,周邊又多了幾個(gè)新帳篷,有一些陌生的人在活動(dòng)。
這晚的月亮很好。她在月光下點(diǎn)著一支煙。煙是薩仁留給她的,同時(shí)留下的還有一個(gè)精美的打火機(jī)。她并不打算以后繼續(xù)吸煙,但她覺得偶爾抽一支煙也挺好。
一個(gè)人坐在荒野的月光下,周圍的一切都蒙上了神秘感。她想起群馬奔騰、群蝶飄飛的夢境,連薩仁都變得不真實(shí)起來。然而一切都還那么清晰,薩仁爽朗的女中音還響在她耳邊。
第二天早上,帳篷上依然爬滿了毛毛蟲。它們中的一些可以變成蝴蝶,另一些的生命會終結(jié)在蠕動(dòng)的階段。
回去的時(shí)候,項(xiàng)婧主動(dòng)要求當(dāng)司機(jī)。
“回去要好好學(xué)習(xí)。”趙博對趙小語說。
“知道了,知道了,趙先生回去也要好好工作。”趙小語說。
“我正在化蛹。”項(xiàng)婧插話說。
“啊?什么?”他們兩個(gè)異口同聲地驚問。
“化蛹,我在化蛹。”項(xiàng)婧平靜地說。她還回想著那個(gè)奇怪的夢,她沒跟趙博和趙小語說這個(gè)夢,也沒有告訴薩仁,這個(gè)夢屬于她自己。她覺得她值得擁有一些屬于自己的事情,包括和“草原人”那簡單卻充滿人間溫情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