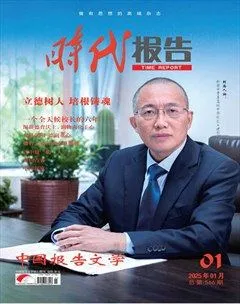梁曉聲:父母是最樸素的人文
父親常年在外工作,母親一個(gè)人帶著五個(gè)孩子。這個(gè)家庭沉重但不乏堅(jiān)韌和患難與共。在面對(duì)旁人的不理解時(shí),母親還是湊足了錢(qián)給渴望閱讀的兒子買(mǎi)書(shū),為他構(gòu)建了一個(gè)精神家園,讓他在苦難的生活里得到了文學(xué)最初的啟蒙……
在近日中央電視臺(tái)播出的《朗讀者》節(jié)目中,著名作家梁曉聲通過(guò)對(duì)自己作品《慈母情深》的朗讀,再憶母親和家庭,打動(dòng)了許多觀眾。
近日,梁曉聲接受中國(guó)婦女報(bào)記者專(zhuān)訪。
他憶家庭,談家教。在他看來(lái),在自己那個(gè)并無(wú)豐厚文化底蘊(yùn)的家庭里,母親像一棵樹(shù),父親像一座山。父母教育他很多樸素的為人處世的道理,令他終身受益。以此為傳承,梁曉聲作品中的平民化傾向以及他對(duì)兒子的特殊教育方式,成了這個(gè)家庭潛移默化的樸素的人文思想。
潛移默化的家庭教育
“成文成系統(tǒng)的家風(fēng)家訓(xùn),是無(wú)從起的。”這是梁曉聲對(duì)兒時(shí)家庭的回憶。1949年,他就出生在哈爾濱這個(gè)“父母皆目不識(shí)丁”的工人家庭。
梁曉聲告訴記者,在自己那個(gè)并無(wú)豐厚文化底蘊(yùn)的家庭里,真正意義上白紙黑字的家風(fēng)家訓(xùn)無(wú)從談起。但父母卻用樸素的行動(dòng)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的一生。
父親的一次“拍桌子”,讓梁曉聲在六十年后依然記憶深刻。
那是1957年的一天,父親工作的建筑工地上“分”來(lái)一名“右派”女大學(xué)生,班里的一些工人成心往女大學(xué)生挑的擔(dān)子上多放磚頭,看著她挑不起來(lái)就嘻嘻哈哈地笑。作為班長(zhǎng)的父親大怒,與工友打了起來(lái):“那是不對(duì)的!”談起這件事,父親生氣地拍著桌子吼,“你以后敢那樣,我就不認(rèn)你這個(gè)兒子!”
“我的外祖父是念過(guò)幾年私塾的,這使我母親在‘文化知識(shí)’方面比我父親‘厚’多了。”在梁曉聲的記憶里,相較于父親,母親對(duì)兒女們的教育是有意識(shí)的、自覺(jué)的。
小學(xué)時(shí),梁曉聲一家搬到了哈爾濱的“光子片”,那一“片”的街名依次是光仁街、光義街、光禮街、光智街、光信街,歷經(jīng)“文革”,這些街名至今未改。母親告訴他,光智街中的“智”非指心機(jī),是指理性。梁曉聲愛(ài)讀書(shū),即使在那些艱難的歲月里,母親也會(huì)像《慈母情深》中描寫(xiě)的那樣,給錢(qián)讓兒子買(mǎi)書(shū),滿(mǎn)足兒子求知的“奢望”。
梁曉聲的青少年時(shí)期,父親常年在外地工作,父子二人見(jiàn)面時(shí)間不多。與父親真正可用“相處”來(lái)論的日子,是父親60歲退休時(shí),那時(shí)梁曉聲在北京電影制片廠工作。父親成了慈眉善目、幾乎完全沒(méi)有脾氣、與人說(shuō)話(huà)先自微笑的老者。
父親給許多北影人留下的印象極深。
當(dāng)年,梁曉聲家安在北影廠筒子樓的一個(gè)14平方米的老舊房間內(nèi),父親經(jīng)常打掃公共樓道、水池、廁所,鄰居們都很尊敬他,至今仍時(shí)常談起。梁曉聲說(shuō),受父親影響,他充當(dāng)公共衛(wèi)生員也有近20年時(shí)間了,很多人家都已搬走,樓梯依舊被梁曉聲拖得一塵不染,以至于后搬進(jìn)來(lái)的人家以為他就是清潔工。
“母親的善良引導(dǎo)我創(chuàng)作”
梁曉聲一直認(rèn)為,母親給予他的人文影響超過(guò)父親。
當(dāng)年,城市人家也愛(ài)養(yǎng)雞,梁曉聲家同樣如此。在一次野貓吃雞后,父親就下了鋼絲套,并套住了一只大野貓,吊在木圍欄上,命懸一線(xiàn)。母親為了救下它,衣服被撓破了,胸前被撓出了一片血道子。最后終于救成功了,母親疼而不悔,這件事給梁曉聲留下了很深的記憶。
梁曉聲說(shuō),母親的善良、寬厚幫助了許多人,得到了許多人的敬重,這些人心向善與感恩懷德,至今仍對(duì)他的為人處世深有影響。
鄰居家小女孩偷走了梁曉聲母親剛剛借來(lái)的5元錢(qián),派出所破案后要通知學(xué)校,母親堅(jiān)決不許,反而請(qǐng)女孩到家里來(lái)吃了頓“壓驚飯”。后來(lái),女孩認(rèn)梁曉聲母親為干媽。
梁曉聲哥哥的初中同學(xué)父母鬧離婚,母親臥軌自殺,少年終日以淚洗面,甚至有了輕生念頭。母親得知后,將少年接到家里住,一住就是幾個(gè)月,直至他有了監(jiān)護(hù)人。
在饑餓的年代,家里來(lái)了討飯的農(nóng)村老人,母親會(huì)恭敬地請(qǐng)老人入座,一次次地為老人添粥。
…………
對(duì)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梁曉聲始終心懷感激,“其最‘接地氣’的部分,經(jīng)千百年來(lái)向民間的輻射、傳播,直達(dá)草根階層。”他說(shuō),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以經(jīng)典“語(yǔ)錄”的形式,影響著貧困人們的心性,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等。
梁曉聲說(shuō),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關(guān)于人何以為人的部分,經(jīng)戲劇、評(píng)書(shū)、曲藝及各種各樣的民間文藝形式,較成功地起到過(guò)“文化育人”的作用。“我自幼確乎是聽(tīng)母親說(shuō)過(guò)并加以闡明的,我的母親深受其影響,在對(duì)兒女的教育中引用過(guò)、借力過(guò)。”
母親對(duì)梁曉聲的影響也體現(xiàn)在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梁曉聲說(shuō),他從不愿花精力寫(xiě)壞人有多壞。除了“天生”的壞種,呈現(xiàn)一個(gè)原本不壞的人何以做了壞事的社會(huì)原因包括教育失敗的原因,倒是他認(rèn)為值得的。“我逐漸認(rèn)識(shí)到,文學(xué)不僅要寫(xiě)人在生活中是怎樣的,還要寫(xiě)人在生活中應(yīng)該怎樣。即文藝不僅僅應(yīng)是鏡子,還應(yīng)發(fā)出作家的呼喚之聲。”
母親的善良、溫潤(rùn)、寬厚,梁曉聲在他的作品《母親》中有過(guò)描述。他說(shuō),寫(xiě)作《母親》是在當(dāng)年哈爾濱作協(xié)主席林予的一再督促下完成的。兩人在“文革”中相識(shí),林予對(duì)梁曉聲的母親極為尊敬,稱(chēng)之為“老姐姐”。他曾經(jīng)對(duì)梁曉聲說(shuō):“如果你不寫(xiě)你母親,那我可就要寫(xiě)了!”母親去世后,在辦喪事時(shí),梁曉聲驚訝地發(fā)現(xiàn),母親竟有20幾個(gè)干兒女,皆為貧困家庭的孩子。
不爭(zhēng)名利不求人的“基因遺傳”
在梁曉聲的心目中,父母都是對(duì)名利看得很透的人,他們真正主張的是平淡的人生。父親是個(gè)剛強(qiáng)的山東漢子,從不抱怨生活,也不唉聲嘆氣,且愛(ài)惜榮譽(yù),不爭(zhēng)名利。1963年,梁曉聲和哥哥一個(gè)就讀初中,一個(gè)考上大學(xué),家庭面臨著沉重的負(fù)擔(dān)。父親單位的領(lǐng)導(dǎo)在一次偶然的家訪中了解到情況,便建議梁曉聲寫(xiě)信給父親讓他向單位申請(qǐng)困難補(bǔ)助。父親探家時(shí),母親問(wèn)起才知道,申請(qǐng)根本沒(méi)交。父親說(shuō):“我是班長(zhǎng)啊,全班十幾號(hào)人,每年的補(bǔ)助是有名額的。如果名額讓我這個(gè)班長(zhǎng)占了,班里別人家再有困難怎么辦?”
“一直當(dāng)班長(zhǎng),獲獎(jiǎng)眾多,父親珍惜榮譽(yù),所以他對(duì)自己有要求了。”梁曉聲這樣認(rèn)為。
父親的那些言行,似乎化作基因也“遺傳”給了梁曉聲,因此他從未在名與利方面爭(zhēng)過(guò)。梁曉聲說(shuō),如果自己愿意,三十五六歲就可以當(dāng)上北京電影制片廠文學(xué)部主任,四十多歲就有機(jī)會(huì)當(dāng)副廠長(zhǎng),“但我不愿意,因?yàn)槲覠釔?ài)文學(xué)創(chuàng)作。”
從北京電影制片廠搬到中國(guó)兒童電影制片廠,梁曉聲沒(méi)求過(guò)人。連雙人沙發(fā)都是自己背上三樓的。“以至于當(dāng)年童影的勤雜工趙師傅詫異地對(duì)別人說(shuō),新調(diào)來(lái)的那個(gè)姓梁的,是不是在北影人緣太差了呀,怎么搬家都沒(méi)個(gè)人幫忙?”
梁曉聲不愿因個(gè)人或家人的事求人,但幫助底層人解決困難而求人,他往往可做到理直氣壯。他曾三次向老友、藝術(shù)家韓美林索過(guò)畫(huà),轉(zhuǎn)手就送給別人了——貧困者有時(shí)憑他一張畫(huà),就能度過(guò)一籌莫展的坎,“我是向韓美林實(shí)話(huà)實(shí)說(shuō)過(guò)的,他很愿意他的畫(huà)能起到那樣的作用。”
用平淡的人生觀教育兒子
梁曉聲的父母對(duì)兒女們是有些期望的。父親一生以工人階級(jí)的一員為榮,他希望兒女成為國(guó)企工人,家族成為工人之家;母親對(duì)子女們的期望比父親“理想化”一些,希望兒女可以成為中小學(xué)教師、醫(yī)生護(hù)士、工程師,但他們不追求不切實(shí)際的期望,更多的是主張平淡的人生,希望兒女善良、健康、有較穩(wěn)定的工作,在單位是表現(xiàn)良好的員工就可以了。
“父母根本不曾想過(guò)有一個(gè)兒子能成為作家。”梁曉聲說(shuō),母親與他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見(jiàn)他每次因被采訪、催稿而苦惱,往往心疼地說(shuō):“看把我兒子煩的,你不是說(shuō)你也能當(dāng)老師嗎?要不你改改行,媽支持。”
對(duì)名利看得很淡,也讓梁曉聲完全沒(méi)有望子成龍的想法。“大部分人過(guò)的是平凡的一生,我不覺(jué)得自己是一個(gè)寫(xiě)小說(shuō)的人因而自己不普通,也不認(rèn)為有一個(gè)平凡的兒子是沮喪之事。”
在梁曉聲看來(lái),理想中的家庭不能稱(chēng)之為“完美”,應(yīng)稱(chēng)之為“美滿(mǎn)”。“美滿(mǎn)的家庭主要是指成員關(guān)系情況而言的,也包括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室不在大,夠住就行;錢(qián)不在多,夠花就行;生活不必豪奢,豐衣足食足以。在此基礎(chǔ)上,家庭和睦,家人健康,榮辱與共,這就是美滿(mǎn)的家庭,并且是大多數(shù)人都可追求到的。”
梁曉聲和兒子討論過(guò)這樣一個(gè)話(huà)題:“人怎樣度過(guò)自己的一生才算是值得的?”“普通人的生活是不是幸福的,”他對(duì)兒子講:“我以為平平淡淡才是真。一個(gè)人有一份普通的工作,有一處住房,過(guò)著普通人的生活,這沒(méi)有什么可感到羞恥的。盡你所能就好了,不論結(jié)果如何,擁有快樂(lè)的人生最重要。”
“現(xiàn)在兒子早已工作了,每天擠地鐵上下班,微小單位,工資中下水平,用電腦制作‘非遺’軟件。”梁曉聲說(shuō),兒子年輕、陽(yáng)光,見(jiàn)到的人都說(shuō)兒子單純,這讓他頗為欣慰。“我相信,好文化是那種足以教人活得簡(jiǎn)單,并且也能活出愉快的文化。”
責(zé)任編輯:張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