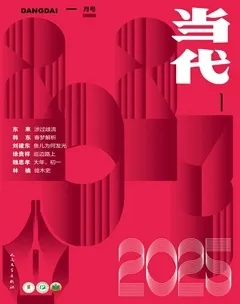文豪中的思想者
有兩類思想家,一類是“自成一體”,自己就邏輯地建立了一個(gè)宏大的體系。還有一類則是“待成一體”,卻是要等別人去為之梳理出一個(gè)思想體系。像孔子、蘇格拉底,他們甚至自己不專門撰述,而只是說出一些富有意義的話而由弟子記錄,再由后人不斷整理、闡發(fā)出他們的思想體系。當(dāng)然,值得后人如此整理的思想家的確是本身要有一個(gè)精深的思想系統(tǒng)在其話語中隱含地存在。但這里也還存在一個(gè)疑問:中國的許多思想家基本都是“待成一體”,這甚至就是中國思想的一個(gè)特殊風(fēng)格,他們不追求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的體系化,我們固然可以對(duì)他們的思想做一些系統(tǒng)的整理,但是否一定要將他們的思想做成一個(gè)百密無疏、宏大精巧的體系?這是否會(huì)加入太多的己意而扭曲他們的真正思想?
而還有一些文學(xué)家、史學(xué)家、藝術(shù)家等,他們并不以構(gòu)建一個(gè)哲學(xué)體系為己任,但人們還是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發(fā)現(xiàn)豐富深刻的思想,甚至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gè)有內(nèi)在思想邏輯——包括變化的邏輯——的系統(tǒng),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
我認(rèn)為,英國十八世紀(jì)的一代文豪塞繆爾·約翰生(Samuel Johnson,1709—1784)也是這樣一個(gè)文豪中的思想者。鮑斯威爾在他1793年給他的大為風(fēng)行的《約翰生傳》寫的“再版弁言”中說:“我已經(jīng)把這個(gè)國家約翰生化了,我想他們不僅會(huì)談?wù)摷s翰生,而且會(huì)思考約翰生。”[1]他對(duì)英國的“約翰生化”也許估計(jì)過高,但不斷地“思考約翰生”卻值得嘗試。
對(duì)于中國學(xué)者來說,約翰生是一個(gè)我們熟悉而又不太熟悉的作家。一方面,他的一些格言我們耳熟能詳,經(jīng)常引用,他是僅次于莎士比亞,其格言被人引用最多的一位作家,比如很著名的這一句:“愛國主義是無賴的最后庇護(hù)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scoundrel.)[2]但另一方面,約翰生的作品又是我們不熟悉的,他寫了很多杰出的作品,但并沒有集中于一兩本特別厚重的代表作。或可說他最龐大的作品是他編的《英語詞典》,這是第一部權(quán)威可靠的英語詞典,但這是非思想性的著作,而且,詞典教材一類書籍的命運(yùn)幾乎注定是要被超越和更新的,其中作為“經(jīng)典之作”的主要意義是歷史的意義而非現(xiàn)實(shí)的意義。
當(dāng)然,我們不熟悉他最重要的原因,可能還是他不是切合我們今天這個(gè)時(shí)代思想主流的人物。約翰生是當(dāng)時(shí)英國文壇的領(lǐng)袖,但他的時(shí)代已經(jīng)過去。當(dāng)然,在今天的世界上,總是還有不多的一些人執(zhí)著地喜歡他,研究他,世界各地有一些約翰生協(xié)會(huì),也不時(shí)會(huì)有一些新的研究著作和傳記出現(xiàn)。包括在中國,也有幾位作者在持續(xù)關(guān)注、翻譯和研究他的作品。
約翰生涉獵的領(lǐng)域甚廣,他的作品的文體就有詩歌、散文、戲劇、小說、傳記、詞典、評(píng)論等十九種之多。還有鮑斯威爾親炙其人而記錄其言行甚詳、著名的《約翰生傳》,以及他剛?cè)ナ啦痪镁统霈F(xiàn)的多種傳記和回憶錄。他所生活的時(shí)代甚至被稱為“約翰生時(shí)代”。但是,我們又的確看到,雖然對(duì)他的研究連綿不絕,但他的影響在現(xiàn)當(dāng)代的確是衰落了。他的思想看來不怎么適合后來的時(shí)代發(fā)展的主流方向,但這在我看來恰恰也是需要梳理和研究他的思想的另一個(gè)理由。最“新”的思想并不一定最“對(duì)”。思想并不總以“后出”為佳。而某種捍衛(wèi)基本常識(shí)、保守基本價(jià)值的思想雖然不那么轟動(dòng)和引領(lǐng)時(shí)潮,卻有更加持久的意義。這種“捍衛(wèi)”和“保守”恰恰也是我想揭示的他的思想的主旨。他還預(yù)先為他死后不久即出現(xiàn)的“保守主義”提供了一個(gè)人格的范型。
下面我就想結(jié)合約翰生的生活來梳理他的思想,努力揭示他的所行、所言、所思與所望。這一嘗試我想在一種人性的“欲望—情感—意志—認(rèn)知—信仰—審美”的結(jié)構(gòu)中進(jìn)行,主要考察他在尋求美的過程中對(duì)欲望和情感的處理,意志和認(rèn)知的展現(xiàn),以及對(duì)信仰的渴望,亦即我的闡述不僅會(huì)注意他的作品,也會(huì)注意他的生平。從道德哲學(xué)的角度來研究這樣一個(gè)生活如此豐富的人,不注意他的生活言行而又想求得全面深入簡(jiǎn)直是不可能的。他不僅一生坎坷,而且富于交游,他的不少思想就是見之于在俱樂部或者密友之間即興的說話,幸虧也有人詳細(xì)記錄了不少這樣的話語。約翰生作為一個(gè)極具現(xiàn)實(shí)感、不重理論,甚至反體系的思想家,不重視他的人格和思想的密切結(jié)合是難于入手對(duì)他的研究的。也正是這樣的一生,讓他的道德思考打上了一種“深具現(xiàn)實(shí)感”的印記,讓他的道德教訓(xùn)有了一種充分考慮“可行性”的特征。而他的道德觀和人生觀,也有許多觀念是從他的生活和行為中凝結(jié)出來的。
幸福與不幸
康德著名的四問,其中的兩個(gè)問題是最具道德意義的——“我們應(yīng)當(dāng)做什么”和“我們可以期望什么”。或者說,我們應(yīng)該怎樣行動(dòng)?可以對(duì)人生抱有何種期望?這涉及道德與信仰兩個(gè)方面。這兩個(gè)問題提出于十八世紀(jì)有一種特別的意義,因?yàn)槟鞘且粋€(gè)社會(huì)開始激烈轉(zhuǎn)型的時(shí)代,也許普通民眾還沒有確切的感知,但知識(shí)分子已經(jīng)有相當(dāng)?shù)念A(yù)感:或興奮或憂慮,當(dāng)然前者居多。舊的可靠根基已經(jīng)動(dòng)搖,往昔道德與上帝的緊密聯(lián)系已然削弱,上帝趨死或者說神在隱退。他們努力尋找新的行動(dòng)標(biāo)準(zhǔn)和希望,而即便是肯定傳統(tǒng)的標(biāo)準(zhǔn)和希望,也需要對(duì)時(shí)代做出回應(yīng)。
約翰生無意于哲學(xué)體系或宏大理論,但他諸多體裁的作品深含著道德意味。他崇敬莎士比亞的作品,認(rèn)為它們是深刻而豐富地反映人生和人性的鏡子,同時(shí)也認(rèn)為莎翁作品中缺少比較明確的道德評(píng)價(jià)。但這也是各人的風(fēng)格不同,并不一定就是缺點(diǎn)。要展現(xiàn)人性的豐富和深刻,描寫光明和陰暗都具有道德意義。
亞里士多德曾經(jīng)談到人生幸福的來源有三:一是來自外界的,二是來自自身的身體,三是來自自己的靈魂。叔本華的三分法則是將來自自身身體和心靈的幸福合二為一,另外兩類分別來自外界的財(cái)富以及他人和社會(huì)的評(píng)價(jià)。這里我們可以更細(xì)致地將這來源分為四類:一方面是來自意識(shí)與物質(zhì)之分的四種——前兩者是自己的心靈和外人的評(píng)價(jià),后兩者是物質(zhì)的財(cái)富和肉體的狀態(tài);另一方面是來自自己和他人(或社會(huì)環(huán)境)的四種——前兩者是自己的心靈與身體,后兩者是外部的財(cái)富和評(píng)價(jià)。
后面我們還要談到約翰生對(duì)人生追求幸福的看法。這里我們?cè)谡f明約翰生的生平和性格特點(diǎn)時(shí)也可以借助上面的劃分。幸福的來源也是不幸的來源。約翰生的一生倒是充分體現(xiàn)出這不幸的一面,也就是說經(jīng)常陷入一種身心交瘁、內(nèi)外交困的狀態(tài),而且是一種長期的逆境,尤其是在他的早年。這倒不是說他天性本身就有向著不幸和痛苦的傾向,相反,他是挺追求幸福、歡樂和友誼的,但的確也就承擔(dān)了這樣一種在不幸中奮斗的命運(yùn)。
先說約翰生的身體和心靈。似乎上天就是要磨礪這個(gè)天才,給他的磨難格外多些,他不僅很早就處于一種困境,而且是一種長期的逆境。他出生不久,他的淋巴腺就從奶媽那里感染上了肺結(jié)核病菌(瘰疬),動(dòng)了沒有麻醉的手術(shù),在臉上和脖子上留下了明顯的疤痕,而且左眼失明,左耳失聰,走路失衡,身體還會(huì)抽搐,大口喘粗氣。他的一個(gè)親戚說,在街上見到這樣一個(gè)遺棄的嬰兒都“不會(huì)撿回家來”。他身材還是魁梧的,動(dòng)作卻是笨拙的,常被人比喻為獅子或者大熊。他的心理也有抑郁的傾向,尤其是在二十歲后的兩年到五年和五十五歲左右的數(shù)年里,他兩度陷入嚴(yán)重的抑郁癥,甚至幾乎自殺。
再說外部的財(cái)富和評(píng)價(jià)。他出生的時(shí)候家境尚可,但出生時(shí)父親已經(jīng)五十二歲,母親四十歲,后來父親的書商生意破產(chǎn)。他十九歲到牛津大學(xué)讀書,讀了一年就因?yàn)橹Ц恫黄饘W(xué)費(fèi),甚至日常生活也出現(xiàn)困難而不得不輟學(xué)回家。到他二十八歲時(shí)去倫敦闖蕩,也不像他的同伴和學(xué)生加里克那樣很快出名和有錢,他到四十歲的時(shí)候還幾乎是囊中羞澀,寂寂無名。
對(duì)約翰生來說,一切讓人艷羨的東西似乎都來得太晚。他四十歲才有了自己第一篇署名發(fā)表的作品《人類愿望皆虛幻》;四十六歲才出版了自己厚重的代表作《英語詞典》,有了穩(wěn)定的名聲,并得到牛津贈(zèng)予的第一個(gè)學(xué)位;但他的收入并不多,在編完《英語詞典》之后還因?yàn)閭鶆?wù)進(jìn)過監(jiān)獄。他到五十三歲才有了自己穩(wěn)定的收入,得到了一筆王室年金。
在造成他早年困境的四種因素中,最重要的可能還是貧窮,其次是自我的身體這樣一些物質(zhì)的原因,然后才是他的心理傾向和別人的評(píng)價(jià)。由于他學(xué)習(xí)很好,知識(shí)非常豐富,他還是得到了一些人的好評(píng),并贏得了一些朋友。他居住在親戚家的時(shí)候,甚至因其智慧的談吐進(jìn)入過上流社會(huì)的社交圈。如果他一直是完全閉塞和始終貧困,我們很難說他一定能夠掙脫出來,他還是有過一些稍稍幸運(yùn)的窗口期。
當(dāng)然,最終還是要靠他自己。約翰生的確有一種不同于凡人的強(qiáng)烈個(gè)性,這就是他對(duì)自己一貫的高期許和嚴(yán)要求,或者說是在任何情況下對(duì)自我的不放松追求也不放松要求的嚴(yán)格管控。這種嚴(yán)格的自我管控的確也在某些時(shí)候造成了劇烈的心理沖突,但是,最終還是這種高度自律和自強(qiáng)將他帶出了困境。他的持之不懈的寫作,他的奴隸般的勞作——這尤其體現(xiàn)于他九年編輯《英語詞典》的苦工,當(dāng)然也有他的巨大天賦,終于將他帶出了困境,最后獲得了一種中等財(cái)富和上等名聲。
雖然約翰生經(jīng)歷過長期的逆境,但他并不認(rèn)為這都是社會(huì)造成的,而有些就是個(gè)人的偶然境遇或者性格所致。他的貧困開始主要是因?yàn)楦赣H判斷失誤而投資失敗。當(dāng)時(shí)的英國社會(huì)也已經(jīng)容有許多奮斗的機(jī)會(huì)。而他自己的創(chuàng)業(yè)失敗也有判斷失誤的原因。他在鄉(xiāng)下辦一所學(xué)校,發(fā)展開始就受到很大限制,而他談話的才能并不一定就是講課的才能,再加上他臉上的傷疤,還容易嚇著學(xué)生,所以,只招到很少的幾個(gè)學(xué)生。創(chuàng)業(yè)失敗迫使他不得不和他的一個(gè)才華橫溢的學(xué)生一起到倫敦去闖天下,這又未嘗不是他的幸運(yùn),否則他可能終身就是一位鄉(xiāng)鎮(zhèn)學(xué)校校長。他和學(xué)生加里克去了倫敦。這次他們兩個(gè)人都成功了,學(xué)生成為著名的演員,他后來成為更為著名的文學(xué)家,兩人死后都安葬于西敏寺。他的成功是因?yàn)樗麚碛芯薮蟮奶熨x,但更多的是頑強(qiáng)的奮斗精神,他絕不怨天尤人,他相信天賦終能展現(xiàn),不能的話,還是自身有缺陷——不是才能的,而是性格的缺陷。
約翰生是一個(gè)愛說話的人。他首先是一個(gè)“立言者”。他不僅寫得多,也說得多,擅長談話,又幸運(yùn)地遇到了一位忠實(shí)地記錄他的談話的鮑斯威爾。但約翰生還是一個(gè)“立德者”。他非常重視道德,甚至以“道德家”自居。他最早的詩劇《艾琳》,他的長詩《倫敦》和《人類愿望皆虛幻》,小說《拉斯海斯王子出游記》,尤其是他收錄在《漫步者》《冒險(xiǎn)者》和《閑散者》中的數(shù)百篇散文,都充滿了道德的蘊(yùn)涵。他的許多政論、他對(duì)莎士比亞的評(píng)論以及他的《詩人傳》也有許多基于道德觀點(diǎn)的批評(píng)。他認(rèn)為我們?nèi)绻麤]有美德,那么擁有再多的東西也不會(huì)幸福。而美德也并不是我們追求幸福的工具,它最多只是讓我們心安,在臨終的時(shí)候能夠交代自己。
約翰生區(qū)分人類中的多數(shù)與少數(shù)。他說:“上帝允許一些人有資格對(duì)人類知識(shí)做出增益。這類人數(shù)量極少,即使在這個(gè)特別優(yōu)秀的階層中,每個(gè)人在思想上所能增加的東西也是非常有限的。在這個(gè)大千世界里,有很多錯(cuò)誤因沒有受到指責(zé)而流行,因?yàn)閹缀鯚o人有這種天生的糾錯(cuò)能力。只有少數(shù)人能選擇適當(dāng)?shù)臋C(jī)會(huì),以自然賦予他們的天賦進(jìn)行改進(jìn)。”(《漫步者》“知識(shí)的作用”)對(duì)于絕大多數(shù)的學(xué)生來說,他們生來也沒有建立體系的能力或者說具有先進(jìn)的知識(shí),沒有任何希望超越其他人。但是,另一方面還是應(yīng)該鼓勵(lì)人,哪怕最后成功的只是少數(shù)。“虛構(gòu)的王國可建立在那些無邊際的可能性領(lǐng)域里。那里確實(shí)有成千條道路尚未開通,上萬朵鮮花等待采摘。”(《漫步者》“論模仿”)只是要記住畢達(dá)哥拉斯的一個(gè)金句:“能力與危險(xiǎn)如影隨形。”他肯定少數(shù)先驅(qū)者的作用:認(rèn)為如果沒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進(jìn)取心,敢于沖破偏見和蔑視責(zé)難,新事物就不會(huì)被嘗試。但他也鼓勵(lì)多數(shù)普通的人們,說我們每個(gè)人的責(zé)任是盡力通過自己的勤奮,去增加世代積累的知識(shí)和幸福。要增加很多,確實(shí)很少人能做到,可是,每個(gè)人都有希望做到增加一些。而且,即便是再優(yōu)秀再偉大的少數(shù)和個(gè)人,也沒有誰是一定不可缺少的。這也許是上天為了人世間可能發(fā)生的互相間的暴虐,才確立了這一任何個(gè)人的作用都不那么重要的法則。世界不會(huì)因那個(gè)人的退場(chǎng)和死亡,產(chǎn)生任何大裂口。這也包括他自己。在他的悼念儀式上,一位演講者卻根據(jù)這段話做了另一種解釋,他說約翰生走了,還是出現(xiàn)了大裂口,讓我們尋找下一個(gè)最優(yōu)秀的人,雖然無論如何不會(huì)再有和他完全一樣的人了。約翰生也反復(fù)提醒我們整個(gè)人類的局限性:征服世界的計(jì)劃是暴君的瘋狂,希望在所有科學(xué)上都達(dá)到優(yōu)秀是文人英雄的愚昧,這兩類人最終都會(huì)發(fā)現(xiàn),他們努力追求的是一種人類被拒絕達(dá)到的最高峰。不僅少數(shù)天才在認(rèn)知、理性、情感和希望上達(dá)不到盡善盡美,眾人還對(duì)少有的天才普遍感到恐懼。他甚至說人類是非常不愿意使自己變得更聰明的。
什么樣的言行一致
約翰生的現(xiàn)實(shí)感首先是由于他對(duì)人性有深刻的認(rèn)識(shí)。其次是他要致力于解決實(shí)際問題。他說懂得復(fù)雜理論體系的人們卻常常不能解決簡(jiǎn)單的生活問題。而這種現(xiàn)實(shí)感的表現(xiàn)在于,他提出的道德要求是可行的期望,他的政治立場(chǎng)也不是固守于某一黨派、某一過去的觀點(diǎn)。博爾赫斯有一次曾經(jīng)和人聊起“擱置懷疑”的話題,他堅(jiān)持認(rèn)為約翰生在這方面是先行者,認(rèn)為“約翰生主要的優(yōu)點(diǎn)就在于他看清事實(shí)的能力”[3]。
楊絳談到,簡(jiǎn)·奧斯汀最愛讀約翰生的作品,欽佩之至,被稱為“約翰生博士精神上的女兒”。她承襲了他的“實(shí)踐智慧”,有通情達(dá)理、明辨是非的頭腦。[4]范存忠中肯地評(píng)論說:“約翰生對(duì)于人生有一個(gè)基本的態(tài)度,就是死命地抓住現(xiàn)實(shí),一刻不肯放松。……他的頭腦是倫理的,不是哲學(xué)的;是實(shí)用的,不是唯理的;是重經(jīng)驗(yàn)的,而厭惡冥想的——是當(dāng)時(shí)標(biāo)準(zhǔn)英國人的頭腦——所以有人說他是英國的代表人物。”[5]
約翰生所考慮的道德“可行性”首先是對(duì)自己的,亦即你自己是否能夠做到。你想倡導(dǎo)一種道德嗎,那么,首先你自己是不是準(zhǔn)備這樣做?而且,你只要努力,也是能夠履行這種道德要求的話,你是不是馬上身體力行?如果你自己并不準(zhǔn)備實(shí)行,那就是虛偽;如果你自己想做但其實(shí)也做不到,那就很可能是空談的高調(diào)。
約翰生講述過他在餐桌上與一位主張平等主義的貴婦麥考利夫人交談的故事。他說:“夫人,我如今要洗心革面,改換成你的思維方式了。我如今開始深信所有人類都是平等的,夫人,我要給你一個(gè)確實(shí)的證據(jù),來證明我是認(rèn)真的。”他指著旁邊一位伺候他們用餐的仆人說:“這位公民,你的仆人,有理智,有禮貌,有教養(yǎng),我希望能讓他坐下來和我們一起用餐。”這自然讓麥考利夫人很尷尬,他說,從那以后,“她就再也不喜歡我了。”[6]
倡導(dǎo)者是首先需要這樣做的。其次,這種道德要求也還要考慮整個(gè)社會(huì)。如果這個(gè)社會(huì)是等級(jí)社會(huì),那么對(duì)上層應(yīng)該要求更嚴(yán);如果這個(gè)社會(huì)是平等社會(huì),那么就要考慮這個(gè)社會(huì)上的所有人,至少大多數(shù)人,是否都具有這種道德意愿,也基本具有實(shí)行這種道德的能力。約翰生認(rèn)為:“以道理教人美德好處的人,應(yīng)用自己的榜樣去證明它的可行。”(《漫步者》)他自己在這方面做得也的確比一般人要好得多。道德理論家并沒有讓人在實(shí)踐中對(duì)自己特別網(wǎng)開一面的特權(quán)——我提倡了,似乎我就可以豁免了。約翰生指出:理論與實(shí)踐本身就有一種差距。提倡理論的人可能用心高尚,人們應(yīng)該記住,實(shí)踐中可能會(huì)有許多障礙阻攔我們?nèi)?shí)踐我個(gè)人倡導(dǎo)的道德。一個(gè)人提出一種高的道德理論或主張是容易的,而現(xiàn)實(shí)中生活的人們,他們有自己的熱情,要接觸其他的人,實(shí)踐這種道德就可能會(huì)遇到很大的困難。人們即使保持最高度的警醒,也不能確保每一天都過得純潔無瑕;即使投入最大的思想上的努力,也很少能到達(dá)深思熟慮的德行頂峰。這就是人的局限性,主要是一種普遍實(shí)踐的局限性。約翰生認(rèn)為,雖然人們提出“完美的觀念”還是有必要的,可以讓我們有一個(gè)努力的方向。但一定要體會(huì)蕓蕓眾生的種種難處。而且,即便是完美的道德觀念也同時(shí)應(yīng)該是現(xiàn)實(shí)的,既不是那種天使的理想,也不超越現(xiàn)實(shí)的可能性。一般人對(duì)那些他們認(rèn)為不可信、做不到的事情是不會(huì)去模仿的。
所以,約翰生自己的嚴(yán)格自律和他倡導(dǎo)的社會(huì)道德還是有差距的,他對(duì)社會(huì)的道德要求并沒有那么高,而且對(duì)他人表現(xiàn)出一種寬容,甚至有些說法非常低調(diào)。他說文人(尤其寒士街上的文人)寫作不考慮錢那就是一個(gè)傻瓜。當(dāng)然,這并不是唯一的動(dòng)機(jī)。他也談到寫作的目的就是要讓人學(xué)會(huì)享受和學(xué)會(huì)忍受,而因?yàn)槿松纯嗌醵喽鴼g樂甚少,作品最好還要讓人愉悅。當(dāng)然,這其中也應(yīng)該包含有道德的目的。不過,博爾赫斯說藝術(shù)家寫作起來,常常會(huì)忘記這些目的,而讀者也不太會(huì)考慮作者的寫作動(dòng)機(jī)。重要的依憑還是經(jīng)驗(yàn)。約翰生也重視經(jīng)驗(yàn),說我們現(xiàn)在的作家需要他把從個(gè)人孤獨(dú)奮斗中獲得的經(jīng)驗(yàn)和從書本中能夠得到的知識(shí)結(jié)合起來,還要求他必須具有普遍的常識(shí),能準(zhǔn)確地觀察活生生的世界。也就是說,道德作家除了從書本得來的知識(shí),還應(yīng)該有經(jīng)驗(yàn)的依托:一是自己的個(gè)人經(jīng)驗(yàn)——按英文“經(jīng)驗(yàn)”的拉丁語詞根的本義,這常常是個(gè)人要通過危險(xiǎn)和考驗(yàn)獲得的產(chǎn)物;二是表現(xiàn)為“常識(shí)”的普遍的人類經(jīng)驗(yàn)。
約翰生不僅是思想上重視道德,也律己甚嚴(yán),但他對(duì)人的文字和談話卻從來不高高在上,而是以人群中的道德家的形象出現(xiàn)。我們可以先討論一下從英國近代啟蒙早期先驅(qū)到十八世紀(jì)亞當(dāng)·斯密、休謨都特別看重的道德的基本情感——“同情”。約翰生低調(diào)地認(rèn)為同情并不是出自人的本性,因?yàn)槲覀儠?huì)看到,原始人和孩子都沒有多少同情(這兩者是從人類與個(gè)體接近人的自然本性的),甚至相當(dāng)無情。他說我們自己坐在馬車上,如果馬車夫突然狂打馬匹,我們可能會(huì)感到不安,但是一般也不會(huì)阻止車夫,讓馬車停止前進(jìn)。他甚至也談到孟子所舉的典型的惻隱之心的類似例證,說如果我們看到一個(gè)人落入深井會(huì)想救他,但如果救他的代價(jià)太大,會(huì)給我們帶來生命危險(xiǎn),一般人大概也不會(huì)出手。他之所以這樣說,這里當(dāng)然可能有他談話中的夸大和刺激——為了語言鋒利和震撼,約翰生在談話中有時(shí)是會(huì)這樣做的。但更重要和更真實(shí)的原因,約翰生在這里大概也是重“行”,看有沒有行動(dòng),但是我們所說的“同情”說的是“心”,是心里的一種情感。人看到別人的痛苦和災(zāi)難心里有不安,想去救,就已經(jīng)說明人有惻隱之心了,這就是道德的動(dòng)力源頭,至于這一同情心是否能變成行動(dòng),或就是因?yàn)槟承┰蚝蜅l件受到阻礙而變不成行動(dòng),并不影響這種惻隱之心的本然善和它是普遍的人類共性。但約翰生主要是從行動(dòng)與否來考慮同情,所以他不輕許人的本性以同情。
我們還可繼續(xù)察看約翰生為什么會(huì)不那么重視同情。這可能是和他的自身經(jīng)歷有關(guān),是因?yàn)樗匾暳硗庖环N德性——不嬌慣自己的自強(qiáng)自立。如約翰生傳記的作者貝特指出:約翰生一生都十分警惕病痛可能把一個(gè)人慣壞。晚年他一次中風(fēng)后說:“疾病使人變得很自私。”思雷爾夫人也引用了他經(jīng)常說的一句話:“病人很容易變成無賴。”他最害怕的不是病痛所造成的痛苦和癱瘓,而是疾病會(huì)不經(jīng)意間消磨人的斗志和意志。這來自他的個(gè)人經(jīng)驗(yàn)和警惕。他曾向好友霍金斯透露說,他生活中就“不知道完全沒有病痛的感覺是什么樣的”[7]。一種拒絕他人的幫助、力求自我解決的性格在他早年就表現(xiàn)出來了,乃至表現(xiàn)極端:在他三四歲讀幼兒學(xué)校的時(shí)候,因?yàn)樗纳眢w不好,且眼睛看不清有陰溝的道路,一位創(chuàng)辦這所學(xué)校的女士悄悄地在后面跟著他,而他突然發(fā)現(xiàn)之后,竟然拳打腳踢地將她趕走;在他讀牛津大學(xué)的時(shí)候,他的破鞋已經(jīng)穿得很爛了,有人悄悄將一雙新鞋放在他的宿舍門口,他發(fā)現(xiàn)后也氣得將新鞋拋掉。
約翰生對(duì)接受別人的同情很苛刻。但是,這并不是說約翰生對(duì)別人沒有同情,他在同情的行為方面所做的甚至遠(yuǎn)遠(yuǎn)超出一般人。他許多次為援助別人匿名寫稿。他生活寬裕之后所租住的大宅子里,長年住著幾位他收留的人:一個(gè)雙目失明的女人,一個(gè)專為窮人看病的無執(zhí)照醫(yī)生,一位曾陪伴其亡妻的女子,一名洗心革面的妓女。還有一位黑人男仆巴伯,他十歲就來到約翰生這里,約翰生送巴伯上學(xué),為他脫離船上的苦役求情,最后在遺囑中留給巴伯每年七十英鎊的年金。
人們一般都譴責(zé)言行不一。但這種譴責(zé)多是指行不如言,所言甚為道德高尚,但自己實(shí)際做不到,甚至不去做。約翰生卻也有一種“言行不一”,他這種言行不一卻是言不如行,亦即他對(duì)外的言說往往是低調(diào)的,但自己做得卻要比這些言說更多更好。這也表現(xiàn)了他一種寬以待人、嚴(yán)以責(zé)己的特點(diǎn)。言說往往是對(duì)著外界的,是希望(常常還是要求)別人或者說普遍要求人們應(yīng)當(dāng)怎樣行為,而行動(dòng)是自己的。
我們當(dāng)然追求道德上的言行一致,但肯定也不能達(dá)到絕對(duì)的平衡,那么,一種不平衡與其說是“言過于行”就不如“行過于言”。這是基于對(duì)人性的深深認(rèn)識(shí),是考慮到道德基于人性的可行性,是對(duì)人類社會(huì)有一種真正的現(xiàn)實(shí)感,也是來自對(duì)人我之別的區(qū)分認(rèn)識(shí)。真正的道德從來都是要求從自己做起的,也是要求自己的行為和自己主張和宣傳的言論一致的,甚至是一種超前的、示范的一致,是一種更加嚴(yán)格要求自己的一致。反躬自省自己是否能做到也是一種驗(yàn)證道德理論的一個(gè)很好的試金石。
處理欲望
道德實(shí)踐的重要問題莫過于如何處理與自己伴隨一生的欲望了。我們?nèi)绾慰创吞幚砣松械挠@涉及對(duì)人的本性和人生目標(biāo)的看法:欲望是人性中本有的嗎?是否也是我們?nèi)松匦璧模康覀兪遣皇且酥扑吭鯓涌酥疲恐饕揽渴裁纯酥疲克軌蚯宄蓛魡幔可踔劣斜匾绱吮磺宄龁幔康鹊取?/p>
這里也許要稍稍注意和區(qū)分一下“希望”和“欲望”。希望總是要有的,約翰生說:“有希望,才會(huì)有奮斗。”但是,希望和欲望又不是那么好分的,它們常常合在一起,甚至本來就是混在一起的,許多人的希望也就止于欲望或只是欲望。我們常常只是給它們,或者其中我們看來健全的一部分一個(gè)較好聽的名稱——“希望”,給其中一部分一個(gè)不那么好聽的名稱——“欲望”。狹義的“欲望”也許可以分為物欲(利益)和體欲(食色)。對(duì)前一種希望,約翰生是有保留地贊成的。無希望就無以談人生。從反面甚至可以說,約翰生的一生就是努力免除絕望。這方式一是不拒斥乃至抓住人世間不多的歡樂,二是寄望于彼世的天堂。
對(duì)塵世的欲望,尤其是他人的、多數(shù)的、大眾的欲望,約翰生并不大聲批評(píng)和譴責(zé)。許多理論家都嚴(yán)厲譴責(zé)社會(huì)的物欲,甚至贊美貧窮,從貧窮中覓出快樂,但在約翰生看來,他們用許多證據(jù)說貧窮不是一個(gè)壞東西,但恰恰說明貧窮就是一個(gè)壞東西。他希望所有人都能過上一種體面的、富裕的生活。約翰生自己親身經(jīng)歷過長期的貧困,他有資格說這個(gè)話。他也曾為了妻子、母親而努力掙錢,這來自他的責(zé)任感,也許還有對(duì)親人的一種愧疚。他對(duì)朋友的物欲和體欲也是相當(dāng)寬容。但他自己的物欲的確還是淡薄,對(duì)自己的體欲更是克制。用一句俗話來說就是“嚴(yán)以責(zé)己,寬以待人”。他說他對(duì)人類了解得越多,對(duì)他們的期待就越低,現(xiàn)在我叫一個(gè)人“好人”,依據(jù)的標(biāo)準(zhǔn)比以前寬松許多。
約翰生自己是努力管控自己的欲望的。他是追求歡樂的,也喜歡喝酒,但是后來戒酒。而最明顯的、最長期的自律則是他對(duì)情欲的自律。他并不是沒有這種生理沖動(dòng)和欲望,他也有許多這樣的方便和機(jī)會(huì)。鮑斯威爾的《約翰生傳》出版后,有一個(gè)故事廣為人知,這個(gè)故事提到約翰生對(duì)他的好友劇院經(jīng)理加里克說過的一番話:“大衛(wèi),我不會(huì)再來后臺(tái)了,你那些女演員的長絲襪和雪白的胸部讓我心猿意馬,難以把持。”一位常和他深夜談話的夫人說,他是多情的,但控制住了自己的激情。約翰生對(duì)自己這方面的自律甚至也是嚴(yán)格到了常人難解的地步。他的年輕摯友、性生活放蕩的鮑斯威爾很好奇約翰生的性生活,多方打聽調(diào)查,他懷疑,但卻還是沒有發(fā)現(xiàn)約翰生的性緋聞證據(jù)。
約翰生強(qiáng)調(diào)一個(gè)人的志向和斗志,這里面也包含著欲望或希望。這些對(duì)創(chuàng)造偉大的事業(yè)或優(yōu)秀的成果都非常有必要,但這種志向和行動(dòng)也確實(shí)又很容易被過分乃至放縱的欲望所損害。但是,我們的確注意到,總體上約翰生對(duì)人們追求希望或欲望的活動(dòng)是比較悲觀的。他不說人是從一個(gè)滿足走向另一個(gè)滿足,而是說人是從一個(gè)欲望走向另一個(gè)欲望。雖然這可能是一回事。人追求實(shí)現(xiàn)自己的一個(gè)欲望,如果事成則會(huì)感到滿足(但也可能不成,那就更苦惱了),但即便事成,這滿足也是短暫的,馬上他又要追逐另一個(gè)欲望。否則他就會(huì)感到空虛無聊。約翰生解決自己的精神抑郁的一個(gè)辦法是通過工作,這也是一種“分心”。如果我們強(qiáng)調(diào)人生是從一個(gè)滿足走向一個(gè)滿足,從一個(gè)快樂走向另一個(gè)快樂,那是一種樂觀的說法;像約翰生那樣強(qiáng)調(diào)人只是從一個(gè)欲望走向另一個(gè)欲望,永無止境,永不停息,永難滿足,那就比較悲觀了。以后叔本華對(duì)此有哲學(xué)上的系統(tǒng)闡述。
約翰生還注意到,人的欲望并不是實(shí)際的,而經(jīng)常是想象出來的。借用他使用的一個(gè)概念,那就是一種“想象的饑渴”(the hunger of imagenation),實(shí)際自己并不饑渴,或者說是一種“想象中的匱乏”“想象中的缺少”。和動(dòng)物不同,人會(huì)不斷地幻想出無數(shù)自己所缺少的東西,還不滿足的東西。他舉金字塔為例,認(rèn)為它毫無實(shí)用的目的,那只能說是滿足了帝王永遠(yuǎn)偉大榮光的想象。這種“想象的饑渴”一是指向未來,總希望未來能得到更多的利益;一是指向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總覺得別人得到的東西自己也就應(yīng)該得到。不過,對(duì)于單純屬于自己利益的謀求,只要在正當(dāng)手段的范圍內(nèi),約翰生并不怎么批評(píng)。他特別譴責(zé)的是損人利己,一種即便不利己也要損人的嫉妒。在他看來,嫉妒幾乎是一種最大的惡德。
約翰生將嫉妒與謀求自我利益的物欲進(jìn)行比較。欲望是自己想得到,嫉妒卻是不希望別人得到。但高于平均線的權(quán)、錢、名始終是少數(shù)人擁有的,這就會(huì)引起永久的傷害和敵意。雖然利益有最強(qiáng)大和最廣泛的影響。但求利也有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積極作用,嫉妒則是純粹的惡。約翰生相信相互關(guān)愛仁慈的偉大法則,常被嫉妒而非利益所違背。嫉妒的帝國是無任何限制的。利益追求總是盯著物質(zhì),而嫉妒則是全面的。物質(zhì)的東西總是還可以共享,但非物質(zhì)的一些東西則無法共享,比如高度的名望、愛護(hù)和尊重。而在這些領(lǐng)域內(nèi)也照樣會(huì)產(chǎn)生嫉妒。謀求自己的利益總是要有所付出,嫉妒卻不需要什么付出,也沒有什么危險(xiǎn)。散布懷疑、編造誹謗、宣傳丑聞,既不需要辛勞,也不需要鼓勵(lì)。嫉妒幾乎是唯一的惡習(xí),在任何時(shí)代和任何地方都存在,也是唯一這樣一種情緒——永遠(yuǎn)不會(huì)因?yàn)闆]有刺激就消停下來。嫉妒在所有邪惡之上,不與人類社會(huì)的個(gè)性和諧。雖然嫉妒其實(shí)是承認(rèn)了別人的優(yōu)秀,但它用卑劣的手段追求可恨的目的,渴望的與其說是自己的幸福,不如說是另一個(gè)人的痛苦。也就是說,自我謀利可能導(dǎo)致使用不正當(dāng)?shù)氖侄危哪康谋旧韰s不是不正當(dāng)?shù)模蛘呖梢哉f是道德上中性的,而嫉妒不僅在手段,在目的上也是邪惡的。但如果人們認(rèn)識(shí)到嫉妒的邪惡,嫉妒也是不難糾正的:要避免嫉妒,并不需要一定成為英雄或圣人,而是立足于保持一個(gè)人的尊嚴(yán)即可。[8]
婚戀、家庭與友誼
約翰生很重視婚姻和家庭。他的一句名言是:“家居的快樂,是所有志向的最終目標(biāo),是所有事業(yè)的勞苦的終點(diǎn)。”他自己只結(jié)過一次婚,但后來也在深厚的友誼中感受到“新家”的快樂。他結(jié)識(shí)了待他如親人的思雷爾夫婦,也建立了一個(gè)文學(xué)俱樂部,并在他自己的大屋房客中也感受到親情。
約翰生二十六歲時(shí)和比他大二十一歲的寡婦伊麗莎白結(jié)婚。據(jù)說這位夫人看重他,是因?yàn)橛X得他是“一位最睿智的人”。婚后感情也很好,但據(jù)說后來因?yàn)榉蛉说纳眢w也不同房,他們也沒有孩子。他四十三歲時(shí)這位他一生唯一的太太就去世了。約翰生一直很懷念她,沒有再婚。當(dāng)然,這并不意味著他不愿與女性交往,他還是很希望生活在一種女性溫柔關(guān)照和感情智慧交流的氛圍之中,但不再談婚論娶,這或許也是因?yàn)闆]有很合適的機(jī)會(huì)。他曾經(jīng)心儀的一位女性卡思比不久就去世了。
約翰生在他唯一的一次婚戀中也表現(xiàn)了一種獨(dú)立的男子氣概。他覺得自己在心理上比他妻子更強(qiáng),并不逢迎。他第一次就那樣衣衫襤褸、不修邊幅地去見她,以致她的女兒都覺得他形象可怕。他就保持自己的本色,而看中他的夫人肯定不是因?yàn)樗南嗝玻皇撬呢?cái)富——他那時(shí)窮得叮當(dāng)響——但依然和他結(jié)婚,說明她在看人方面還是很有眼力。婚后她盡數(shù)拿出她的資產(chǎn)來支持他辦學(xué),這也是后來約翰生努力寫作為妻子掙錢,讓她到海邊過一種較好的生活的一個(gè)動(dòng)因。
他們互相吸引。她所重視的是他的睿智。她的年齡比他大,但心理或精神年齡其實(shí)還是比他小。但后來這一現(xiàn)實(shí)的情況——年齡和身體的差距,在她接近五十多歲的時(shí)候還是顯示出來了。但她和他的感情還是始終真摯的。他對(duì)她也一直有愧疚,也擔(dān)心在她死后——除了上帝的眼睛,好像還有一雙眼睛在看著他。
約翰生有很多朋友,甚至后來非常著名的文學(xué)俱樂部也是朋友為排解他的抑郁癥而建立的。里面有當(dāng)時(shí)一些最優(yōu)秀的文化名人。但我們這里還是主要談聯(lián)系于家庭生活的友誼,這方面他與思雷爾夫婦的關(guān)系特別突出。思雷爾夫人和她的丈夫在尋求與約翰生的友誼上一直是非常積極主動(dòng)的。后來約翰生經(jīng)常住在他們的家里。他們夫妻也在與約翰生的交往中得到了很大的樂趣。約翰生不僅自己吸引人,他還吸引了倫敦的文化名人來到她家的沙龍。她那面也有一些優(yōu)雅和智力超群的女性。所以,約翰生也得到很多,他第一次得到這么多溫柔的,也可以在智力上匹敵的女性的關(guān)懷乃至崇拜。雖然一直關(guān)照和支持他的思雷爾夫人在其丈夫去世之后嫁給了她的所愛——一位意大利家庭音樂教師,于是,和約翰生的關(guān)系變得疏遠(yuǎn),這讓約翰生感到相當(dāng)失落,雖然他們最初的通信有一些誤解,但約翰生還是有尊嚴(yán)地,也給對(duì)方以尊嚴(yán)地處理了這一關(guān)系的結(jié)束。在某種意義上,雖然結(jié)局不是很圓滿,但他的婚姻還是婚姻的一個(gè)典范,友誼也是友誼的一個(gè)典范,其中包含著真摯、自律、尊嚴(yán)和得體。
約翰生反對(duì)家庭中父母對(duì)兒女的專制,認(rèn)為年輕人對(duì)自我和世界不同于父輩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說來自家庭內(nèi)實(shí)施的暴力是危險(xiǎn)和可憎的,這種殘暴是在尊敬的父母權(quán)力名下的專制。這種父母暴君與帝王暴君的區(qū)別只在他們管轄的范圍大小和他們奴隸數(shù)量的多少。他在《王子出游記》中談道:兒女和父母之間,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意見自然是不一致的。他們雙方各有各的希冀和經(jīng)歷,各有各的希望和失望。子女們?cè)趺茨芟嘈鸥改傅臄嘌阅兀康磥碛植环磳?duì)學(xué)校對(duì)學(xué)生的體罰,他有點(diǎn)調(diào)侃地說他自己的優(yōu)美拉丁文和希臘文能力是經(jīng)過鞭打才學(xué)會(huì)的,鞭笞是將一門語言灌輸進(jìn)男孩腦袋的最好方式。
在兩性能力的問題上,約翰生認(rèn)為,由于寫作能力主要為男性壟斷,女人就總是背上使這個(gè)世界痛苦不幸的罵名并受到責(zé)怪。他在生活中很尊重女性,也很支持女性寫作,喜歡和聰明優(yōu)雅的女性諸如“藍(lán)襪子”們交往。在他的第一部作品,詩劇《艾琳》中,女主人公如此抗議道:“難道我們女人就沒有廣闊的思想,沒有啟人的機(jī)智,沒有深邃的理智?”他還認(rèn)為:既然女人在很大程度上有諸多天然的不幸,就不能再給她們?cè)黾油纯嗔耍屗齻兊拿利愐鹑藗兊牟毮浚齻兊奈难炮A得人們的贊美。約翰生尤其譴責(zé)家暴,說他無法容忍男人對(duì)女人們一邊是信誓旦旦,另一邊是拳打腳踢。他憐憫那些被丈夫用權(quán)威和暴力對(duì)待的女性。
約翰生對(duì)是獨(dú)身好還是婚姻好的問題沒有立即下明確的斷語,他說結(jié)婚的人羨慕單身狀態(tài)的輕松和自由;而單身的人想趕緊結(jié)婚來消除孤獨(dú)寂寞的煩惱。但他指出,不要忘記,懷念以前獨(dú)身的日子,其實(shí)也是懷念過去那年輕的日子,懷念青春時(shí)期那身體健康、充滿活力和希望的日子。看來他還是更傾向于結(jié)婚,甚至認(rèn)為當(dāng)妻子去世或者離婚之后,當(dāng)事人雖然獲得了自由,但卻還是寧愿放棄這自由而再次結(jié)婚。這就說明他其實(shí)還是感覺到了婚姻的好處。他舉了兩個(gè)反面的例子,一個(gè)是純粹為了獲得巨大的財(cái)富而結(jié)婚,一個(gè)是一見鐘情而結(jié)婚。他不愿意將愛情婚姻過于浪漫化和理想化,甚至認(rèn)為沒有那種天生一對(duì)一的、非你不娶或非你不嫁的唯一良偶,在他看來,固然會(huì)有配偶的好壞差別,但選擇的范圍還是相當(dāng)寬廣,當(dāng)有人問他如果沒有找到最好的配偶,是不是還可以找到五十位也還適合自己的佳偶,他的回答是有五萬人都還適合你。他甚至認(rèn)為婚前不見面的婚姻也還不錯(cuò),因?yàn)殡p方就不會(huì)有欺瞞——即雙方盡量表現(xiàn)自己的優(yōu)點(diǎn),掩蓋自己的缺點(diǎn)也是一種欺瞞,這樣的婚姻有時(shí)就還不如婚前未見面的婚姻。但他似乎也不太贊同父母包辦,認(rèn)為絕不可為防止自由的濫用,就以合法名義壓制生命。他希望女性貞潔,但看來更多的還是出于對(duì)財(cái)產(chǎn)繼承權(quán)不混亂的考慮。在他看來,婚姻最重要的是情感的投入,互相信任和美德,尤其美德是婚姻應(yīng)該考慮的最優(yōu)先事項(xiàng)。他不同意人們似乎要努力去尋覓世間最適合自己的“唯一的一人”才能結(jié)婚,這太難了,甚至可能太自我了。我們也許可以說他更重視的是“唯一的一次”,即把婚姻看作“終身的相許”。約翰生希望人們不要?jiǎng)虞m就抱怨自己的婚姻。他說這可能是由于他們不知道別人的婚姻。就像有些人動(dòng)輒抱怨自己的職業(yè)一樣,是因?yàn)樗麄儾⒉恢绖e人的職業(yè)。人都說自己的狀態(tài)糟糕,覺得別人的情況更好,其實(shí)他是不了解其他人。只為金錢而結(jié)婚的人,其惡無比;只為戀愛而結(jié)婚的人,其愚無比。
約翰生認(rèn)為,過度的浪漫幻想會(huì)影響人們真實(shí)的幸福。讓自己迷失在對(duì)未來的幻想中,以至于人們?yōu)榱四怯肋h(yuǎn)也達(dá)不到的理想,會(huì)忘記在自己現(xiàn)有的能力下適當(dāng)?shù)叵硎苎矍暗臅r(shí)光。但是,幻想未來這一思考特性,看來又是人類不可避免的狀態(tài)。人總是會(huì)去發(fā)現(xiàn)新的行為動(dòng)機(jī),新的恐懼、興奮、欲望和誘惑。但至少,人類要不斷地調(diào)整自己對(duì)未來的期望。人類是有某種共同性的,有大致相同的一些欲望和動(dòng)機(jī),這集中在一些基本的領(lǐng)域,比如對(duì)物質(zhì)的需求和身體的關(guān)照,對(duì)安全的考慮和自由活動(dòng)空間的保證。但是,在比較高層的,比如婚戀的領(lǐng)域,就越來越分化,出現(xiàn)諸多差異性了。就像人都有焦慮和痛苦,也有滿足和快樂,這就像約翰生說同樣是滿足,但幸福則不同,如鮑斯威爾引一位牧師說的話強(qiáng)調(diào)的那樣,即便都是斟滿酒的“滿足”,但卻有大杯和小杯的差異。但這似乎只是說到了量的差異,后來功利主義者邊沁也是注意量,密爾則談到了滿足性質(zhì)的不同,甚至說蘇格拉底的不滿要?jiǎng)龠^豬的滿足。
完美的幸福
在約翰生看來,人難以求得完滿的幸福。甚至德性也不能使人幸福,或者用其《王子出游記》中的一個(gè)人物的話來說:完美的德行是不是能換得完美的幸福,在這個(gè)塵世并不能得到證實(shí)。一切自然的災(zāi)難和幾乎所有政治方面的禍患會(huì)發(fā)生在壞人身上,也會(huì)發(fā)生在好人身上。德性只能給人以良心的安寧,一種將來情況會(huì)好轉(zhuǎn)的穩(wěn)定的前景。這種前景也許會(huì)讓我們更有耐心忍受災(zāi)禍。約翰生的第一部署名作品、他的長詩《人類愿望皆虛幻》,他最流行的小說《王子出游記》,主題都是人追求幸福的愿望是達(dá)不到的。曾經(jīng)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給他以極大關(guān)懷和支持的赫斯特·思雷爾夫人說:“生命空虛這個(gè)信條,在約翰生先生的頭腦中根深蒂固,經(jīng)過反復(fù)強(qiáng)化后,變成了他最喜愛的命題,而他推理的總體思路通常導(dǎo)向這一點(diǎn)。”(《重返昨日世界》)遍布他作品的確實(shí)是這個(gè)主題:生命的空虛很可怖,除非強(qiáng)行填滿——最好是用建設(shè)性的興趣,如果沒有,那就用任何能分心的事物。
于是,對(duì)人類命運(yùn)的這種看法將人與信仰,與超越的存在聯(lián)系起來。究竟是認(rèn)為人生虛幻空洞的看法推動(dòng)人們走向宗教信仰,還是宗教信仰會(huì)導(dǎo)致人們持一種人生虛幻空洞的看法?兩者誰更是初始動(dòng)因殊難回答,但至少這兩者是密切聯(lián)系的。但在約翰生那里,有一個(gè)明顯的特征是,他不僅僅是將塵世看作一段無關(guān)緊要的旅程,只是消極地等待來世的到臨,或者過一種修道士或苦行僧的日子,而是積極地投入現(xiàn)實(shí)的生活,享受普通的歡樂,同時(shí)也以最嚴(yán)格的道德來規(guī)范自己的心靈和行為。他的人生觀和道德觀是一種深具現(xiàn)實(shí)感的人生觀和道德觀。他關(guān)心社會(huì)、政治和人類文明,他追求人世間不多的歡樂,享受愛情和友誼,但他也始終表里如一、言行合一地遵循道德的戒律。直到最后時(shí)刻的來臨。他不相信不太信神的休謨能夠安詳?shù)仉x開這個(gè)世界。
約翰生在他的文字中并不怎么引《圣經(jīng)》或神學(xué)的話語。他自己也在生命的早期發(fā)生過動(dòng)搖,禮拜日他不愿去教堂做禮拜,而是偷跑到野外看書。直到他在牛津讀到一本威廉·勞(William Law)寫的書——《喚起神圣的使命》,此后就堅(jiān)定不移。他是一個(gè)英國的國教徒,他覺得天主教過于拘泥形式禮儀,而像清教又過于丟棄形式禮儀,但是,在他看來,如果改宗的話,還是由新教轉(zhuǎn)為天主教徒更為可取。不過,他認(rèn)為,這些教派的教義其實(shí)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它們的分歧其實(shí)主要是政治上而非教義上的。這也反映出他的一種現(xiàn)實(shí)主義態(tài)度。
在約翰生那里,基督教義的四個(gè)詞——死亡、審判、天堂、地獄——被他牢牢銘記在心。他最深的恐懼是對(duì)被判下地獄的恐懼。在《漫步者》中,他提醒讀者要心存足夠的恐懼: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懸在永世毀滅的深淵之上,維系自己的不過是一條生命之線,而這條線必將很快因自己的軟弱斷裂,可是,環(huán)顧四周的時(shí)候,他們?nèi)匀徊粫?huì)因?yàn)榭謶侄澏叮粫?huì)急于尋找安身之所。
人無論如何得控制自己的欲望,如何控制?能僅僅靠理性嗎?對(duì)約翰生來說,除了理性的約束之外,更重要的是信仰的支持,尤其是人生的空虛感和對(duì)死亡的恐懼。他認(rèn)為經(jīng)常嚴(yán)肅地思考那個(gè)終止我們的所有計(jì)劃和剝奪我們的所有物的死亡時(shí)刻,確實(shí)能讓我們以公平和理性來最有效地規(guī)范我們的日常生活。人要通過死亡來警醒生活。這并不是為了死,而是為了生。約翰生說,重要的不是我們要考慮如何死,而是要考慮如何活。生和死、此岸和彼岸總是要結(jié)合在一起。
在約翰生那里,道德是顯露的,信仰是深藏的。道德是深具現(xiàn)實(shí)感的,信仰則是極其高遠(yuǎn)的,它不僅是面向未來,而且是面向永恒。但只要人生在世,這對(duì)彼岸的信仰又始終發(fā)出對(duì)此生的呼語。約翰生持有一種深具現(xiàn)實(shí)感的道德觀,但是,這種現(xiàn)實(shí)感并不是引領(lǐng)時(shí)代潮流的,因其現(xiàn)實(shí)感的核心是對(duì)一種真實(shí)人性的認(rèn)識(shí),而時(shí)代的主流思潮卻開始離這真實(shí)的人性越來越遠(yuǎn)。
責(zé)任編輯:王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