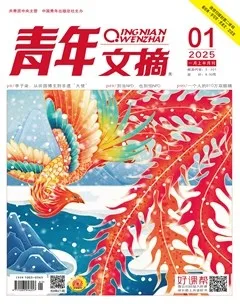谷川俊太郎:我把活著喜歡過了

一
很多人從《詩遇上歌》這張專輯開始聽我的音樂,尤其是里面那首《春的臨終》。詩的作者是谷川俊太郎,他被公認為最生動和最具代表性的當代日本詩人,“生命”“生活”和“人性”是他書寫的主題。
1931 年,谷川俊太郎生于日本東京,17 歲時,正癡迷于組裝收音機,而辦雜志的友人的一句話,讓他開始嘗試文學創作。
他的父親是谷川徹三,日本著名哲學家兼法政大學校長。他把自己創作的詩歌給父親看,父親通過作家好友三好達治,把谷川俊太郎的作品推薦給了《文學界》雜志,刊登發表后,谷川的詩獲得巨大反響,從此一舉成名。他為宮崎駿、手冢治蟲的動畫作詞,給荒木經惟的攝影集和佐野洋子的畫配詩,他影響了村上春樹、大江健三郎、北島等無數人,曾多次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諾獎作家大江健三郎曾直言,自己年輕時曾立志當一名詩人,可在見到谷川的詩歌才華之后,便放棄了這一夢想。
1952 年,21 歲的谷川俊太郎出版首部詩集《二十億光年的孤獨》,寫下那句意味深遠的“萬有引力/是相互吸引孤獨的力”,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宇宙詩人”。他的詩歌風格,是生動的、鮮活的,似乎是想盡量避免那些嚴肅而煩瑣的修辭,他偏愛使用日常、簡明、筆畫盡量少的詞匯,作品拿給小孩也可以閱讀。他的寫作非常自由,在看似日常的敘述中,卻總有著出人意料的余韻。
到今年,谷川俊太郎已經92 歲了,然而最近他自己卻說,年齡越大,越容易寫詩。“我是非常孩子氣的。我寫作的時候盡可能回想起幼年時代的感性,甚至找到心中童年、少年的自己。”
二
還記得和這位詩人在東京的第一次會面,是在2014 年。
當時,我就注意到他的目光。明明臉上皺紋滄桑,眼神卻絲毫沒有歲月感。他看東西的時候,有點像小動物。眼神亮亮的,特別專注,特別單純。初次來到這個世界,對一切充滿好奇和新鮮感的時候,人才會有這樣的眼神。那時他已經80 多歲了,目光卻仍如孩童一般。
后來,我和他的中文譯者田原,一起去拜訪詩人的家。他住在父親母親生活過的一棟很老的木頭房子里,想來或許也是在這里出生。周圍環境非常靜謐,屋內完全是和風的布置,木結構,榻榻米。里面的擺設,如果從他出生之前就是如此,估計要有100 多年了。
和谷川聊起《春的臨終》這首詩,以及我想要譜曲的想法。他笑著說,這是他20 多歲時候寫的。我很詫異。
然后他說,臨終,是死亡的意思。他寫作時,受到寫下《死亡賦格》的德國詩人策蘭的影響,想象著在春天死去的場景。
其實我在讀到“臨終”這個詞時,并沒有直接想到死亡。因為前面有個春字,我所理解的臨終,也許只是終結,春天的終結。那就是更加活力無限又綠意充溢的夏天啊,反而一點也不令人悲傷。
直到聽了他的話,我才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這首詩。他之所以會寫“我把活著喜歡過了”,是一種面對死亡時釋然的心態。因此他選擇在春天,這樣一個并沒有多少悲情色彩,反而總是令人充滿期待的季節。
這讓我想到日本的國花——櫻花。在春日,一樹一樹地開,如雪般爛漫,卻在短短一周的花期后,立刻全部零落。這不正是《春的臨終》最真實的寫照嗎?
2014 年春末,我為該詩譜曲完畢,旋律幾乎一遍完成。用我最喜歡的古典吉他,后期的編曲,加入了很多如康加鼓、雷聲的元素,來配合歌詞“我把惱怒喜歡過了”。
后來,我帶著這首歌去過很多城市演出,每次唱起,都有不同感受。
除了這首詩,谷川俊太郎共出版了《62 首十四行詩》等70 余部詩集。除了日本當代著名詩人這樣的身份,他也是多產的作家、翻譯家及劇作家,共創作了60 余部劇本,翻譯了許多外國童謠,包括史努比(《花生漫畫》)這樣的漫畫書。
他精力旺盛。他為宮崎駿《哈爾的移動城堡》寫了主題歌《世界的約定》。1964 年東京奧運會開幕式,谷川俊太郎負責藝術指導,寫了紀錄片《東京奧林匹克》的劇本。1970 年大阪世博會,谷川俊太郎擔任藝術指導,并且參與同名紀錄片的劇本寫作。
他一直宣稱自己“把詩歌當成商品”,“我寫詩就是為了賺錢,養家糊口。”這段話,初讀令我感到意外。后來想了一下,又心領神會。
他就是這樣一個沒有框架、非常自由的人,隨性、松弛、毫無虛榮心,有時甚至讓你覺得過分真實。
文如其人。也因為是這樣的谷川俊太郎,才會寫出這樣坦誠的文字和詩歌。
(摘自《肆意生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