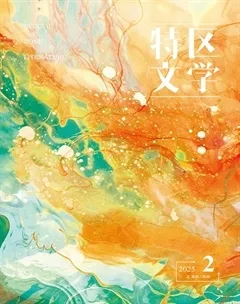眼睛與幸福
一
我們的眼睛發光,因此我們能看。
我們能看,首先并非由于物理意義上的光的照亮,而是由于眼睛的存在。所有從外部降臨的光,無論是陽光、星光、火光或燈光,都只有被“目光”先行照亮,才能被我們看到。在“看”之中,包含著雙重光線,包含著一種光被另一種光所照亮的事實。眼睛不只是感光細胞的集成或一個由晶狀體、視網膜等部分組成的視覺系統,而是一個從深處涌出的光源。它向外部不停放射著不太容易被看到、卻使看得以可能的光線。世界首先不是在日光、星光、火光或燈光中顯現,而是在這些更隱蔽的光、在發出這些光的眼睛中顯現。
我們不僅看到一些瞬時閃過的色彩和點,而且能看到一個個具體、飽滿的事物。我們看到石頭、樹木、飛鳥,它們有名稱,相互之間還有著微妙的聯系。我們不僅看到這些事物的外觀,也能看到它們的存在和本質,看到它們的“是”和“什么”。有時,我們能看得更遠、更深,不僅看到事物,而且能看到“世界”,看到和我們一樣能看到世界的“人”。我們還能看到他人眼中的光,那使我們感到喜悅和幸福的目光。
眼睛就是我們隨身攜帶的小小的光源。即使在完全的黑暗中,我們也能看,至少能看到“黑暗”。盲人也攜帶著這一光源,他們的眼睛雖不能看到物理性的光,卻依然能在另一種光中辨認事物并構成世界。很多盲人看得比其他人更清楚。那么,眼睛發出的“目光”究竟是哪種或哪些光線呢?這些光的至深根源在哪里,它們究竟是從哪兒涌出的?
很多人都意識到,眼睛并不只是一個感覺器官,而且是一個語言器官。我們之所以能夠看到“石頭”“樹木”“飛鳥”,是由于我們在語言中,并通過語言來看。“目光”的本質,是賦予事物以形態和意義的語言。我們看到的幾乎一切事物及其特征、性質,都被語言或意義之光照亮。離開它,我們最多只能看到一些混亂、嘈雜、離散或密集的點,而看不到任何具有形式或形態的東西。在西方主流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中,這種“意義之光”經常被窄化為“理性之光”,亦即主要以概念和范疇為發光介質的、對世界進行秩序化整理的光線。日常世界中,“意義之光”往往并不那么明亮、清晰,它留下了許多模糊、幽暗和神秘的區域;而“理性之光”則是一種持續高能的、具有超級亮度的冷靜光線,企圖驅除一切模糊、幽暗和神秘,把所有事物都變成可認知和控制的對象。在“理性之光”中,我們也許能看得更透徹,但濫用這種亮度過高的光線卻會傷害事物,也傷害我們的眼睛。為了保護事物和我們自己,我們需要恰當地限制“理性之光”的運用,經常從“理性之光”返回較為平易的“意義之光”中,并使這一“意義之光”更微妙、更有庇護力量。
幾乎每一種光都源于火焰。從眼中射出的光線,無論是“意義之光”還是“理性之光”,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生命深處——有一團火,在生命的中心持續燃燒。生命的“中心”,我們稱之為“靈魂”或“心”;當它點燃時,我們稱之為“熱情”。“心”并不是“心臟”,而是某種使得眼睛能發出光亮的生命之火。我們的心居住在眼睛的最深處。在這一意義上,眼睛發出的“語言之光”源于“生命之火”或“心火”,眼中有光彩是因為心中有熱情。嚴格來說,眼睛無法直接地看到它自身,也不能直接看到“目光”從中涌出的“心火”,盡管我們能感受到它在燃燒——我們只能通過他人眼睛的反射和映照,而迂回、間接地看到自己的眼睛和心。透過一雙眼睛(哪怕這是盲人的眼睛),如果我們看得足夠深的話,就可以看到與它們相連的“心”。當然,我們得用“心”去看。在對視之中,在眼睛與眼睛的反射、映照和迂回中,構造出了一個由兩顆心、兩朵火焰共同照耀的區域或空間——我們在這個空間中相互看見,不僅看見對方,而且第一次真正地看見自己,看見被相互看見所照亮的天地。
這就是生命照亮世界的方式。生命自己照亮世界,并因這種照亮而感到幸福。但生命從來不是獨自照亮世界,而是通過眼睛與眼睛的對視,通過與另一個或另一些生命建立關聯,來共同照亮世界。一切幸福都不僅與光的照亮狀態有關,而且與照亮的相互性有關——“照亮”賦予了世界以意義或理智的清晰性,而“相互照亮”則讓世界變得豐盈和溫暖。它讓我們回溯到光從中涌出的火焰那里,并將這火焰置于世界的中心。
二
有一種占據主流地位的意見,將眼睛的“看”理解為單向的或對象性的。這種對象性的看包含著兩類主要形式:第一類是被欲望支配的看,是對對象進行攫取、占有的前奏環節;第二類則是為理性所支配的看,包括各種認知和理論活動。通常人們對“看”的諸種評判,無論是對“理性”或“認知能力”的高揚,還是對觀看中的欲望—快感機制或自戀模式的攻擊,抑或對“視覺中心主義”和“光之暴力”的指控,都源于“看”的此種主流定位。然而,如果真實地理解“眼睛之看”在生活中的位置、作用和活動方式,我們肯定能發現,更多的、更重要的看絕不是單向和對象性的,而是可逆和相互的;不是受制于欲望和自戀的,而是通向他者的;不是認知或理論性的,而是充盈著情感和倫理意義的。眼睛的看不僅有亮度,還有溫度;不僅有快感,還有真實的喜悅。作為“光源”,眼睛因與生命之火、與“心”的連接而構成了幸福的源泉。現代思想中那些層出不窮的對“看”的貶低,皆來自對“看”的窄化和誤解。要破除這些誤解,就需要從生命的真切經驗出發,為眼睛、為“看”正名,并重提“看”在所有知覺和經驗中的首要位置。
看和聽是人僅有的兩種能夠獨自構建起一個清晰、立體、豐盈世界的感知方式。觸覺、味覺和嗅覺雖然也有其豐富、深度和微妙性,但無法單獨地構建一個富于時空形態的世界,而最多只能構成世界中的某些要素和局部。誠然,一個圓滿、深厚的意義世界需要所有感知方式之間的聯覺、互滲和并作,且一種感知中常常包含另一種感知,甚至以之為前提條件(比如各種感知都以觸覺為條件),但它們之間仍有重要次序上的差別。我們可以問問自己:在這幾種感知中,最不想失去的感知是什么?只要誠實地回答這一問題,就能知道究竟何種感知對我們是更重要的。
顯然,我們最不愿意失去眼睛和看的能力,即使是那些強調“聽”“味”“觸”的人也是如此。每一種感知都連接、對應著一種對其進行提純或觀念化的方式,因而感知之間的重要性排序也延伸到以它們為模型的觀念方式之中。人們常說,柏拉圖以降的西方思想傳統對“理念”(idea)、“相”(eidos)或“形式”(form)的重視,體現了“觀看”的優先地位;然而,即使是在以“傾聽”為中心的希伯來傳統和以“感興”為中心的中國古典傳統中,“看”也是不可缺少的(當然并非理論性的看)。在《圣經》傳統的創世論中,“光”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位置(“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并在基督教那里被解釋為“基督”本身——正如奧古斯丁所說,這“光”就是logos或語言。光與暗的區分,是神之“看”的結果(“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另一方面,對上帝的“傾聽”需要親眼“看見”來補充或完成。《約伯記》中說:“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而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也說:“我們如今仿佛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這種“面對面”的親眼見證,就是“愛的觀看”,它朝向的不是“對象”和“表象”,而是神之“位格”。在中國古典思想中,以“天道”為本源的“感興”或“感通”并不只是一味地標舉“體味”或“味道”,同樣也強調“觀象”和“觀文”的重要性。《易·系辭》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賁·彖傳》亦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言。這些都表明對“易道”的領悟不能離開觀察,“象”“文”和“理”都需要“看”來顯現。當老子和孔子以“水”來比喻“道”“上善”或“時間”時,他們的著眼點顯然是“水”在觀看中無形、動變不居的特性,而非從“水”之“味”獲得啟示。從觀念的整體形態來說,人是很難以味覺或嗅覺為中心構造起一個完整的觀念系統的;即使強行這樣做了,最終來說也會有嚴重缺陷,它注定缺少色彩、清晰性、空間感和時間深度。
當代思想中,關于“視覺中心主義”或“光之暴力”的談論已成為陳詞濫調。如前文所說,其前提是把“看”或視覺限定于理論或認識活動之中,或者只看到其中的欲望攫取機制,而忽略了“看”的其他更重要的維度和可能性。理論性的看朝向的是事物的一般本質;欲望性的看則朝向事物滿足主觀需要(自戀和享受)的用途。這兩種看都是用一套同一化的機制去強求事物,而不允許事物作為其自身存在。這兩種看都不能尊重事物的自由和獨一性。我們不難察覺與它們完全不同的看的模態:與認知或理論性的看相對,還有行動性的看或“尋視(Umsicht)”(海德格爾);與帶來利益和快感的欲望性的看相對,還有無利害的對“美”的觀看(康德)。然而,無論是“尋視”還是“美”,都沒有擺脫看的單向性,都仍然攜帶著某種自我同一性的機制(“尋視”著眼于器具之用,“美”的鑒賞中對形式的關注往往受制于集體性的自戀趣味)。真正尊重事物和他人的看,是一種倫理性的、朝向其獨一性和異質性的注視。薇依曾用“注意力”的概念來闡發這種倫理性的看:
對他全心全意的愛,這僅僅是能問他:“你何處痛苦?”而且應當知道不幸者并非作為一群人中的統一體而存在,也不是作為帶有“不幸者”標簽的社會階層的一個樣板而存在。他是作為人,同我完全一樣的人而存在,這個人某一天被不幸打上了無法模擬的標記。為此,只要,也是必須,朝他看上一眼就夠了。
這目光首先是全神貫注的目光,在目光中,靈魂排除了自己所有的內涵,以在自身容納它所注視著的那個人和他的實際情況。只有全神貫注的人才能做到這一點。
這種朝向他人之獨一性的“全神貫注的目光”,就是愛(Agape)的目光。它既不是理論性的,也不是欲望性的,同樣不是“尋視”或“美”的目光,而是全然忘我的。這一目光是“心”的顯示。除了對“不幸者”進行注視的目光之外,那些承載著對他人的信任和喜悅的目光也同樣包含著倫理性的溫度——它們雖不是完全忘我的,但卻是相互性的、讓人感到溫暖的。我們總是愿意這樣去看和被看。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的開篇說:“較之其他感覺,我們都特愛觀看。”我們贊同這句話,卻并不是在“看=求知”或“看帶來快感”的意義上,甚至也不只是由于人渴望活在一個明亮的、有著豐富色彩的世界中,而是由于“看”顯示著“心”,并最終與我們的喜悅和幸福相關。我們用“看”來詢問,來說話,用相互間的凝視來表明愛意。我們會對自己喜歡的人說:“我會去看你的!你也一定要來看我!”這些“看”并不包含任何暴力。
談論“視覺或光之暴力”的人,總是把“看”比喻為一種“吞吃”:看一個對象就是用觀念去同化、剪裁它,這就相當于吃掉和消滅它。然而,既然“看”被比作一種“吃”,那么“吃”難道不是更具暴力性的行為嗎?而“吃”難道不是與“味覺”的關聯更緊密嗎?事實上,那種以“味覺”為中心強行建立起來的觀念系統才是更暴力的,因為一切滋味都是從“吃喝”行為衍生出來的,那些高級的味道、趣味、品位不過是對“吃之暴力”進行精致化、美化的結果。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一個以“食”為天的國度里,文人們最愛談論“味”的豐富、精微和高妙。味覺在本性上具有享樂主義和情調化的特征,幾乎一切趣味都植根于享樂,而享樂是一種吃喝活動——吃更多的東西,吃他人勞動生產的東西,有時候是吃他人本身。所謂的“高級趣味”的基礎,是一個剝奪他人勞動、生命和自由的“上等人”(貴族或士大夫)階層的存在。這個特權階層對“下等人”的剝削就是一種吞吃活動,而他們趣味的“高妙”及其帶來的“區隔”都是不平等的產物,并再生產出這種不平等。以“味覺”為中心的人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不斷致力于將趣味進一步精微化,但由于味覺是一種無距離的感受方式,它注定是缺少反思能力的。一切自我反思都以與自身的距離為條件,無論這是看的距離還是聽的距離。因此,即使是在中國古典思想中,在談論“慎獨”和“自省”時,使用的仍然是視覺化的比喻(《大學》:“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而不是味覺性的比喻。那種以為中國思想是以“味覺”為中心的人,或許是忘記了這些而選擇性地尋找證據。如果過度地、單一化地強調語言“舔舐萬物”的味覺能力,除了使這種語言失去清晰性、空間感、時間深度和從理性而來的反思能力之外,也會導致享樂主義和頹廢在精神世界中的泛濫——味覺再精致、再發達,最終也擺脫不了從吃喝而來的習氣。
三
眼睛的神奇之處在于,它不僅是世界中的一樣東西,而且能把整個世界包含、容納在自身之中。眼睛看上去很小,但似乎比世界更大,它里面有一個(或者說“連通”著一個)無比深邃廣大的空間。另一方面,如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所指出的,眼睛似乎又不屬于世界,它在某種意義上處于“世界之外”。這些奇特的、悖論性的特征,表明眼睛有更多的奧秘等待著我們發現和闡釋。
眼睛之所以能夠包括世界,是由于它提供出了一個“視野”并將萬物圍在其中。這個給出視野,并以“目光/語言”照亮世界的點,在西方近代以來的思想中被命名為“主體”,而眼睛就是“主體”的基本隱喻。提供視野的眼睛不在視野之中,或者說,眼睛看不到它自身,這意味著“眼睛—主體”不屬于世界。眼睛是超越性的。然而,這樣一種主體主義的觀念并未恰當地理解眼睛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因為它仍然是理論化和對象性的,并且是唯我論的。它認為世界是由一個點、一只眼睛或單一主體提供出的視域,卻忽略了世界從來都是被許多眼睛共同照亮和看見的事實。即使是在同一個人身上,眼睛對世界的構成也包含著內在異質性——因為他是用兩只不同的眼睛形成了一片共同的視域。這似乎表明,主體自身就是復數性和自我差異化的,一只眼睛總是需要另一只眼睛,一雙眼睛總是需要另一雙和更多的眼睛。而眼睛的超越性也并非理論化的“先驗自我”的超越性,而是由于眼睛與作為超越者的靈魂或“心”相連通,而“心”既在認識世界,又在開啟、理解和吸收世界。
世界之成為世界,是被眼睛開啟的。眼睛的第一次睜開近似于一次創世活動。然而,眼睛對世界的開啟和照亮能力,是在漫長的時間或歷史中逐漸形成的。在眼睛睜開之前,它處在一種純然內在的空間中,作為還沒有涌出地幔的火焰而存在。這團在內部燃燒的生命或靈魂之火,它在無意識中渴望著從自身中出來,不只是照亮它自己,而且照亮一個外部。正是這團渴望走出自身的“火”塑造了人的眼睛,在我們睜開眼的瞬間形成了我們的視力。而“世界”作為一種超越一切事物、一切局部的整全空間,其整全性也有賴于靈魂自身的活動。世界不是事和物,而是事/物的可能性或可理解性的境域。這一可能性的境域需要先行張開或撐開,而張開它的力量是一種超越性。海德格爾將“世界的開啟”解說為“林中空地”(Lichtung)的發生,而“林中空地”這一隱喻指向“火”的開辟作用。我們認為,世界作為先行被開啟的可能性的境域,打開它的超越者正是“靈魂”或“心”——通過靈魂之火對混沌黑暗的辟易,亦即通過靈魂的記憶、注意和想象,至高的可能性與至深的可能性才被給予,無論這是生存狀態還是邏輯模態意義上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同時也被提供給作為“光”的語言或logos,由眼睛放射出來。于是,與靈魂相連的眼睛不僅能看到深淵和天空,而且自身就有深淵和天空。
看到或照亮世界,這是眼睛向外部超越的方式。但是同時,還發生著另一重方向的運動:世界在被看到時也被吸納、收聚到眼睛之中,作為一種“征象”而進入靈魂或“心”的內在記憶之中。當眼睛閉上時,無論是在睡眠、冥思還是接吻,靈魂都在其內部吸收、沉淀著世界的這些征象。在這一意義上,眼睛是靈魂的內在空間與世界之間的接口或“窗戶”,它并不只是身體器官和語言器官,更是靈魂的器官。在面孔,甚至身體的所有組成部分中,眼睛最重要、最能體現出個體的獨特性和深度,這正是基于眼睛、靈魂和世界之間的關聯:眼睛通向靈魂,因而它構成面孔的靈魂;在面孔中,它是唯一能發光,能容納、照亮、吸收整個世界的部分。一個人美,首先在于其眼睛美。眼睛之美,則是由于眼里有光,有熱情,能看到世界的美和另一些眼睛的美。
眼睛之所以能夠成為在靈魂與世界、內與外之間進行連接和判分的邊界,除了它具有映現世界,并用語言照亮世界的能力之外,與它的空間構成和形態特征也深有關系。我們相信眼睛中“有”或者“通向”一個深邃的內空間,是因為眼睛本身具有一種向內收斂的、如同正在旋轉的星體或星云的形態。眼睛向我們顯現出來的部分,從眼白、虹膜到瞳孔,逐漸收聚為一個黑色的孔,從形態上說具有某種“吸力”。當我們看進虹膜和瞳孔深處,就會看到那里發生著萬物的生滅,似乎那里有閃電,有精芒,有大海和波濤,有日月與星體的運行。這些吸力、遼闊和深邃讓我們感到,眼睛確實具有將整個世界吸收到它內部的潛能。正如我在一首名為《黑眸轉動》的詩中所寫:在世界被吸入眸子的時刻,/你也讓其中的黑暗轉動。
光明與黑暗同時在眼睛里轉動,構成了一個微縮的宇宙。眼中的黑與白,像陰陽一樣分布又嵌合在不同的位置。眼睛既可以是明亮的(像燈火或星星),又可以是幽暗的(像黑洞或深淵),因為眼睛是感受和判分明暗的依據。通過判分明暗,眼睛處在靈魂與世界的邊界上。作為世界中的一樣事物,眼睛被固定于身體;而作為與超越者相連,并具有超越性的東西,眼睛又有著某種特殊的自由。在靈魂出竅、世界完全被置換為內在空間的時刻,與靈魂的超升相對應,眼睛也漸漸脫離了身體,“像兩只甲蟲,在天空飛旋”(一行《追憶》)。
四
在前文中我們說過,世界被眼睛照亮,但不是被一雙眼睛,而是被無數雙眼睛照亮。世界是共同的世界。“共同”意味著,眼睛總是能看到另外的眼睛,并把它們當成和我們一樣的生命或靈魂的眼睛;同時,我們也需要通過他人的眼睛來看待世界和自己。通常,對他人的眼睛的需要,是為了用不同于我的視角來補充、修正我自己的視角(康德所說的“擴展的思維方式”);同時,我們也試圖在他人的眼睛中,找到或看見真正的自己,避免受自欺蒙蔽。這里,“他者的眼睛”成為我們理解世界和自身的必要條件和前提,但它并不只是一種反射性的鏡面效果,而且包含著一種內置性。每一雙能進行正常觀看的眼睛都在自身中內置著他者的眼睛。這樣,我們無論看什么,都同時用好幾雙眼睛在看,而且會看到那些眼睛正在看我們自己。
但是,眼睛中的“他者之眼”不止于是我們理解世界和自身的中介性條件;如果我們活得真實,“他者的眼睛”也構成了我們生命的目的。這當然不是指虛榮者為他人的眼光和認可而奮斗,而是指,我們最終的、真正的幸福,就在于能看到一雙滿含愛意地注視著我們眼睛的眼睛。這里所說的“愛”并非薇依所說的“摯愛”(Agape),而是指構成婚姻共同體之真實本質的倫理之愛(love)。倫理之愛固然需要行動和言辭,但它最深切的表達是在眼睛的相互凝視之中。愛是兩雙眼睛、兩顆心的相互尋找。在無數的時間里,我們看到了各種各樣讓人眼花繚亂的東西,但都歸于黑暗和空無;而當我們遇見了一雙真正能“看見”自己的眼睛的時刻,目光才抵達了它的終點。在這個時刻,“我的世界”被“你的眼睛”所吸收,而“我”渴望著完全住進“你的眼睛”里。這不僅是因“看”而感到幸福,而且是因“看見自己被看見”而幸福。當“我”看到“你”在看“我”時,整個世界都在旋轉。而只有看到“你”,世界才進入“我”,才成為“我”愿意居住于其中的世界。
這當然需要一種更豐盈的看,需要目光中蘊含深刻的情感。在這些時刻,眼睛說話,不僅通過“意義之光”來說話(賦予事物以可理解性),而且是在“對話”的意義上說話。眼睛是一種語言器官:沉默中,我們通過注視來說;在愛的注視中,眼睛說著最深的話。愛之中最不可缺少的并不是性,也不是有聲的交談,而是默默的相互凝視。這凝視是把對方的眼睛當成一個可以永遠迷失的深淵或天堂,當成一泓永不枯竭、沁人心脾的潭水——“你眼睛的深潭,我每日都要從中汲水”(一行《深潭》)。我們也通過閉上眼睛來說話,通過流淚或微笑來說話。在接吻的時刻,我們總會閉上眼,使自己從世界返回到靈魂的純然內在性之中——在這一時刻,我們把自己整個地純化為“心”(所謂的“全心全意”),并將它完全交付出去。閉上眼是為了讓眼睛返回心,并從心中汲取深刻的力量,正如在冥想或睡眠中,閉上眼是為了用“不看”來培育和促成“更好地去看”。眼睛的“看的能力”同時也是“不看的能力”:那些懂得何時應當不看的人,才懂得何謂真正的看。
淚與笑是兩種極為重要的眼睛言說方式。眼睛本是一個具有庇護力量的內空間,但痛苦卻使之傾覆、撕裂——“每一滴淚中都有一只尚未孵化的雛鳥,從眼睛這深邃的巢中跌出”(一行《回聲》)。這傾覆的“巢”,也可以被比喻為難以愈合的“傷口”,淚水是從這“傷口”中迸出的詞。不過,感到歡樂和幸福的時候,我們也會流淚,就好像是一些已經長出翅膀的鳥在進行試飛。這些帶翼的淚珠總是伴隨著歡笑,被笑所具有的溫柔浮力輕輕托護著,讓它們不會重重地墜落在地面。在“笑”的諸多情形中,人們總是過分關注幽默、反諷或滑稽的笑,因為這幾種笑都具有某種認知和揭示性,或者因為朝向的是僵化的窘境而具有恢復生命活力的效果。但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笑仍然是從愛的喜悅而來的笑——與其他的笑主要依賴于張開的嘴巴不同,這種笑主要依賴的是眼神的流轉。在幽默、反諷和滑稽帶來的笑聲中,眼睛幾乎被嘴和臉擠得不可見了;而愛的微笑卻使眼睛之美突出地顯現出來,如花綻放的盈盈笑意不僅是甜蜜的,而且具有療愈所有創傷和痛苦的效果。
在愛的喜悅中,在它所帶來的淚與笑中,眼睛抵達了它最完滿的形態。我們不僅在另一個人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而且在其中忘掉了自己,并因此成為真正的自己。我們看到了彼此眼中那親切又異樣的光,有時會把這光歸之于“神”。相愛者認為,愛是神意所規定的命運。在用“倫理之愛”對《約翰一書》中“神就是愛,住在愛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的“愛”(Agape)進行替換之后,這句話仍然成立。確鑿無疑的是,“神”住在我們的“心”里;但由于眼睛與心的連通和接近,“神”也常常住在眼睛里。我們總是能在另一雙眼睛中看到“神”的蹤跡。在一種轉義用法中,我們可以說:“眼神”是最微小的神,也是今天唯一能親眼見到的神。能見到神的人是有福的。而只有在愛的相互注視中,我們才能領受“眼神”的啟示。
一行,本名王凌云,1979年生于江西湖口。現居昆明,任教于云南大學哲學系。已出版哲學著作《來自共屬的經驗》、詩集《新詩集》《黑眸轉動》和詩學著作《論詩教》《詞的倫理》,譯著有漢娜·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等,在各種期刊發表哲學、詩學論文和詩歌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