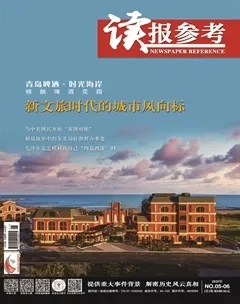我們需要什么樣的“老年觀”
進入現代社會后,人類的長壽化已經成為趨勢,一些研究預測,新近出生的人口中,活到100歲的概率會越來越大。但人活80歲和100歲相差了整整20年,人們對晚年生活的各種安排,包括健康、醫療、財務,都需要作出哪些調整呢?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客座教授沈潔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 記者:近年來,你在很多場合都強調說,我們現在光講老齡化已經不夠了,還要關注長壽化,為什么會這么講?
" 沈潔:老齡化大家越來越關注,但長壽化的問題在國內還不太受重視。日本是世界上第一個長壽國,平均壽命也是世界第一位,所以,長壽化對日本早就是個常態化問題了。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也在不斷提高。根據聯合國人口研究機構預測,未來我國百歲老人的數量會保持快速增長趨勢,將從2005年的1.9萬人增長到2025年的14.4萬人,再到2050年的59.7萬人。活到100歲曾是生命的奇跡,但以后這可能是一種常態了。一個人的生命延長了20年,你過去的觀念、過去積攢的錢、過去作的各種安排都不一定適應現在的需求了。這場悄悄行進的長壽化將改變我們的經濟結構、社會形態和生活方式,快速地將我們推進到一個新時代。
" 記者:我們到底應該構建一種什么樣的“老年觀”?
" 沈潔:日本社會這些年在倡導一個口號,就是創建共生社會。日文是這樣表述的,即共同生活、相互幫助、相互依存的社會。我們已經進入了老齡社會,這是一個所有人都必須接受的事實。在這樣一個社會里,不管你是老或者少,有錢或者沒錢,能不能自立,作為一個人的最起碼的尊嚴要得到平等的尊重。這種尊嚴包括老人臥床不起一直到死亡階段的尊嚴,只有這樣才可以說,一個人的生命得到了很好的照顧。
" 在這個邏輯之上,去構建一種新型的老年觀,當然需要長期的社會教育。日本從中小學開始就在課程體系里面設置了有關老齡社會的內容。比如,開設模擬課程,高齡老年人可能半身不遂,還有一些眼睛看不見的殘障老人,他們怎么行動、怎么生活,這些課程會給孩子們提供一些模擬的工具和場景,讓他們親身去體驗老人們面臨的身體不自由的處境。
記者:按照人口學家的預測,中國近幾年將迎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退休潮,數以千萬的城市職工將迎來退休。如何安排好退休后的生活,似乎大部分人并無充分的身體和精神上的準備。對于已經迎來老年或者將要迎來老年生活的人們,你認為他們應該如何發揮自己的主體性,過上更有尊嚴、更高質量的老年生活?
" 沈潔:首先是老年人自身的意識要變革。為什么現在年輕人和老年人會有所謂的代際沖突?背后很大程度上還是價值觀的沖突。我們所有人現在身處的就是一個急劇變化的多元化社會,但很多老年人客觀上來講道德價值觀還是比較單一,這是老人自身存在的問題,需要自己去改變,要盡量讓自己的價值觀也多元化。
" 其次,老年人要有自己的人生設計。我們國內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還有能力給退休老人,尤其是城市退休職工支付相當高的替代率的養老金,但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由年輕人承擔撫養老年人的現收現付社會保障機制會越來越困難。日本老人現在領取的養老金就是在逐年削減,而且削減得非常厲害,已經打破了“退休金只漲不落”的傳統觀念。因為當初的制度設計者誰也沒預料到老齡化速度這么快,現在還要解決少子化的問題,資源要轉移到兒童和育齡青年身上。這也是無奈之舉,所以,老年人更要及早地進行人生設計。
" 記者:中國這些年也在嘗試推行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在很多地方進行了試點,也遇到了不少問題。你認為日本的介護保險制度有哪些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 沈潔:日本的介護保險制度確實做得比較細,它是一個準市場原則,由政府制訂服務價格,每三年調整一次,市場主體不能隨意抬價,老人到這個準市場里去找第三方的服務機構,根據這些機構提供的服務以及相應的評分來獲得保險方的費用支付。這樣一來,介護服務就形成了一個社會市場,它既是一個公共產品,但又存在市場化的競爭,從而提高了服務供給的規模和質量。介護保險制度實施后,大量的民間資本進入照護行業。
" 記者:東亞社會的家庭結構正在解體,獨居家庭越來越普遍,這會給養老帶來什么挑戰?我們對傳統家庭的概念是否也應該作出調整?
" 沈潔:傳統上是以血緣作為家庭的判斷標準,這也是主流,但是那些非主流的,我們應該怎么去認同也是關鍵。比如,年輕人不結婚同居,生下的孩子在法律上要同權,并且消除社會歧視,這個問題在日本已經基本解決了。日本一些地方政府還在推動組合家庭的模式,由政府提供一些比較廉價的公租房,吸引年輕的大學生或者公司職員與老年人同住,只需交很少的租金,但要兼顧對老年人的照顧。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張從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