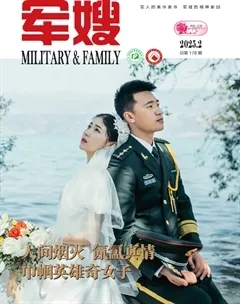父母的拿手菜
父親的“三件套”
父親會(huì)做的美食不多,十個(gè)手指頭就能數(shù)得過來。可他做的每一種美食,制作過程都挺復(fù)雜。現(xiàn)在想想,應(yīng)該是他處事很嚴(yán)謹(jǐn),容不得半點(diǎn)馬虎的原因吧。
父親做的美食中,有三種比較典型,也讓我印象深刻。它們是:煙熏肉、鹵食和豆腐腦。
前兩種比較講究季節(jié)性,后一種則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每當(dāng)深秋來臨,風(fēng)吹葉落,小院滿地金黃的時(shí)候,父親就開始準(zhǔn)備做煙熏肉的工具了。那是一個(gè)超大的鐵質(zhì)廢舊油桶,該有一米多高,不知他從哪里弄來的,進(jìn)行廢物利用。
父親先是把空油桶上口的鐵封皮剪掉,然后就讓我哥哥拎個(gè)籮筐,到家后面的山上去滿山遍野地找黃土。我們當(dāng)時(shí)住在江蘇南京,不像北方,黃土遍地都是,那里要想找到一點(diǎn)黃土很難。但哥哥還挺有本事,竟然能把黃土找來。因?yàn)橹挥悬S土可以泥墻,一般土沒有黏性是不行的。
父親要黃土并不泥墻,而是泥那只空油桶的內(nèi)壁。他用哥哥挑回來的黃土,加上水和成泥糊狀,然后糊在油桶的內(nèi)壁上,大約要糊至少3厘米厚。等黃土風(fēng)干了,這個(gè)自制的煙熏爐就可以用了。
買好了肉,放上各種作料腌制后,就要開始下一道工序:熏。
父親將煙熏爐倒扣過來,底部朝上,在底部的中心鉆一個(gè)小孔,將腌制好的肉從煙熏爐內(nèi)部用鐵鉤子掛在小孔上。熏肉用的柴火是院里那棵柏樹落下來的葉子和枯掉的樹枝。父親說,用柏樹枝熏出來的肉,味道更香。
當(dāng)然,火候的掌握很重要。這其中的技巧,就只有父親知道了。
熏肉做好后,便成了我們家深秋季節(jié)乃至隆冬時(shí)節(jié),飯桌上的一道菜。我不愛吃熏肉,但是其他人都愛吃,而且吃得很香。
利用土灶的原理做出吃的東西,對(duì)父親來說是有歷史淵源的。他對(duì)我們說過,過去行軍打仗,遇到緊急情況時(shí),經(jīng)常會(huì)輕裝簡(jiǎn)行,把多余的東西都扔掉,甚至做飯用的鍋啊、爐子啊什么的都不帶。有一次,又是在那樣的緊急狀況之后,他們急行軍到了一個(gè)前不巴村、后不著店的地方,想要做點(diǎn)吃的,又沒鍋沒灶,怎么辦?
他們有的是辦法,當(dāng)然,這也是艱苦的環(huán)境逼出來的。天寒地凍,他們?cè)诘厣吓僖粋€(gè)坑出來,找點(diǎn)干柴放進(jìn)去點(diǎn)著后,把隨身攜帶的糧食袋里的玉米粒子丟進(jìn)去,再用土松松地把坑掩住。炭火被蒙在土里,就將玉米粒子烤得膨脹開來。不一會(huì)兒,那些玉米粒子就從火坑里一粒一粒地蹦出來了。他們就圍著火坑撿爆米花吃,既取了暖,又填了肚子。
父親給我們講這些故事的時(shí)候,笑得非常開心。想想也是,經(jīng)歷了槍林彈雨、生死攸關(guān)的危急時(shí)刻之后,還能夠放松下來,用那種特殊的方式吃到爆米花,的確值得高興,也值得回味。

熏肉做好之后,季節(jié)繼續(xù)更替,只有在冬季才能吃到的鹵食,就登上我們的餐桌了。
為什么說只有到了冬季才能吃到鹵食呢?因?yàn)槎旒依飼?huì)額外升起一個(gè)烤火爐。我們家用的是那種“北京爐”(一種老式的蜂窩煤爐)。為了省煤,父親也會(huì)在“北京爐”的內(nèi)壁糊上一層厚厚的黃土。當(dāng)春天來臨的時(shí)候,那層黃土就已經(jīng)被燒得像磚一樣了。
冬天的“北京爐”會(huì)承擔(dān)起很多重任,除了取暖,全家用的熱水都是靠它燒,這樣可以省很多做飯用的蜂窩煤。而它的另一個(gè)任務(wù),就是燉制鹵食。
父親用來燉制鹵食的器皿是一個(gè)高高的、大敞口的陶罐,里面可以同時(shí)放進(jìn)去一個(gè)蹄膀和一只雞。做鹵食的過程,不像做熏肉那么復(fù)雜,只需把料調(diào)好了,再加上水,放在“北京爐”上燉就是了。那個(gè)陶罐里的食物,不斷地被撈出來放上餐桌,又不斷地有新食材放進(jìn)去,不斷地?fù)剿畵搅希u汁越燉越濃、越燉越香。
每年冬季那段時(shí)間,當(dāng)我們頂著朔風(fēng)放學(xué)回家,一進(jìn)門,聞到那濃濃的鹵肉香,就知道父親又做鹵食了,冬天的感覺也就來了。
等到開春,天氣漸漸暖和,鹵肉的香氣散去,豆腐腦的甜美味道就隨之而來。
說到制作豆腐腦的過程,那又復(fù)雜了。但這是父親經(jīng)常會(huì)做、我們也愛吃的一種食物。為了做豆腐腦,父親還特地請(qǐng)石匠做了一副小石磨。
豆?jié){是豆腐腦的前奏曲,要先磨出豆?jié){,才能做出豆腐腦。
做豆?jié){要先泡黃豆。父親在頭一天晚上就把黃豆泡起來,到第二天早上就可以上小石磨研磨了。通常,這道工序是我最喜歡摻和幫忙的,而且那很考驗(yàn)一個(gè)人左右手的協(xié)調(diào)能力。
小石磨由兩部分構(gòu)成:磨盤和磨子。我剛開始學(xué)著磨的時(shí)候,左手在轉(zhuǎn)動(dòng)磨子時(shí),常常會(huì)把右手拿著的料撞翻,被父親笑話了好幾回,后來才慢慢適應(yīng)。
磨出來的豆?jié){和著豆渣,順著磨盤上的彎道源源不斷地流入下面的一個(gè)大桶里,父親用兩片三厘米寬、半米長(zhǎng)的竹片交叉成十字狀,中心用螺絲固定。竹片的四個(gè)角鉆四個(gè)眼,分別吊住一塊白布的四個(gè)角,就做成了濾網(wǎng)。把這個(gè)濾網(wǎng)用架子吊起來,下面接一個(gè)大鍋,將磨出來的豆?jié){混合物舀到濾網(wǎng)里,豆?jié){就被過濾到鍋里。白布兜著豆?jié){,豆?jié){往下滴落,仿佛奶牛的乳汁。
純豆?jié){到了鍋里,加熱,點(diǎn)石膏,這道工序特別考驗(yàn)父親的技巧。石膏點(diǎn)多了,豆腐腦就老成了豆腐,點(diǎn)少了,又太嫩,不能結(jié)成豆腐腦。但父親總能恰到好處地點(diǎn)到為止,我們也能吃到滑口、香濃的豆腐腦。通常,我們喜歡在豆腐腦里加白糖,吃甜漿。
34年前,父親離世后,我家的煙熏肉和鹵食盡管也還在做,但都是簡(jiǎn)易版,無需再去找黃土,也不用“北京爐”。那副磨出過很多美食的小磨盤,也在一次修房子時(shí),把上面的磨子弄丟了。豆腐腦這一家常美味,也就永遠(yuǎn)留在了父親在世的時(shí)候。
母親的珍珠丸子
母親的拿手菜,總是和年味不期而遇。
在我兒時(shí)的印象中,母親不常下廚做飯,她說過,“我一小出來參加革命,又不是為了做家庭婦女”。母親說這話時(shí)的表情,仿佛又回到了小姑娘的樣子,多少帶著點(diǎn)任性和倔強(qiáng)。這種性格,和年輕時(shí)一身戎裝的母親,倒是十分般配。
雖不常下廚房,但母親只要進(jìn)了廚房,做起食物來就特別認(rèn)真。她最擅長(zhǎng)的一道美食——珍珠丸子,這道菜的制作程序就挺復(fù)雜。
每次,母親都先要將豬肉洗凈剁成肉糜,蔥姜剁碎拌到里面,再撒些料酒、適量鹽,攪拌均勻。之后,搓成直徑3厘米左右的肉丸,放到事先泡脹的糯米里滾一翻。最后,她把沾上糯米的肉丸子裝盤,上鍋蒸15分鐘,便“大功告成”。
小時(shí)候一看母親做珍珠丸子,就總感覺繁復(fù)無比。我那時(shí)其實(shí)并不愛吃這道菜,因?yàn)楫?dāng)時(shí)很少有凈瘦肉賣,所以丸子里帶了不少肥肉。我從小就不愛吃肉,更不要說肥肉了。我只是覺得這道菜很好看,雪白的糯米附著在肉丸子上,上鍋一蒸,糯米熟了,膨脹開,晶瑩剔透,真的像一粒粒的珍珠。
但是家里其他人都愛吃。每次珍珠丸子一上桌,往往是最快被吃完的。所以這道珍珠丸子,帶給母親很大的成就感。

除了珍珠丸子,母親還有個(gè)絕活,就是做牛肉湯,而且味道獨(dú)特。我先生特別愛吃她做的牛肉湯,他也曾試著自己做,但就不是那個(gè)味。他很納悶,問我:“媽媽那個(gè)牛肉湯是怎么做的?我怎么就做不出那個(gè)味呢?”
說實(shí)話,我也不知道母親是怎么做的牛肉湯,盡管我在一旁看她做過。灶臺(tái)上一溜排的調(diào)味品,母親挨個(gè)兒打開聞一聞,覺得好的就往湯里撒一點(diǎn),她是憑著感覺在做。哈哈!而我就算再看她做10次,也記不住她究竟放了哪些調(diào)味品啊。
不過,珍珠丸子我倒是學(xué)會(huì)了。
母親的珍珠丸子的做法也在逐年地改進(jìn),食材也變了。主要的食材——原來帶肥帶瘦的豬肉,變得沒有肥肉了,也合了我的口味。丸子餡里還加了雞蛋和嫩豆腐,這樣更加鮮嫩一些。蔥姜、鹽、料酒、醋和醬油起鮮,其他程序不變。珍珠丸子繼續(xù)雄踞我家年夜飯保留菜品之首。
珍珠丸子年年有,這是母親的菜。
后來,母親年事高了,不再做菜。每年我們忙年夜飯的時(shí)候,她就坐在旁邊看我們做。我則接過母親的真?zhèn)鳎旨恿艘稽c(diǎn)改進(jìn),在丸子餡里加一點(diǎn)黑胡椒粉,這樣做出來的珍珠丸子,味道更加鮮美了。
母親患上阿爾茨海默病后,腦子一時(shí)糊涂、一時(shí)清楚。但是我們和她說話,她都會(huì)有反應(yīng),會(huì)很開心地笑,會(huì)說“好孩子”,會(huì)突然說“謝謝你。”
2024年8月25日,母親因病離世,享年99歲。從此,餐桌旁再看不到母親的身影,但我會(huì)讓母親的那道珍珠丸子,一直出現(xiàn)在我們家的年夜飯桌上。
(作者為影視編劇)
編輯/李穎